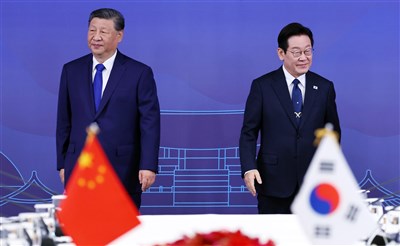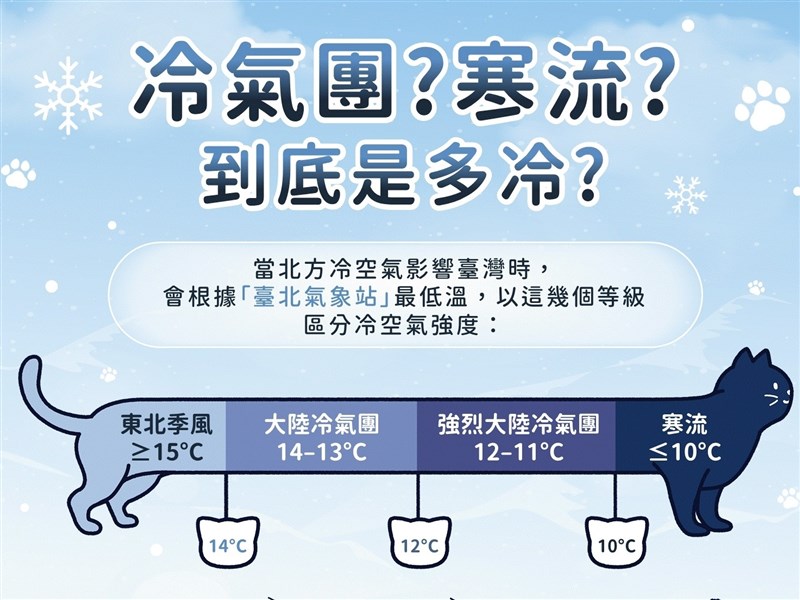科幻小說家X未來學家 劉宇昆與眾不同的創作之路【專訪上篇】
文:黃淑芳
若用武俠小說的辭彙描述,劉宇昆(Ken Liu)是個罕見的奇才。他在中國甘肅出生,11歲隨父母移居美國,在哈佛大學一口氣修習文學、法律、資訊工程;畢業後先是在新創公司當工程師寫程式,然後做了律師,主攻專利與企業法務,利用每天搭火車通勤的時間寫小說,單程寫個500字之類的。
他以短篇小說〈摺紙動物園〉〈物哀〉成為史上第一位同時獲頒星雲獎、雨果獎和世界奇幻獎三大科幻獎的作家,同時把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三體》、郝景芳的〈北京摺疊〉、陳楸帆的《荒潮》翻譯為英文,推上世界舞台。
他以自創的「絲綢龐克(silkpunk)」風格,描繪獨樹一幟、植基於東亞古代工程傳統的科幻技術美學,用10年時間寫完架構龐大的史詩長篇《蒲公英王朝》(故事裡的英雄是工程師而非巫師),展現過人的長才與強烈的企圖心。
劉宇昆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摺紙動物園》2018年在台灣出版,立即造成轟動。15個短篇故事遊走於軟、硬科幻與歷史奇幻之間,題材多元、情感深刻、文字優美,不但收服向來嚴苛的科幻小說迷,也打動無數非科幻讀者——原來科幻小說可以這麼寫、這麼讀。
現在,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選集《隱娘》來了。同名短篇改寫自唐人傳奇、因為侯孝賢電影而聲名大噪的聶隱娘;許多篇章反覆凝視人類與「後人類」如何不斷重複過去的錯誤與愚蠢。寫著望向未來的科幻,不斷回頭從歷史取材,輔以哲學思辨,是劉宇昆的一大特色,也因此既瑰麗又殘酷,深沉而迷人。
中央社書面專訪這位重量級科幻作家,與他一同回顧20年來的創作歷程,看他如何探觸科技,從中提煉出猶如珍珠般可貴的隱喻,幫助我們理解充滿困惑的凡人旅程。
祖母教我的事:好故事不是說出來的
Q:您把《隱娘》題獻給教您「該如何說故事」的祖母。能否與我們分享這部分的回憶?您與祖母誰講、誰聽?說好一個故事的要訣是什麼?
A:祖母是第一個說故事給我聽的人:童話、民間傳說、她自己編的故事,也告訴我家族的歷史。她也是第一個唸書給我聽的人:《福爾摩斯》、《西遊記》、狄更斯,甚至《數學手冊》。她還是那個驕傲地對朋友展示我寫的第一本書的人,當時我在讀幼兒園,自己用蠟筆畫插畫。她訂閱許多小說類雜誌,這在當年算是很奢侈的享受,她帶我認識藝術與文學的重要,讓我知道兩者都值得投資。
最重要的是,她讓我明白,好故事不是說出來的,而是領略出來的。她會用她患了關節炎的疼痛手指替我織毛衣,讓我在嚴冬裡免於受寒,於是,「愛」這個字總會令我想起她顫抖的雙手。她讚美我創作的故事,遠多過我的學業成績,這讓我終其一生都在乎我對事物真正了解了多少,更勝於考試的成績,很多考試其實是威權者為了自身目的而強加於人的無用的障礙賽。
我們每個人都像古代史詩裡的英雄:生來天真無知,就如亞當或吉爾伽美什(Gilgamesh),沒有名字與故事,心靈潔白如紙;而後神祇與惡魔化身為父母及師長,引導我們穿越蘆葦叢生的海岸,橫渡浪濤洶湧的怒海,賜予我們此生最初始的種種回憶;這些最早的故事,等同於我們個人的神話,定義了我們——我們被愛的方式教會了我們如何愛人,我們受傷的經歷建構了我們看待痛苦的方式;層層疊疊,故事接著故事,歷經漫長的探索、取經,是沿途遇到的導師、朋友、情人和惡棍留給我們的傷疤與老繭成就了我們;而後,當我們從人生旅途的陰暗森林掙扎而出,我們意識到——隨著死亡愈近,體認愈深——我們也成為後浪眼中的巨大形象,也許是英雄,也許是惡棍。我們敘述自己的存在,用大量的故事將靈魂填滿,直至衰老降臨,在寫滿咒語的裹屍布中,心靈終得安息。
我很幸運,第一個講故事給我聽、帶給我個人神話的人是我的祖母,但願我人生的故事能讓她引以為傲。
傳奇「再折疊」 重塑聶隱娘的道德勇氣
Q:〈隱娘〉和選集裡其他故事明顯不同,這個故事確有所本,而且有八成與唐人傳奇原著相符,補足了傳奇沒有講白的奇幻,給隱娘下嫁磨鏡少年一個浪漫的新解,也改動部分情節。為什麼這麼設定?這是一種顛覆善惡嗎?
A:我想,〈隱娘〉可以看成是唐人傳奇的「再折疊」。透過拓樸學的再折疊,原始元素仍能以各種形式呈現,但在數學上變形為新的組態。
原著質樸而鮮明,徹底顛覆了俠客的人設,成為律法之外、以武犯禁的形象。唯一有行動力的角色是隱娘,故事中的所有男人本質上都軟弱無力,只是她——或許還包括她的比丘尼師父——行使意志的工具。
在我的「再折疊」中,保留了隱娘不受控制的行動力,與認為自己才正確的剛烈,不過我想讓它再複雜一點,與現代世界接軌。我們活在經常被告知只要乖乖遵循行為準則就能期待得到正確結果的社會:程式設計師毋須關心編寫的程式是好是壞,只要它能依照要求的規格運作;經理人毋須在乎窮者更窮還是富者更富,只要能讓股東賺到最多的錢;工程師毋須在意是否正在殘害環境或破壞動物棲地,只要照藍圖行事。這與年輕女子只因師父心意已決就被要求取人性命,並無二致。對個人「角色」的癡迷,抱持只要奉命盡職,道德後果自有他人解決的心態,正是邪佞惡行屢見不鮮的主要原因。
我們最感到自由的時候,也最可能在不經意間同流於世界的不公義,選擇了一條容易走的路。所以,當我們被告知要履行職責時,都該戒慎警惕。
經過我「再折疊」的隱娘,質疑得到的指令,甘犯上意。希望我們都能有這樣的道德勇氣。
Q:《摺紙動物園》與《隱娘》的短篇選集,在動鐘延緩、人造感知等科幻元素之外,有很強的歷史性(而且頗沉重)。〈終結歷史的人〉、〈訟師與孫悟空〉、〈重生〉背後共同的軸線,可以說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有權勢的勝者試圖掩蓋過去的罪愆、改寫歷史,這是跨國、跨文化、跨時代不斷重複發生的事。〈訟〉寫到:「既然知道了那段過去,你就不再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你如果不行動,就是在這股新暴力、這種根絕真相的做法下(與當權者)狼狽為奸。」
持續以歷史元素創作,是您身為創作者的行動嗎?您希望讀者讀了之後,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A:我對工具主義者對藝術的辯護抱持高度懷疑。他們認定文學理應「振奮」或「鼓動」人心,引導讀者做出具體的行動,對我來說那太像政令宣導。我不以這種角度看待文學。
所以,我不期望讀者對我的故事做出任何回應。
這說法背後有更深層的理由,我想我最好解釋一下。
當然,我的故事有道德立場,有觀點——也就是說,純粹「客觀」或非道德的藝術稱不上藝術,只是裝飾。我鄙視這種裝飾。
那我期待讀者對我的作品如何反應?我希望,但不期望,他們以獨立的道德身分參與其中。歷史沉重是既成事實,但回應這份沉重的方式,就是寫下我們一部分故事,交由他人評斷。好的藝術作品應該體現創作者的靈魂:包括作者的道德判斷、理解、情理共感,以及愛。讀者將以同樣的方式回應,就像他們的靈魂回應另一個赤裸的靈魂那樣,毫無狡詐,毫不扭曲,毫不粉飾。
在靈魂與靈魂的坦誠互動中,讀者是有力量的道德存在。他們隨後選擇的行動,反映了他們的靈魂,是其意志的產物。這就是為什麼作者其實不能期望讀者的任何行動——在此我想借道家的一段話:「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無所期盼,能創造出最真實、最有意義的回應空間。
創作核心:生而為人 究竟有什麼意義
Q:讀完《隱娘》全書,再回頭讀第一篇〈鬼日子〉,它的強度比第一次讀時拉高很多。這篇2013年發表的短篇,早於選集很多其他作品,卻某種程度貫串了整本選集。〈鬼日子〉的歐娜就是兩種文明的混合物,害怕被遺忘的舊人類努力想要留下遺贈,人類與後人類的交流、身分認同問題永遠不會消失……。我們可以解讀為這反映著您近十年關切的核心議題嗎?
不過,您先前受訪時提及,選集的第一個故事會選一篇相對不討喜的,過濾掉不喜歡這一味的讀者。對您來說,〈鬼日子〉也是這樣的安排嗎?
A:我寫作生涯的核心主題是:生而為人,究竟有什麼意義?
科技、歷史、科學,社群媒體、神話、奇異點、基因工程、氣候變遷、刑事司法、哲學、人工智慧……這些議題只是對上述主題提問的諸多方式。究竟是行為造就了我們,還是記憶成就了我們?我們對歷史有什麼責任?對子孫後代的職責又在哪裡?怎樣才算是正確的人生?人類是由感性主導還是理性主導?我們是生物機器還是靈魂動物?就像您說的,這些問題沒有唾手可得的答案,也可能永遠不會有答案。
這很好,表示我會有源源不絕的小說題材。
關於您最後一個問題:我想我原可挑選其他故事來扮演「守門人」角色。我喜歡科技主題,認為我們愈探觸科技,故事就愈靈性、愈共感——唯有真正深入科技主題,才能提煉出最令人回味、如珍珠般可貴的隱喻,幫助我們或多或少理解自己正在行進中的,充滿困惑的凡人旅程。(編輯:王靖怡) 1110415
書名:隱娘
作者:劉宇昆(Ken Liu)
譯者:歸也光
出版社:新經典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08
新書線上活動:從《摺紙動物園》到《隱娘》——閱讀劉宇昆開創性的科幻寫作
時間:4月22日(五)7:30pm-9:00pm
主講人:高翊峰(小說家)、馬欣(作家)、譚光磊(版權經紀人)
合辦單位:Readmoo
活動平台:Google Meet
活動詳情:https://forms.gle/pjcwa8jzSeXqH74w9
- 2025/08/27 15:06
- 2022/05/06 12:12
- 2022/04/15 19:13
- 科幻小說家X未來學家 劉宇昆與眾不同的創作之路【專訪上篇】2022/04/15 18:20
- 2022/03/12 16:06
- 2022/02/18 15:43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