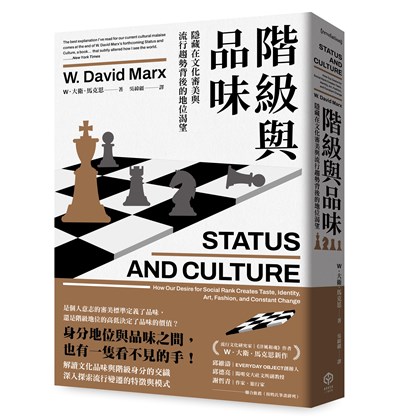
個人的審美判斷定義了品味,但人對地位的渴望也決定了品味的價值。在本書中,流行文化研究家大衛‧馬克思結合跨學科研究與流行趨勢觀察,解讀文化偏好的誕生、品味機制的運作。他注意到,在文化的運作與變遷當中,人對「地位」的追求是貫穿一切的關鍵。實際上,地位與文化緊密交織──本書企圖建立地位與文化的基本概念架構,而藉由解構地位的本質,解讀在人際互動背後的地位宣告與評估,便能發現品味不只關乎美學價值,更標示身分差異,體現的是我們選擇背後的思維及其限制與突破。
內容節錄
《階級與品味:隱藏在文化審美與流行趨勢背後的地位渴望》
我是在八歲的時候首次看到披頭四的拖把頭照片,距離他們聲名狼藉的顛峰已整整二十年。當時我住在密西西比州牛津,一個思想十分傳統的小鎮,父母仍期盼孩子回答他們「是,先生」和「是,女士」。當我看到《披頭四: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精選輯(The Beatles / 1962–1966)的卡帶封面時,我只是想,他們看起來就像我和我哥一樣。當時,牛津的大多數年輕男子都留著瀏海,跟一九六一年的史都‧沙克里夫沒有太大差別。那款披頭四髮型曾經造成國家和世代分裂,但此時就連在保守的美國南方都已非常普遍。小時候我覺得很奇怪,一個如此傳統的髮型竟然能引起那麼多責難。今天,那股憤怒看起來甚至更加荒謬。拖把頭不僅變得普遍,而且成了經典。二〇一九年,《GQ》雜誌指出,它「現在看起來和當時一樣好看」。
大多數人都知道拖把頭和它遭到反彈的故事,但這種熟悉感可能使我們忽視其中顯露的奇特人類行為。就像拖把頭和我們稱為趨勢的其他成千上萬個微型社會運動一樣,人類集體從一套任意性的做法跳向另一套,其原因難以捉摸。起初,這些微小的風格差異會引起可怕的社會摩擦——只是後來就為人所接受,包括最初的反對者在內。日後,權威人士將這些趨勢的創始人吹捧為「偶像」和「傳奇」,從此,過去的激進行為在我們共同的文化遺產中鞏固了一席之地。史都‧沙克里夫某天決定留瀏海,結果創造出一個年代的有力象徵,那個年代我們稱為六〇年代初期。
這些人類行為的特異之處可以歸納成一個更廣大的謎,我稱之為文化大謎團(Grand Mystery of Culture):為什麼人們集體偏好某些做法,然後多年後,在沒有實際理由之下,就轉向其他方案?正如《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中的殯葬業者奧默先生(Mr. Omer)所譏諷的:「流行就像人類。它們來了,沒有人知道時間、原因或方式;它們離開了,沒有人知道時間、原因或方式。」
相較之下,科技變遷就非常合乎邏輯,因為創新提供了更高的效率和便利性,而且成本更低。我們的祖先使用紡車,不是因為它是一種「流行」,而是它縮短了將纖維紡成紗線所需的時間。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變遷就顯得怪異。史都和他的模仿者希望藉由拖把頭達到什麼目的?是什麼改變了他們的品味?演化生物學和經濟學都無法解釋這種行為——拖把頭在本質上並沒有比其他造型更有價值,也無法提供更多有形的愉悅。拖把頭是不是一種自我表達的形式?如果是,大家怎麼知道這種特定的髮型表達了什麼感覺?為什麼每個人都想要透過相同的髮型,在相同的時間表達相同的情感?
與人類經驗的其他許多面向不同,對於是什麼改變了我們的文化偏好,目前仍然缺乏權威性的答案。近期有一本試圖解釋品味機制的書,最終以舉白旗投降的方式提出結論,將「隨時間而改變的情況」視為一種類似股市短期波動的「隨機漫步」(random walk)。在過去二十年中,最受認可的文化變遷理論將其描述為「病毒傳染」(viral contagion),認為我們屈從流行就像感染麻疹一樣。
但是文化變遷絕非隨機,也不像瘟疫那樣降臨在我們身上。趨勢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個人選擇採取新的行為。審視文化變遷的歷史時,我們可以發現人類從一種做法轉向另一種做法有清楚的模式。在拖把頭風行之前六十年,社會科學家孫末楠(William Graham Sumner)似乎就預測到它的興衰:「一種新的服裝潮流起初看似荒謬、不優雅或不得體。過了一段時間,這種第一印象已然和緩,所有人都開始追隨這種流行。」幾乎在所有情況下,新的行為剛開始都是小型社會團體——無論是菁英還是局外人——的專屬做法,然後最終擴散到更廣大的群眾。這一點對外在髮型的擴散是如此,對不被視為「流行」的事物同樣適用:像汽車和雜種種子玉米這樣的實用科技、像巧克力和琴酒這樣的美食、政治和精神信仰,以及現代藝術中藝術運動的演替。我們所謂的文化始終是個人行為的集合體,而如果品味僅僅是隨機習性和非理性心理的產物,那麼文化就不會展現出任何模式,只有噪音。這些不同領域的偏好都遵循類似的變化節奏,可見其中必定存在著人類行為的普遍原則——有一種「文化重力」(cultural gravity)將人們同時推向相同的集體行為。
儘管文化變遷經常被視為膚淺,但它對我們人類的生活經驗卻至關重要。它界定了我們的身分,並決定他人如何對待我們。我們每天都必須做出選擇,是遵從社會標準還是「做自己」。我們在不知不覺中發覺某些事物很「酷」。我們將文化變遷的標誌當作檢驗過往的標準,比如尷尬的髮型幫助我們確定舊照片的年代。披頭四不僅僅是一個樂團——他們是那個頂著拖把頭的樂團。正如我們將在這本書最後看到的,流行解釋行為變遷的能力超出了我們願意承認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