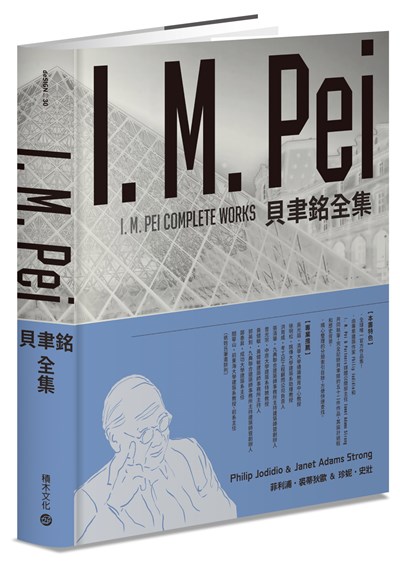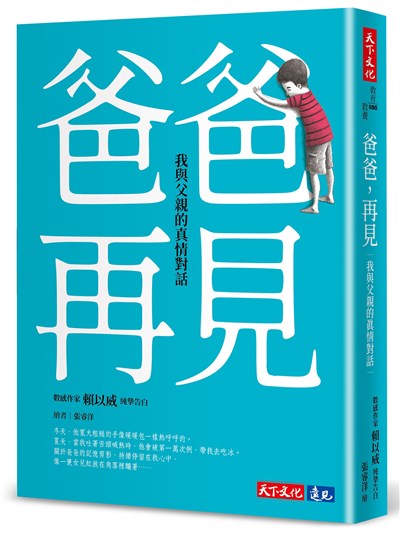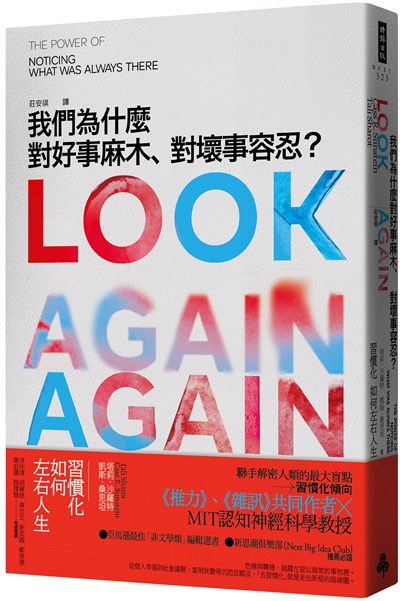繼「植劇場」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創造驚人佳績後,電影《花甲大人轉男孩》上映,再掀熱潮。《花甲大人轉男孩生產紀實》收錄兩位導演、六位演員、四位編劇的心得日誌,以及花甲盧廣仲、花明劉冠廷與兩位導演的心靈對話,並收錄電影版場景再度升級的美麗場景照,將鄭家人的喜怒哀樂哭笑嬉鬧瞬間停格,為讀者留下感動與回憶。
文章節錄
《花甲大人轉男孩生產紀實》
花的詢問─楊富閔
如果花詢成人長大,他將擁有一個怎樣的人生?花詢在影集當中出場次數不多,每每牽動我的心緒,或者他與小說原著密切連結的關係,也可能你我心中都住過一個花詢──
記得花甲阿瑋隨著四叔坐上繁星五號,行星一般繞著鄉村社區展開報喪之路,花詢形貌初次輾轉從花甲口中說出:一個從小就過世的堂弟。而在校車同學會上,花明來到花詢喪命現場,一句阿詢上車,則讓花詢死亡焦點從四叔自身一家,漣漪般擴散到了整個鄭家上下。原來這是四叔的心事,也是大家的心事。我們其實都在年歲相當稚嫩之際,多或少就經歷了死生的課題,然而花詢的問題更在,那是一個早夭的孩童,於你我仍急速發育的少年階段,一句話都沒道別就消失的幼小生命──他們沒有長大。
孩童如何面臨孩童的死亡呢?到現在仍記得一九九三年夏天得知堂哥意外,消息是在中午時間抵達臺南老家,整排樓仔厝其實都是自己親戚,其中一戶在給人開車,立刻義務成了司機。印象中家中所有老輩都趕去了,阿嬤、嬸婆以及當時不知孫兒其實早已亡命的伯公伯婆,一車子加起來三百歲的老大人,慌慌亂亂要去看一個十二歲不到的小男兒。而我奉命留在山村獨自守著這個謎似的秘密,全身顫抖坐在客廳,不敢告訴任何意圖前來探聽的鄰人。
家裡當時掛滿許多堂哥送我的布偶,每隻吸盤我都使盡力氣,逐一附著在我的床頭,他是夾娃娃機的高手,事發之後所有布偶母親都將他取下,至今我仍不知他們下落。我記得有隻長得很像堂哥,事發期間我在家不停重複這句話,這句話最後被阿嬤拿去當成安慰大家,聽到的人都輕輕地笑了。這是二十年前的事。
二十年來這支早逝隊伍不斷整編拉長:病故的,車禍的,戲水的,無來由的⋯⋯而我是否曾經就要走進這支隊伍?比如小學二年級從美容狂奔回家的路上,與一臺從窄巷速度不快的機車迎面撞上,真的是迎面,不知為何毫髮無傷,我還跑得更快;或者小學三年級在奮起湖走山路,自得其樂走太快,前後無人,一時腳底打滑,抓不到護欄繩索,差點滾落山谷,卻沒有告訴任何人⋯⋯原來我們都是好不容易才活到了現在。
我想像花詢過世,得以參與他的喪禮的,恐怕只是他的同輩手足,也就是花甲花慧,花明花亮,他們經歷怎樣的一個童年呢?那又是一場怎樣的小喪禮?花詢是大家共同擁有的一個堂弟,想必也曾嬉鬧在鄭家祖厝院埕,是四叔四嬸唯一的孩子,他會是手足間最能念書的嗎?
影集中花詢出事的那場放課戲碼,後來我們也才知道,差一點點他就活下來了──獨自走在馬路的他,短暫與接送花甲花慧的阿嬤相逢。阿嬤的臺灣國語:阿詢你為什麼在這裡啊?這句話是不是阿嬤最後跟花詢說的話?可以想像放學時間,就讀同所學校但分屬不同年級的花字輩,各自被家長接走了,校門口於阿嬤而言,到處都是阿嬤的子子孫孫,放學時間就是家族時間:猜測花明花亮被任職農會的母親接走了,花詢該是與父母一同坐轎車上下課的,而阿嬤負責接送地是平日照養的花甲花慧。花甲懊悔那日沒有堅持四貼,沒有堅持的也許還包括阿嬤與花慧,花詢也是阿嬤的金孫,這個遺憾相當深刻,它緊緊揪住了我。
實則花詢的故事在劇中先是從繁星五號的報喪之路講起,然後才是雅婷突然動念的同學會,一行人浩浩蕩蕩坐上四叔的校車,陪他完成一趟又一趟的尋子之路,然而失散的豈止是父子,更是四叔自身與自身的距離,正隨時間流逝而不停擴大,而日日重複走上的村路與臨停的站別,成為了自我救贖的一體兩面:他是要繼續這種狀態呢?還是逸離這條軌跡另闢路線,海邊的水戲為此留給我們更多揣想空間。
陰錯陽差地我也成為了車上一員,化身花甲花明的同學,共同守著花詢的秘密。去年冬天回到大肚山,這片大學時期我就極熟悉的紅土地,不曾想過有天我會因著自己作品回到這裡。〈繁星五號〉其實也是在紅土地完成的,當時住在東海別墅三弄底的小宿舍,舊屋重新裝潢的學生套房,價格當時算是偏貴,我開始寫作,多夢睡得不好,一邊專注閱讀,同時遊魂般天天繞著大肚山騎車晃蕩。為什麼會有這篇小說已經記不得,然而多年來大量仰賴交通工具,生活總在移動之中卻是可以肯定的。無論是幼年時期的興南客運,或者中學六年的通勤生活,大學生涯的綠色統聯⋯⋯我想起小時候一有遊覽車出入村莊,總會引起騷動的,它象徵著某趟等待前往的旅程,而我是不是好想逃離山村呢?特別是中學時期,日日搭乘外包的遊覽車從大內出發、歸返,整整六年⋯⋯不同的路線述說著不同的臺南故事,到現在我也清楚記得校車上你我少年時期的長相,同時也就想起臺南清晨日暮的長相。
只是再次坐上校車,我們都已不是青少年了。記得拍攝當日,親睹繁星五號出現我的眼前,簡直不敢相信:我該如何面對這輛被我創造出來的虛擬校車,刻正它經由專業規劃,實體活跳出現在我的眼前;不敢相信還包括我要與它一同向前,穿越在小說、戲劇、人生之間,也就無法判斷當下置身的這個時間與這個空間──印象中呆坐在校車上,內心問了自己一個問題:這也許只是一場戲,但我將被載去什麼地方呢?
沒有要去什麼地方,只是收工最後很幽默地順道送我到烏日坐高鐵,這是戲外的插曲,聽說明天一早它就會回到服務的學校,開始一路又一路接送孩童上下學。記得在車站目送校車駛離,體會到寫作為何如此神奇,這趟只為我私闢的特殊路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或者校車也並非僅是帶我來坐高鐵,這躺車途早在多年前離開大內便已展開,它已帶我繞了好大一圈:從臺南走到了大肚山,又走到了臺北,如今它從臺北折返回大肚山,最後又帶我回到原生的故鄉大內。繁星五號是不是常隨我的左右呢?它像是一則隱喻,它是我的秘密武器,始終在我身側,而車上靜靜坐著來不及長大的花詢。
車與花詢都要我勇敢向前,頭也不回去一個不知遠不知深不知黑的所在,一個有光有花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