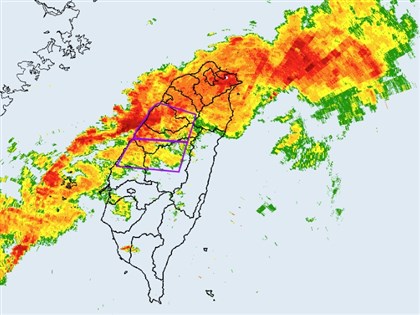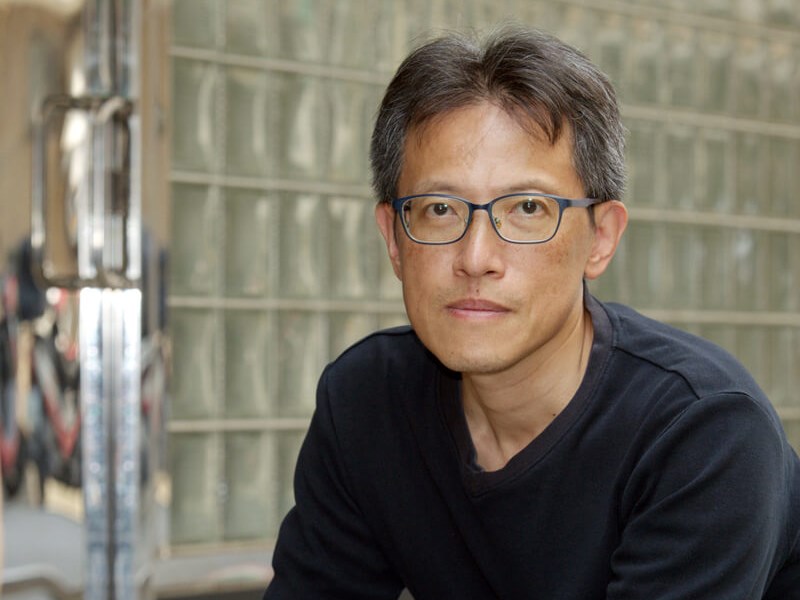余英時回憶錄搶先讀:信仰共產主義者 常是出於誤會
(中央社網站30日電)享譽國際的史學家余英時,終於出版回憶錄。這本回憶錄前後費時12年,細述余英時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他多年來堅持反共、平反六四事件,不因任何利誘而動搖。站在學術界的高位,他對共產主義和共產中國的認知、解讀值得一讀,新書還未正式開賣,就在網路書店預購榜名列前茅。中央社帶您搶先一讀。
以下是「余英時回憶錄」書摘內容:
表哥對共產主義信仰虔誠 成余英時「啟蒙者」
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的理論是在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1947年年底,瀋陽已在共軍包圍之中,我們不能不離開。在北平住了11個月(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華北局面又重蹈東北的覆轍,於是全家又離開北平,流亡到上海。但在北平這11個月期間,我失學在家,無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來往,因此才接觸到當時最敏感的思想問題。我又愛讀當時一些流行較廣的期刊,如《觀察》、《獨立時論》、《新路》之類,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論題,詳情留待後面再說。
回憶1948年在北平的思想旅程,我必須特別提到我的表兄汪志天。他比我年長10歲,當時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三年級。其實我們早知道他在1937年前後便已參加了共產黨的「少年先鋒隊」。1949年以後,我才發現原來他是中共的地下黨員,而且是北大地下組織的負責人。北平的學潮都是他和他的「同志」共同發動起來的,不過每當大批學生在街上示威遊行時,他卻從不參加,往往在我們家中吃茶聊天。我們當面戲稱他為「職業學生」,他也付之一笑。1946年在東北時,他也常往來於北平與瀋陽之間,名義是「跑單幫」,買賣西藥,賺一點錢奉養他的老母親(我的姑母)。
我記得他在瀋陽時,常常約朋友多人到我家聚會,在大客廳中關起門來談話,一談便是3、4小時。1949年8月,我回北平時,他才告訴我當時在我家開會的都是黨中重要的地下領導人,因為當時北平風聲很緊,保不住身,因此轉移陣地到瀋陽活動。但他是一個很懇切的人,確有一股為中國尋找新方向的熱忱,因此我很尊重他。我覺得他對我們一家(他的舅舅家)有真感情,並不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生任何芥蒂。我還記得1948年暑假,他帶著我和另一個年輕的親戚作三天三夜的近郊遠足,從城中徒步走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等地。我們都沒有錢,各人背著一條毯子,隨時在風景區露宿。那是一次很愉快的旅行,今天回想還像是眼前的事。
汪志天是最早向我灌輸共產主義理想的人,他的信仰是很虔誠的。由於我們之間互相信任,我很尊重他的看法,因此才開始研讀並思考種種流行的思想流派。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便是他介紹給我的。就這一意義說,他是我的一位「啟蒙者」。但俗話說:「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同時也願意接受某些涉及全體人民生活的大企業(如鐵路)應由國家經營,但是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當時許多人都討論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四大自由」,我是完全同意的。
共產主義實踐者選擇信仰 全是一場「誤會」
但在我和表兄的思想交流過程中,我發現他並不屬於非常激進的一群。例如對於他的校長胡適,他並不像多數左傾學生那樣一味譴責,有時也能持平看待。他當然責難胡適親美,但胡適在1947年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他卻不只一次加以稱許。
另一方面,在企圖說服我接受他的一套信仰時,他也偶然使用辯證法、唯物論的思想武器。然而,他畢竟只是一位實踐者而不是理論家。我記得他有一次向我宣揚「宇宙一切皆變」的「真理」。我問他:這條「真理」也應是宇宙間之一事,它本身變不變呢?他冷不防有此一問,便很坦率地說,他的理論修養還不能立刻對這個問題作出滿意的回答。這是他「不知為不知」的具體表現,但我也因此悟到:他的信仰並不建立在理智的認識上,甚至可以說,他對「共產主義」的整個體系實在不甚了了。若再參考和他同時代的黨內知識人的例子,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後有了新的覺悟,也無不異口同聲地說當初對信仰的選擇多少不免出於「誤會」。
1949年8月,我從上海回到北平燕京大學時,表兄已是市長彭真手下的一個重要幹部,負責全市青年的組織和活動,經常到各大學和黨、團機構聯繫。有一次他到燕京大學,順道訪我而未晤。事後有人告訴我:項子明同志今天找你不到,他說是你的親戚。我初聞「項子明」之名,為之茫然。幾分鐘後我才省悟,原來這是表兄的黨名。但這時他已成忙人,我再沒有機會和他深談。後來在文革初期,海外報刊有關於所謂「北京暢觀樓事件」的報導,記述了他反對毛的言論。不用說,他必已變成了「革命」和「專政」的對象。
表哥對早年信仰動搖 價值觀回歸源頭「孔子」
我最後一次和他聚會是在1980年代初的紐約。那時他以北大代書記的身分到美國訪問各大學,在西岸的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東岸的哈佛大學都受到隆重的接待。由於事前約定,我們在紐約暢談了兩天,這是分別30多年以後的重晤,彼此都不勝感慨。這次他雖然是官式訪問,所到之處皆獲禮遇,但他的意氣卻相當消沉。
在談話中,我終於發現,他在文革後並不受中央領導人的重視,北大已是一個冷衙門,何況他還只是「代書記」。但更重要的是,他對早年信仰顯然已發生根本的動搖。他自己沒有說過一句悔恨的話,但他的夫人(早年也是一位真正的信仰者)很率直地對我說:「你們(主要指我的父親)看得遠,幸而早出來了。」他在一旁也默認了這個說法。我不願再深入挖掘這個問題,以免觸及他的傷痛,而一切都盡在不言中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們到紐約唐人街去吃飯,途中經過一座很大的孔子銅像。他看見了,忽然十分興奮,一定要和我在銅像前留影,作為紀念。在他早年信仰誠篤的時期,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然而他確是出於內心不可抑止的一種衝動。
很顯然,在早年的信仰徹底幻滅之後,他的價值觀似乎向兩個源頭回歸:一是「五四」以來流行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民主、自由。這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他所參加的「革命」最早本是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以吸引知識青年的。二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主要表現在對於人的尊重。這是他對孔子抱有很深敬意的根本原因。(書摘摘錄自「余英時回憶錄」,余英時著,允晨文化授權)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