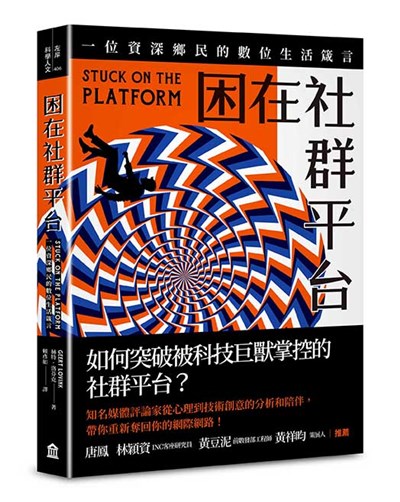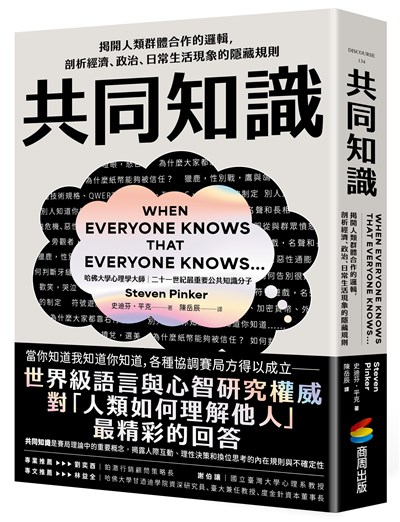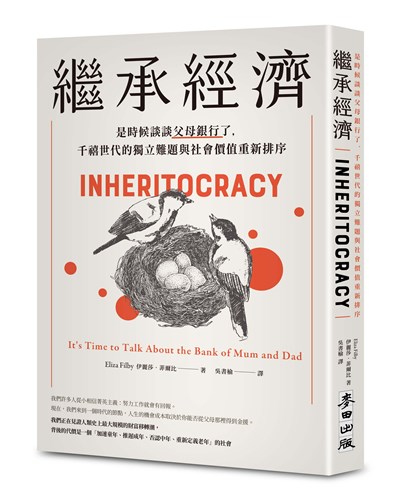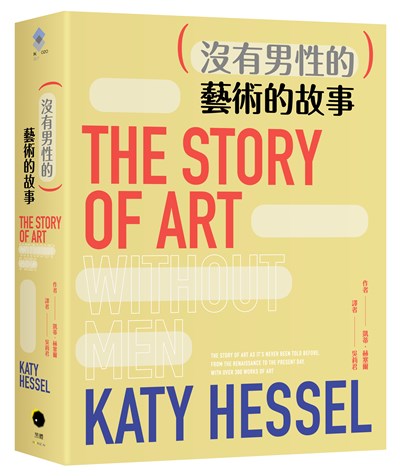
藝術史家凱蒂.赫塞爾在IG社群平台創立了@
內容節錄
《(沒有男性的)藝術的故事》
第四章
戰爭、認同與巴黎前衛
「我不認為有任何男人曾以平等態度對待女人,而平等正是我的要求──我知道,我的價值不亞於他們。」
──貝忒.莫里索,1890
1874年,一群脫離沙龍展傳統和絲滑學院美學的藝術家出現在巴黎,人們用印象派(Impressionists)稱呼他們。這群藝術家以一場徹底顛覆藝術體制的展覽登上舞台。他們獨立辦展,而且辦在不同於沙龍展的另類空間裡,第一次是一間前攝影工作室。這群藝術家創造出一種革命至極的風格,至極到隨後的一切都無法不將它考慮進去。
隨著鐵路出現和周遭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印象派藝術家努力捕捉轉瞬即逝的「印象」,而非靜態、固定的影像。他們拒絕位居高端的歷史畫,轉而從事小規模創作,從當代生活中擷取主題。他們偏愛繁忙的巴黎戶外生活〔經常在「戶外」(en plein air)作畫──這得感謝當時剛發明的管狀顏料,讓藝術家不必被綁在工作室裡〕,他們打破以往的現實幻象,利用充滿光線、一閃而過的小色塊,傳達生活在這個令人興奮的嶄新世界裡的節奏步調。
事實證明,對女性而言,印象派是個既有利又限制的運動。1870 年代時,藝術教育依然僅限於有能力聘請私人教師者,而社會習俗也阻止中產階級女性在沒人陪伴的情況下上街閒逛。反之,男性則可流連於酒吧和咖啡館,到遠方旅遊,隨心所欲地畫他們喜歡的主題。酒吧和咖啡館變成他們筆下的重要主題,以及聚會碰面的場所──位於蒙馬特的蓋爾布瓦咖啡館(Café Guerbois)和新雅典咖啡館(Café Nouvelle-Athènes)尤其受到青睞。印象派女性藝術家則不然,她們只能畫一些閨房和家庭領域的個人經驗與視角。貝忒.莫里索(Berthe Morisot , 1841-95)就是將這些場景發揮到極致的藝術家之一。
莫里索透過她與上層階級女性的交往,以生動親密的角度捕捉到她們的私密世界,哀嘆她們缺乏獨立,但也歌頌她們的小自由。莫里索是1874年第一屆印象派大展唯一的女性參與者,她的繪畫事業蓬勃發展,在印象派1874到1886年間所舉行的八次展覽中,她有七次展出作品(唯一一次缺席是因為女兒出生後她病倒了)。她以快速、輕盈、時而粗糙的筆觸和主題備受讚譽,描畫的範圍從家庭生活到時尚的中產階級。就主題而言,我認為《斜倚的灰衣女子》(Reclining Woman in Grey , 1879)是她最精彩的傑作之一,這張畫布因為邊緣的隨意留白看似尚未完成,卻將我們帶進一片由幾乎無法控制的銀白碎形所構成的海洋。雖然我們是在室內場景看到這名女子,但她表情活潑,散發出的溫暖與光輝,在在暗示出現代女性日益提升的自信與獨立。而莫里索筆觸所呈現
的速度感,也複製出現代性的步調──彷彿我們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捕捉到這位主角的一抹神采。
莫里索出身巴黎中上階級家庭,她與姊姊愛德瑪(Edma)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藝術才華,她們得到雙親鼓勵,為她們聘請了好幾位優秀導師。其中一位驚訝(且驚嚇)於兩姊妹的才華,並做出這樣的報告:「你們的女兒很有這方面的興趣,我的教學不僅能讓她們用才華取悅別人,她們甚至能成為畫家。你們知道這意味什麼嗎?在你們的環境裡,這將是一場革命,或一場災難。」
這兩位年輕女子渴望獲得進一步的機會(而且顯然並未因即將來臨的「災難」感到困擾),持續接受當時一些傑出藝術家教導〔例如卡密爾.柯洛(Camille Corot)〕,到了1864年,兩人已獲准在知名的巴黎沙龍展出。愛德瑪雖然早年相當成功,但在1869年因結婚而被迫放棄她的藝術追求。莫里索在同一年繪製的《窗前的藝術家姊姊》(The Artist's Sister at a Window)中,捕捉到姊姊對自身困境感到悲傷。從敞開的窗戶可以看到對面陽台上正在交談的人物,她利用這樣的室內角度,讓我們留意到那些社會藩籬,它們不僅束縛了身為女人的姊姊,也框限住她做為藝術家的角色。
幾年後,莫里索在第一屆印象派大展中出道,展出姊姊的另一幅肖像,《搖籃》(The Cradle , 1872)。評論家瞧不起莫里索描繪愛德瑪和她的新生兒,說這是一幅歌頌母職的「甜」畫,但這件作品的意義遠不止於此。這幅畫同時充滿了緊張與溫柔。愛德瑪看起充滿愛意地凝視自己的孩子,但她深思熟慮的姿態,以及將這兩位人物分隔開來的那條對角線,似乎都在暗示身為母親的複雜情感(畢竟,她被迫為了這個新生命放棄她的藝術)。和歌頌母職的刻板圖像相反,愛德瑪挑選的時尚服飾(一件蕾絲鑲邊的白色襯衫,配上緊身條紋外衣,還有一條黑色頸鍊)透露出,她依然努力想活出現代女性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