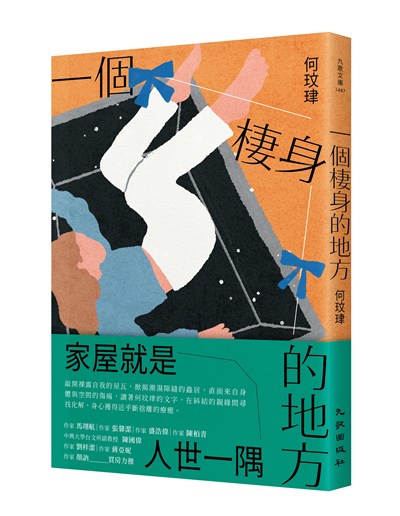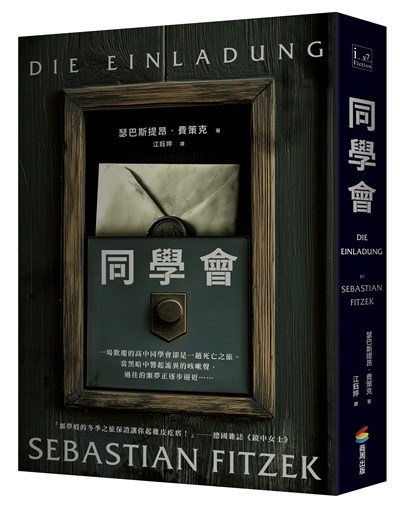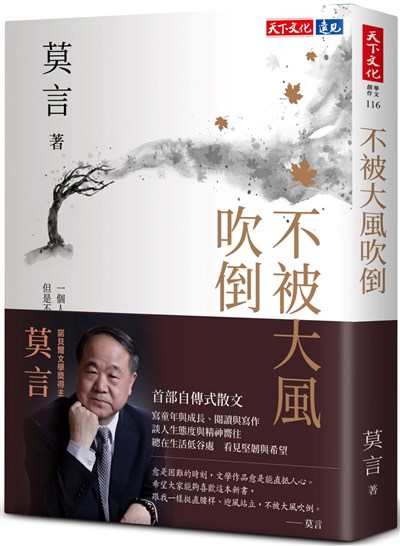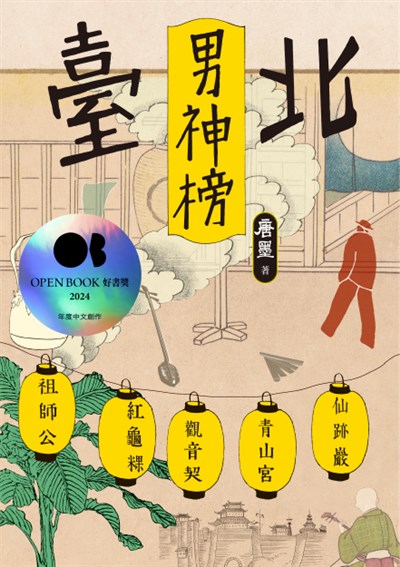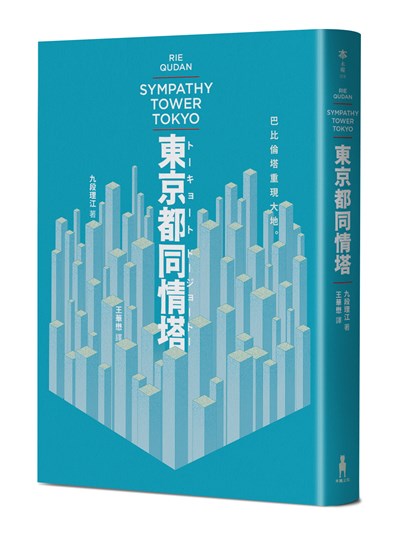
2030年,一座新式受刑人收容所「東京都同情塔 𝙎𝙮𝙢𝙥𝙖𝙩𝙝𝙮 𝙏𝙤𝙬𝙚𝙧 𝙏𝙤𝙠𝙮𝙤」建成,以「罪犯應當被同情」為理念的高級設施聞名。
女建築師牧名沙羅,集完美專業於一身,卻對人工智慧共處的社會感到格格不入,更苦惱於這座塔的寬容信念和語言錯亂。年輕的高級服飾店員拓人在被沙羅搭訕後,兩人開啟一段難以定義的曖昧情誼。建築、文字、性別、犯罪、同情,以多元面向的議題交織成的壓倒性作品,獲170屆芥川獎肯定。
當AI共處成為日常,哪個才是你真正的意志?
內容節錄
《東京都同情塔【170屆芥川獎得獎作】》
我有自信比任何人素描得更正確,也是班上最快學會寫漢字的學生。但是寫起片假名,我再怎麼練習就是寫不好。連小學生和外國人都寫得比我好。事務所的同仁更批評「就像精神異常的連續獵奇殺人魔的筆跡」。我絕對沒辦法和發明片假名的人把酒言歡。片假名就是一條條毫無美感與尊嚴的乏味直線,內容空洞,卻身具「足以包容任何國家的語言」的厚顏無恥。我怎麼可能喜歡這種只要抽掉一根,就立刻垮散成一堆棒子的結構物。來自生理上的極度嫌惡,就這樣無可避免地扭曲了我的片假名字跡。幾年前在東京獨立開業時,要不是建築夥伴為了在國際競圖中容易辨識,強推「サラ・マキナ・アーキテクツ(SARA MAKINA Architect)」這個名稱,我應該會將事務所取名為平凡的全漢字「牧名沙羅設計事務所」吧。我不想輕易增加書寫片假名的機會。
單親媽媽=シングルマザー(Single mother)。伴侶=パートナー(Partner)。非二元性別=ノンバナリー(Non-binary)。外籍勞工=フォーリンワーカーズ(Foreign Workers)。身心障礙者=ディファレントリー・エイブルド(Differently abled)。多重伴侶關係=ポリアモリー(Polyamory)。犯罪者=モホ・ミゼラビス(Homo miserabilis)……我將這些猶如荒廢工寮的文字扔進冰涼的礦泉水,含在口中滾動著品味。
使用外來語替代原有的說法,有時單純是因為更容易發音或更簡略,有時則著眼於降低不平等或歧視的感受,以及語感上較委婉,不易引發衝突。不確定的時候,就先借個外國詞彙來擋一擋。神奇的是,通常都能圓滿地蒙混過去。
這麼說來——我想起設計埼玉音樂廳時的事。事務所內針對音樂廳空間設施的規畫提出各種方案時,我將設計圖中所有性別都能使用的廁所區域註記「全性別廁所」,檔案分享出去後,卻立刻被修改成「ジェンダーレストイレ」(Genderless toilet)。似乎是最年輕的助理修改的,她——當時是他——在Slack 留言:「不合時宜,不夠嚴謹、洗練,而且不尊重當事人。」但我只是因為不想寫片假名,又為了和「男廁所」、「女廁所」統一,才使用「全性別廁所」罷了。導致我後來都得寫上長長的「ジェンダーレストイレ」,空間有限時,還得將一長串片假名寫成密密麻麻的。不過,相較於無性別者遭非其族類毫不尊重地歸類為「全性別」所遭受的痛苦,留意文字大小、忍耐著書寫討厭的片假名,根本算不上痛苦。不應該對此感到痛苦。從未猶豫過該走進哪一邊廁所的我,不論廁所採用怎樣的名稱,都不會為此受到傷害。不應該受到傷害。
那麼,「Sympathy Tower Tokyo」這名稱又如何?
我離開了無法攤平整本素描簿的飯店小書桌,躺到床上,無奈地深呼吸長嘆了一口氣。床上的筆電隨著呼吸傾斜,我召喚小警總,在腦內召開命名會議。總之得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實在無心工作。
比起——比方說「監獄塔」(我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競爭候補名稱),這是更合時宜、更嚴謹、更洗練、更尊重當事人的命名嗎?站在平等的觀點,我不認為兩者有太大的差異。那麼,發音呢?「監獄塔」的音節更少,也更朗朗上口,但終究只是感受的問題。說起感 受,漢字容易予人嚴肅的印象,用作地標的確少了幾分親切感。但考慮到建築物的用途,不就是該採用多少「嚴肅」 點的名稱嗎?——甚至應該要更有「分量」、「威嚴」才對——這是身為昭和世代的我最直白的感想。說不定一九五八年當時生於大正、明治年間的日本人,也對「東京Tower」這個名稱有著類似的不協調感。那麼,這或許表示我對未來的預見還不夠充分吧。
對命名如此執拗地吹毛求疵,連我都感到很不尋常。畢竟我既非語言專家、文案大師,也絕非民族主義者。當然,我也沒有服刑中的友人。幸好——對於稱此為「幸好」,目前我還沒有任何疑慮——我這輩子奉公守法,從未接觸過任何犯罪或罪犯,對於這次的塔興建案,也並無明確的立場。我也不是非得將自己的觀點大肆公開在Twitter——「Twitter」好像改名了,現在叫什麼去了?——不可的意見領袖或知識分子那種人。在此脈絡下用「那種人」恰當嗎?不然要叫什麼?
總之,我所思考的是容器。容器的形狀、結構、材質、預算、工期。容器裡要放進什麼東西、注入什麼思想,那是別人的工作,是社會的問題。我是建築師,不需要管那麼寬。
話說回來,從單純的詞彙任意感受到輕重軟硬這些只存在於想像中的觸感,還覺得受到傷害,實在很不尋常。
「可憐的,
值得同情的,
Homo miserabil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