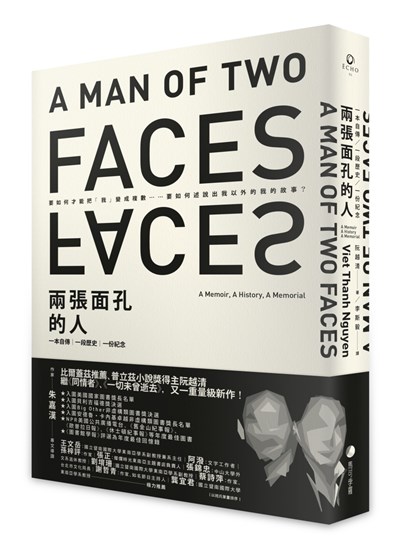在人類戰爭史上,沒有任何一場軍事行動的前24小時會像1944年6月6日這一天那樣關鍵。這一天記錄的不是戰史,而是人的故事。本書絕大部分內容取材於紐奧良大學艾森豪中心,從參與D Day諾曼第登陸行動的軍人那裡搜集到的口述及文字歷史。該中心有超過1400份個人經歷的口述歷史紀錄,這是目前對單一戰役最詳盡,以第一人稱記錄親歷戰鬥的紀錄。
文章節錄
晚上十點,諾曼第夜幕低垂,各個海灘的卸載工作停了下來。通過海空運輸,有將近一七五萬名美、加、英軍官兵在諾曼第登陸,傷亡人數約四九○○人。從右翼的美軍空降部隊到左翼的英軍空降部隊,諾曼第戰場寬九十多公里。在猶他灘頭的左翼與奧馬哈灘頭的右翼之間,有一個十八公里的缺口(拉德的突擊兵在兩翼間的霍角奪取了一小片地盤),在奧馬哈灘頭與黃金灘頭之間,有一個十一公里缺口,在天后灘頭與寶劍灘頭之間,缺口有五公里寬。這些缺口無足輕重,因為德軍沒有可以利用這些機會的部隊。
對德軍來說,戰場是孤立的。關於這一點,隆美爾完全正確,盟軍的制空權使德軍很難將兵力、戰車和大砲急速調遣到戰場。對盟軍來說,無數的兵力、戰車、大砲和補給就在不遠的海面上,天亮就能卸載,在這後面,有更多的兵力、戰車、大砲和補給正在英國準備橫渡海峽。
包括天后在內,幾乎沒有什麼縱深的突破,沒有任何地方超過十公里,而在奧馬哈,甚至不足兩公里。然而在所有地方,盟軍都已突破了「大西洋長城」。德軍仍然擁有打防禦戰的優勢,特別是在柯騰丁,灌木叢為他們提供了現成的陣地。但是在反攻的最前線,他們的防禦工事、他們的機槍掩體和地堡、他們的戰壕體系、他們的交通、他們的重型大砲陣地卻全面崩潰,僅有為數很少的例外。
德國人構築大西洋長城耗費了四年時間,他們傾注了幾千萬噸混凝土,又用幾百萬噸鋼筋加強,他們挖掘了數百公里的戰壕,佈設了數百萬顆地雷,鋪設了數千公里的鐵絲網,他們設置了數萬個海灘障礙物。這是一項巨大的建築工程,耗費了德國在西歐相當大比例的物資、人力和構築能力。
在猶他灘頭,大西洋長城阻擋美軍第四師不到一個小時;在奧馬哈灘頭,美軍第二十九師和第一師耽擱了不足一天;在黃金、天后和寶劍灘頭,對英軍第五十師、加軍第三師和英軍第三師造成大約一小時的延誤。由於大西洋長城完全沒有任何後備力量,所以一旦被突破,即使只是一公里,就會立刻變得毫無用處。更糟糕的是,因為有了大西洋長城,德軍在反攻區東面和西面的部隊喪失了機動性,無法火速調往槍聲響起的戰場。
因此,「大西洋長城」必定會被認為是軍事史上最重大的錯誤之一。
盟軍也有錯誤。午夜空投美軍第八十二和第一○一空降師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肯定地說,要是在天亮執行會好得多。盟軍轟炸機和艦隊是巨大的資源,但時間太短命中率太差,在反攻前的轟炸未能充分發揮效果。一心一意集結兵力搶灘登岸並粉碎大西洋長城或許是必然的,但那些固定防禦工事是如此難以對付,完全等待步兵將它突破,代價十分慘重。這還使官兵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一旦越過大西洋長城,任務就已完成。他們本該趁德軍暈頭轉向時狂飆突進,深入內陸,但他們卻停下腳步為自己慶賀,沏上一杯茶,挖壕隱蔽。
盟軍未能使人員和裝備做好對付在灌木叢後面德軍的準備。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盟軍的情報單位查明了德軍工事的位置,這件事做得非常出色,他們還摸清了德軍駐防諾曼第部隊的位置,這即使不算完美,也是瑕不掩瑜。然而,情報單位完全沒有理解在灌木叢作戰的困難。
盟軍的錯誤與德軍的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後者意圖防守每一個地方,結果無法防守任何地方。他們的指揮結構非但沒發揮作用,反而是在礙事。隆美爾的構想是把反攻擋在灘頭,倫德斯特的想法是在內陸組織反擊,而希特勒介於兩者之間,這使他們無法有效地利用資源。用波蘭人、俄羅斯人和其他戰俘修築工事還合乎情理,而給他們穿上德軍制服,將他們部署在戰壕之中,希望他們頑強抵抗,則是愚蠢的行為。
德軍固然有許多錯誤,但德國空軍犯的錯誤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根本就沒有出兵。戈林要求德國空軍在D日全力以赴。可實際上,他一架飛機也沒有得到。盟軍最擔心戈林將每一架能飛的飛機都投入作戰,對大量的艦船和擁擠的海灘實施大規模轟炸。而戈林正在貝希特斯加登,附和希特勒基於私利的荒謬斷言。希特勒說盟軍已在他預料的準確地點反攻,而此間德國空軍不是在德國,就是在重新部署,或是由於管理與燃料問題停飛。曾經在世界上令人懼怕的德國空軍,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成了一個歷史上的笑柄。
德軍海軍也如出一轍。他們的潛艇和巡洋艦或是龜縮在地下船塢,或是遠在北大西洋狩獵船團。除了幾艘摩托化魚雷艇做了一次小規模的行動外,德軍海軍未對有史以來最龐大的艦隊發動過一次攻擊。
希特勒寄予厚望並傾注了大量德國技術和建造能力的V—1火箭,尚未準備就緒,它們是在D日一星期後才準備好的,希特勒又將V—1發射到了錯誤的目標。
德軍在戰術上和戰略上的錯誤都非常嚴重,但是他們最大的錯誤是政治錯誤。雖然每一個人都仇恨共產主義,但他們在波蘭和俄羅斯的佔領政策,使東方營不可能對他們的目標懷有絲毫的熱情。儘管德軍在法國的行為比他們在波蘭和俄羅斯的要好得多,但也沒有激起法國人對他們目標的熱情。因此,德軍無法從被佔領的法國的巨大潛能中獲利。本該成為德軍資源的法國青年,成了盟軍的資源,他們不是在工廠搞破壞,就是當了反抗組織的成員。
希特勒被視為德軍最大的資產,作為第三帝國的領導信條,是指望德國國防軍從陸軍元帥到二等兵的絕對服從,而在D日,這個信條也不利於德軍。
儘管有極為勇敢的個人,也有一些狂熱的部隊,但國防軍的最高領導層、中層軍官和下級軍官卻表現得非常被動。原因很簡單:他們害怕率先行動。他們寧可等待和執行愚蠢的命令而陷於癱瘓,也不願意承擔責任。而那些命令從遙遠的地方傳來,與戰場上的局勢毫不吻合。戰車部隊的指揮官們知道敵人在何處,知道應該如何攻擊敵人。但在那天,他們始終坐在指揮部裡,等待著在貝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統帥的命令。
像小羅斯福和科塔將軍、坎漢和奧特韋上校、霍華德少校、道森上尉、斯波丁和溫特斯中尉那樣的人,果斷地處理意外情況,與德軍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為民主而戰的人,能夠對危機作出迅速的決策與行動;為極權主義而戰的人,則做不到這一點。除了海特上校和個別的尉級軍官外,很少有德軍軍官對D日的挑戰作出適切的反應。
隨著夜幕落下,岸上的盟軍部隊就地防守,而盟國空軍返回英國,盟軍艦隊為德國空軍可能進行的夜間襲擊做好了準備。夜襲發生於晚上十一點,這凸顯出德國空軍完全沒有戰鬥力。
喬希.霍南記得當時狀況:「突然,所有的東西都開始砰砰作響,我們都過去看,原來是一架德軍的偵察機,飛得不高也不快,在海灣上空繞了整整一圈。每一艘艦艇上的每一門高砲都開了火,你一生從沒見過這樣的曳光彈、高射砲火像串串彩燈飛向天空,而德軍飛機鎮定地在海灣上空到處飛著,又繞了一圈,然後返航。」
美軍二十九師一一六團二等兵約翰.斯勞特也在現場:「天黑以後,敵軍Me109戰鬥機在整個盟軍艦隊上空飛行,從右飛到左,剛好高出防空氣球。英倫海峽的每一艘軍艦都朝那架飛機開火,無數枚曳光彈照亮天空。那個德國空軍空戰英雄對這一切卻全然不顧,甚至都沒有採取規避行動。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穿過那道彈幕的。」
在整個諾曼第前線,士兵們挖壕隱蔽。第五突擊營的約翰.拉恩在維耶維爾外圍的奧馬哈灘頭附近,他在口述歷史中說:「這時候,天漸漸暗下來,我們必須組織起來,以防德軍的夜間反擊和滲透。營部連在公路南面的一個農家小院。在這個時候,我知道了我犯了一個錯誤,我沒帶掘壕工具。
「法國的農家小院好像是用磚鋪的而不是土的。許多世紀以來,動物不斷地破壞著它,太陽不斷地烘烤著它。我根本無法挖坑,別的士兵們有掘壕工具,有幾個人要幫我挖,可是我說,不,你們先顧自己的,等你們搞定了,再把鐵鍬給我,我自己來挖。
「隨著夜色降臨,天變得冷起來,我是說真的很冷。庭院裡有一個乾草堆,我決定躺到裡邊去。我是在城市長大的,對法國穀倉庭院裡的乾草堆所知有限,但它不是乾草堆,而是個糞堆。我剛一躺到那個暖烘烘的糞堆裡,身上就爬滿了你可以想像出來的各種蟲子。我從那個東西裡出來,拍打著,擺動著,哆嗦著,拼命想擺脫那些叮人的蟲子。
「我進去農舍,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法國婦女正向火裡添柴。那是很小的一堆火。」中尉排長范李珀(Van Riper)正在那裡。「我和范李珀在身材矮小的法國老婦人旁邊,在那個小小的火堆上烤著手,度過了那個夜晚。非常激動人心的一天就這樣有些令人遺憾地結束了。」
二十九師一一六團二等兵哈利.帕利在口述歷史中說:「六月六日最後的幾個小時讓我記憶猶新。天黑時,我們不知不覺來到一片有灌木叢圍著的田地。我們又髒又餓,累極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哪裡,我們決定挖傘兵坑過夜。我們能聽到遠處的砲聲,能看到曳光彈在遠處劃出的弧形軌跡。
「我們在田地裡散開,我與中士一組,開始挖散兵坑。地面像岩石一樣堅硬,才往下挖了三吋,我們就筋疲力盡。最後,中士站在黑暗中,知道再繼續挖也沒用,就說,算了吧,帕利,咱們乾脆坐下休息一下。我們兩人背靠背坐在淺淺的戰壕裡,度過了整晚。D日就這樣結束了。」
在飛馬大橋,牛津—白金漢團把任務移交給瓦立克團(Warwickshire Regiment),約翰.霍華德率領他的人穿過夜色向朗維爾前進。傑克.貝利捨不得離開,他解釋說:「你知道,我們在那兒待了整整一個白天和晚上,我們甚至覺得這是我們的一小片領地。」
第五突擊營F連的約翰.雷維爾中尉在奧馬哈灘頭的懸崖頂上。光線逐漸暗下來時,他召喚傳令二等兵雷克斯.洛(Rex Low),指著遠處英倫海峽中的六○○○艘艦船說:「雷克斯,你看那邊,你一生中再也不會見到這種場面了。」
二十歲的二等兵羅伯特.札夫特(Robert Zafft)是奧馬哈灘頭二十九師一一五團的步兵,他這樣形容自己的感受與經歷:「我成功地到達山上,我一直走到德軍晚上阻擋我們的地方,我認為我攀上了一座硬漢嶺。」
二等兵菲力克斯.布南是一一六步兵團K連的士兵。D日,他們是各團中傷亡最為慘重的。他在結束口述歷史時說:「從D日起,我經歷了許多不幸的事情,但是在我看來,D日會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為止。我會把它帶到天堂,那是我或者是其他人經歷過最漫長、最悲慘、最恐怖的一天。
「給我一百萬,我也不會交換我的這些經歷;不過,即使是真的給我一百萬,我也肯定不願意再次經歷一次。」奧馬哈灘頭紅E分區第一步兵師十六團的約翰.艾利中士說:「在法國的第一個晚上,我是在灌木叢旁邊的一個排水溝裡度過的。我裹著半邊潮濕的雙人帳篷,疲憊極了。但是我感到興奮,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我身高將近十英尺,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已成功離開海灘到達高地。至少有一個時候,我在心裡暗想,我是山中之王。我對美國陸軍光榮傳統所做的貢獻,或許是勇敢史上最微小的成就,可是起碼有一段時間,我與連上那些非常勇敢人一起前進。」
藍姆賽將軍用下面的話,結束六月六日的日記:「我們仍必須在陸地上穩定地立足。海軍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在這一天中,來自東部特遣艦隊(英軍灘頭)的消息始終令人滿意,他們有很好的進展。幾乎沒有西部特遣艦隊(美軍灘頭)的消息,關於上岸的狀況依然令人憂慮。
「整體而言,對於這一天,我們仍然非常感謝上帝。」
還有一位軍人沒有忘記感謝上帝,他就是一○一空降師五○六傘降步兵團的溫特斯中尉。六月六日半夜一點,他乘C—47運輸機飛往諾曼第,一路上他都在祈禱,祈禱自己能度過這一天,祈禱自己不會失敗。
他沒有失敗。那天早晨,他榮獲了優異服役十字勳章。
六月六日晚上十二點,準備在聖瑪麗杜蒙特村過夜之前,溫特斯「沒有忘記跪下來,感謝上帝幫助我度過這一天,並希望在登陸的第二天繼續得到幫助」。他對自己許下諾言,假如他能夠度過這場戰爭,他就去某處尋找一個偏僻的農場,在安寧與寂靜中度過自己的餘生。一九五一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州中南部找到了這樣一個農場,至今仍住在那裡。
「他們的榮耀何時會暗淡?」丁尼生關心輕騎兵旅,我也同樣關心D日的官兵。
啊,他們勇猛地攻擊!
整個世界都為之驚歎。
榮耀他們的衝鋒行動!
艾森豪將軍以「好吧,我們走」的命令揭開了D日的序幕,最後的定論仍應由他作出。一九六四年,D日後的二十年,他在奧馬哈灘頭上接受了華特.克朗凱的採訪。
舉目向英倫海峽望去,艾森豪說:「你看這些人在這裡游泳,開著小遊艇,盡情地享受著晴朗的天氣和美麗的海灘。華特,望著今日的海灘,回憶著它昔日的樣子,似乎一切都在虛幻之中。
「但是,回憶二十年前那些使我們為之戰鬥和犧牲的崇高目標,以及那些為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而進行了殊死奮鬥的人,畢竟是一件令人感到美好的事情。不為征服任何土地,不為任何野心,只為確保希特勒無法破壞世界上的自由。
「我想這一切是勝過所有的。想想那些為了原則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這個海灘上,僅僅在那一天,就付出了兩千人傷亡的慘痛代價。然而為了世界能夠獲得自由,他們勇敢面對,這充分顯示出為了不被奴役的自由戰士寧願承擔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