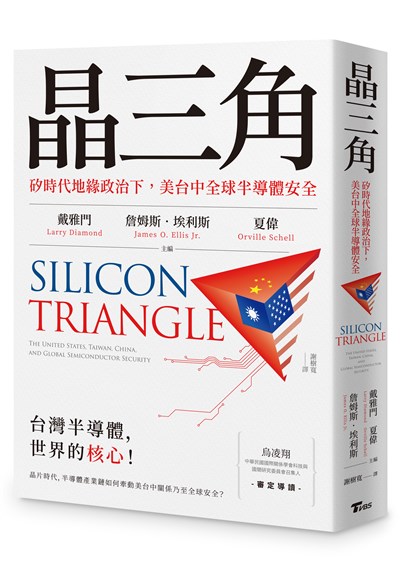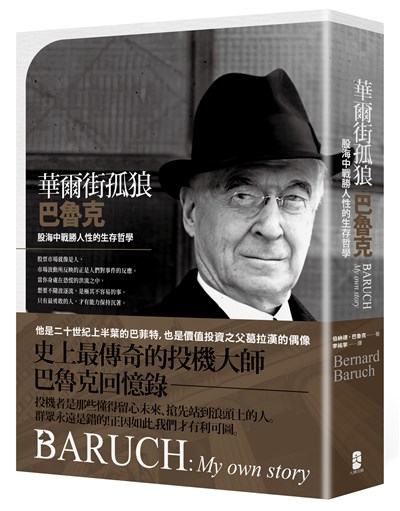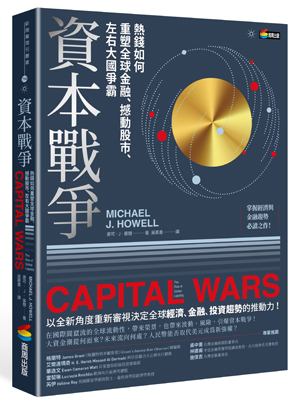
本書以全新角度重新審視決定全球經濟、金融、投資趨勢的推動力,在國際間竄流的全球流動性,帶來榮景,也帶來波動、風險,引爆資本戰爭。大資金潮從何而來?未來流向何處?人民幣能否取代美元成為新強權?掌握經濟與金融趨勢必讀之作。
本書為讀者解析:全球流動性的來源與組成;以全球流動性的觀點重新認識全球經濟與金融;熱錢對金融與實體經濟(產業)的影響;全球流動性在美中金融爭霸所扮演的角色……
這些貪婪且跨境流動的熱錢,引發了資本戰爭,並將風險——流動性不吸引人的那一面——暴露了出來。世界變得越來越大時,也變得更加波動。
文章節錄
《資本戰爭:熱錢如何重塑全球金融、撼動股市、左右大國爭霸》
歷史絕非隨機發生,尤其是金融史。本書的關鍵思維在於,經濟週期是由金融流動所驅動,也就是儲蓄與信貸總量,而非普遍認定的通膨或利率水準所致。全球流動性這座一百三十兆美元自由流淌的現金池彰顯出它們橫掃千軍的破壞性威力。由此可知,我們的中央銀行決策者應該徹底改變政策,更高度聚焦金融穩定性,而非命中虛幻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目標。英國經濟學 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區分經濟領域中金融範疇 與工業範疇的方式,與當今我們劃分資產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手法類似。試圖祭出流動性刺激實體經濟永遠都得冒著製造資產價格泡沫的風險。一九三○年代,決策者遭逢一種與後金融危機時期幾乎如出一轍的情境,當時他們釋出一套雷同的刺激方案並收到相似的後果:一般商業價格幾近持平,但資產價格一飛沖天。一個分化、不確定的世界激勵投資者緊握過剩的「安全」資產,好比現金與政府公債,尤以美元資產為甚,而非將資金投入有益生產的工作領域。當國家無法產出足夠的安全資產時,民間就推出次等替代品介入,不幸的是,它們的價值都會順週期變化。就這個角度來看,政府的緊縮政策與量化緊縮方案有可能聽起來不是那麼完善?不妨把這套機制想成所謂的預防性貨幣需求,傳統教科書只以三言兩語帶過,不過它似乎比眾所周知的投機動機更適切描述我們眼前這道日益茁壯的系統性風險,畢竟投機動機是在評估走高(或下修)的利率足以導致「流動性陷阱」的機率有多高。個人淺見主張,全球流動性永不受困:它不聲援愛國主義、深諳無邊無界,而且在市場與資產類別之間飛速移轉。
事實上,在最新的政策辯論中,有兩道看似令人費解的特徵強調全球流動性的重要性。首先,央行的反覆聲明強化一道廣泛的共識,認為更多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實則降低而非推升期限貼水(term premium),進而提高政府債券殖利率。2016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E.甘農(Joseph E. Gagnon)撰文總結學術界論點,每借道量化寬鬆挹注10%國內生產毛額(GDP),就量化債券殖利率六十七個基點。其次,許多人相信,殖利率曲線的斜率是商業週期一道明確的預測指標,因此,殖利率曲線倒掛應該是在警示我們,經濟衰退正迅速逼近。事實上,這兩套說法都不是正解。前者禁不起數據考驗,它們會清楚顯示,美國推行量化寬鬆時期與高殖利率息息相關,而且在過去的每一場量化寬鬆階段,期限貼水準均上升一百三十四個基點。另有國債殖利率當作商業週期預測指標效率的分析,好比在下2018年發表的文章。這一點證實,標準的十年期與二年期殖利率斜率充其量只是一道不可靠的預測指標。這份分析指出,因為不同的到期利差會在不同的時間發揮作用,另一道也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期限結構的曲率。在其他研究中,斜率與曲率必須一起評估,解釋曲率的一項關鍵要素就是期限貼水的模式。期限貼水是流動性現象,多半反映「安全」資產的需求過剩。
1989年,柏林圍牆(Berlin Wall)崩塌引爆的流動性衝擊像子彈一樣在世界各地彈跳,終究迫使利率下跌並協助反轉全球金融體系的極端傾向。資本順著我所謂的金融絲路(Financial Silk Road)直奔東方,政治與群眾卻移向西方,導致尤以中國為首的許多國家打著安全的名義過度倚賴美元和美國國債市場。當今的金融市場與這些變化環環相扣,越來越有必要擔綱再融資的機制,而非全新的融資機制,使得資產負債表規模這種資本的能耐遠比利率水準這種資本的成本更形重要。劣質的「安全」資產即是我採取更正規方式稱呼的影子貨幣基礎,供應量因此高漲,進而削弱民間的資產負債表展期全球金融危機時代遺留至今大筆未償付債務的能力。諷刺的是,流動性與「安全」資產的供應減少,竟然推升囤積它們的需求。這些特徵加總在一起便放大全球流動性的波動程度,也足以解釋為何世界變大的同時也更波動易變。優質資產的潛在稀少性誘使我們相信資本戰爭一觸即發。在此,戰場涵蓋資金、科技與地緣政治,外加兩股超強勢力正面對決:中國的工業與美國的金融業。中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大:2000年,中國占全球流動性僅5.9%,不到美國占有率的五分之一;2007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肆虐期間上升至10.1%;如今更暴衝至超高的27.5%,顯著超車一路下滑到22.5%的美國。中國對全球經濟與全球金融而言至關重要,我歸納的結論是,雖說美國有必要重振自家工業,中國盡快發展自家金融業的必要性卻更形迫切。正如歷史所示,這些都是演變過程而非單一事件,但我們還是可以問問,市場的最終勝利者究竟將是美元還是數位打底的中國人民幣?
本書是經濟、金融理論與現實世界經驗的結合體。我不採取傳統金融手法,聚焦個別股票的優劣價值,而是專注資產配置,並依據投資群眾與貨幣機構的互動程度評估總體價值轉變的潛力。這套手法為我所有,但確實是有幾位前輩為我提供靈感。在所有影響我的學者當中,首屈一指的幾位是榮恩.史密斯(Ron Smith)、倫敦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理查.波提斯(Richard Portes)、倫敦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賀蓮.芮伊(Hélène Rey)與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的帕沃.波瓦拉(Pavol Povala)。在商界,我有幸得與華爾街資深分析師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摩根士丹利研究部門副總裁馬帝.萊波維茲(Marty Leibowitz)與克里斯.米欽森(Chris Mitchinson)等創意十足的研究者共事。至於思慮周到的銀行家,最著名的就是資產管理顧問依文.卡麥隆─瓦特(Ewen Cameron-Watt)與已故的英國投資銀行家麥可.霸菱(Michael Baring)。1996年,一批同事與我共同創辦投資顧問公司「跨境資本」這家專事蒐集、執行流動性與資本流向數據工作的企業。安琪拉.柯吉妮(Angela Cozzini)尤其值得表揚。我還要感謝佩爾格雷夫.麥克米蘭(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編輯涂拉.薇絲(Tula Weis)與露西.齊薇(Lucy Kidwell)。最重要的是,我要衷心感謝長期包容忍讓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