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搭貝多芬 生日快樂!
喜歡過生日的不只你我,還有古典音樂圈
樂界非常喜歡幫音樂家過生日,還記得2006年莫札特誕生250周年,那時全世界樂團必演莫札特樂作,包裝紙上印著莫札特可愛肖像的巧克力球,無論是維也納代表色的金紅鑲嵌,還是老牌的藍白正統包裝,莫札特巧克力球可說是橫掃世界,走到哪裡都看得到。為了紀念莫札特而舉辦的薩爾斯堡音樂節,更是湧入數十萬人參觀,帶起一波波龐大的文化觀光商機。
盼啊盼的,今年古典音樂界總算盼到了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誕生250周年。

貝多芬一生,活了57歲,在18世紀來說算是相當長壽,也因為他活得夠久,他的樂作非常多,從鋼琴曲,室內樂作品,歌唱曲,交響曲到協奏曲等,貝多芬都有代表作。他從小就是音樂天才,沒有過正統音樂教育,也沒念甚麼書,但他的文學造詣相當好,一生最鍾愛的除了相熟的歌德,就是史詩家荷馬與莎士比亞;他的字跡非常潦草,但也可能是因為僅能靠文字跟外界溝通,想說的比用寫的快的多。
改良助聽器 成功的自學者
貝多芬也是助聽器與鋼琴的改良者,同時還發明了節拍器,滿足他自己對於節奏精準的要求。除此之外,貝多芬沒有受過正統音樂教育,從小就是父親教導與催促,後來貝多芬前往維也納拜莫札特為師,但終究因為莫札特過於忙碌,而貝多芬也因為母親病重,須回到德國波昂而作罷。貝多芬第二次來到維也納,莫札特已經過世一年,他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維也納皇宮內的圖書館看譜,自己學習,從當代角度來看,貝多芬也是成功的自學者。
貝多芬出生於工業革命之時,機械文明初生,他因小時候得過慢性咽喉炎,後來轉為慢性中耳炎,病情逐漸讓他失去聽覺。羅曼羅蘭所寫的《貝多芬傳》提到,貝多芬從未完全聽不見,可以聽見的低音比高音清晰。也因如此,貝多芬在創作時常「用一根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音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這得以讓貝多芬坐在鋼琴前創作時,可以聽見聲音。
晚年貝多芬耳疾日益嚴重,靠著當時發明家梅爾策爾為他特製了特殊的助聽器,至今仍保存在德國波昂的貝多芬之家。
音樂散文作家佐依子(黃瑞芬)就說,貝多芬從現在角度來看,就是充滿創意,在創作上衝撞束縛,因為他要用的音符是那麼多,才能表達他的樂思,當時的鋼琴琴鍵根本不夠他用,這也促進了古鋼琴進階到當代鋼琴的改革。

唾棄當權者違背信念
貝多芬生於1770年,1827年過世,生命與1789年到1799年的法國大革命完全重疊,人生最精華時刻都在烽火中度過,他以他的音樂與道德啟發無數後人,堪稱一名深具信念的政治參與者。
1803年,貝多芬開始創作《第3號英雄交響曲》,作品完成於1804年初,原本貝多芬非常敬佩法國大革命的理想,以及為他們實現這個理想的拿破崙,想要將這部交響曲題獻給他。未料拿破崙1804年5月加冕自己為皇帝,貝多芬知道之後,對拿破崙大失所望,他拿起樂譜,拼命要把拿破崙的姓名改掉。
阿波羅畫廊第二代,也是維也納藝術大學藝術學博士張凱迪說,當時沒有立可白,那紙樂譜就被貝多芬搓搓搓,出現了破洞,之後他把標題改為「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英雄人物」。
貝多芬音樂充滿對社會現狀的映照,更多的是對於自由博愛的企盼。

貝多芬的《第9號交響曲》,撇除開創性的樂曲格式不談,想著貝多芬在陷入幾乎全聾後仍有巨大創作力,他用詩人席勒的詩作譜寫〈第4樂章〉,其中膾炙人口的「歡樂頌」歌詞:「億萬人民團結起來!大家相親又相愛!」,每每相聞,都讓人熱淚盈眶。
彌補裂痕 唯有貝九
1989年11月9日,分隔東西德的柏林圍牆突然「倒塌」,東德政府宣布鬆綁旅遊限制,當晚許多東柏林人便湧至柏林圍牆邊。起初,邊防駐軍逐一在護照蓋上「永久離境章」,但最後由於人數眾多、場面混亂,駐軍幾乎不檢查護照,就讓東德人自由進入西柏林。這一天,象徵分隔東西德長達28年的柏林圍牆「倒塌」!
一個月後的耶誕節,美國作曲家兼指揮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率領東西兩德與英、美、法、蘇四國音樂家在柏林音樂廳演出,用以紀念德國分裂結束,所演出的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中,歌詞裡所有的「歡樂」(Freud)皆改為「自由」(Freiheit),這也讓第4樂章的〈歡樂頌〉變成〈自由頌〉。
現在,這首〈歡樂頌〉已成為歐洲聯盟的官方盟歌,《第9號交響曲》更榮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名錄。法國總統馬克宏發表勝選演說時,用的背景音樂不是法國的《馬賽進行曲》,而是貝多芬的〈歡樂頌〉,意義不言而喻。
佐依子說,只要學到一個程度,沒有一名音樂家可以逃離貝多芬,他的作品太多,交響曲,協奏曲,奏鳴曲甚至聲樂,民歌都寫,「逃無可逃,他就在你身邊。」
作曲家楊聰賢則說,莫札特過世之際,貝多芬都還沒有上場,但他一出手,就大破大立,「作曲家成為一個被大眾認知的身分,貝多芬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楊聰賢說,貝多芬讓世人認同作曲家是一個有自覺,有自發性,有獨立創作的角色,而不僅僅只是貴族委託創作的樂匠,「我認為貝多芬是第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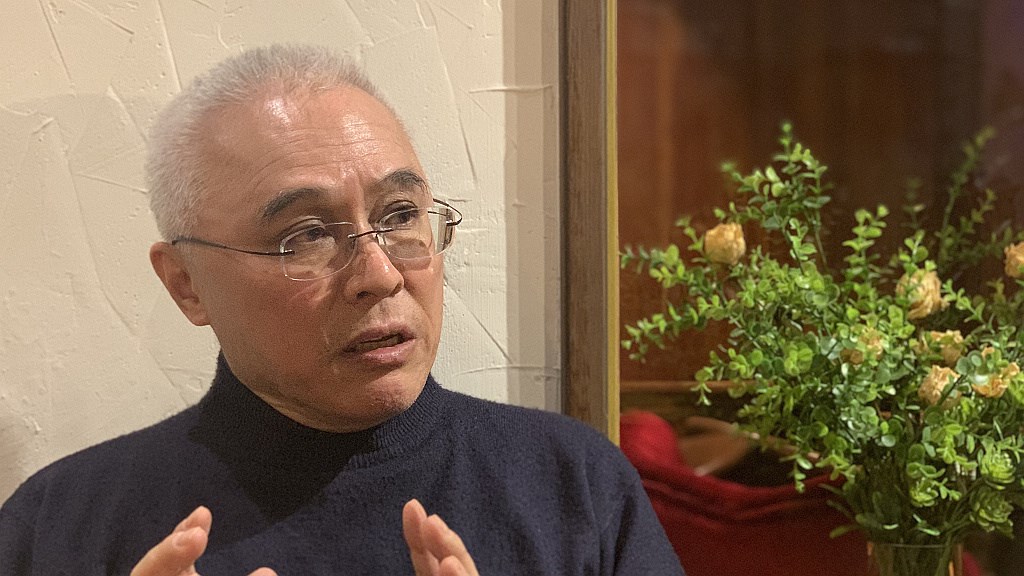
楊聰賢說,從工業革命開始,社會急速發展,專業分工得越細,古典音樂與一般人的距離越來越遠,這已是不可逆的現象,「但我深信每個時代,都有能夠理解如貝多芬音樂的力量,即使微弱,卻足以延續。」
資深樂評人OTTO(賴偉峰)則說,他「很幸運」地有貝多芬一直活在他的生活裡,有很多「共感」。OTTO說,因為小時候學音樂,「都必須面對一個以音樂為職業的父親。」其次,他完全認同貝多芬所主張,音樂是藝術,凌駕於貴族、富人之上,無可妥協,而且「人生是一場不停歇的戰鬥。」

想想貝多芬真的很百搭,如果還是覺得貝多芬好遙遠,那想想倒垃圾時常聽見的《給愛麗絲》好了,是的,那就是貝多芬寫的,而且聽來毫無違和,彷彿那就是一個儀式,倒掉了家裡的實相垃圾,也洗滌了內心的無形負能量,這不正是古典音樂隱形的力量。
謝謝貝爺,生日快樂!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