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反叛之聲:廣播人陶曉清談Woodstock和戒嚴的島嶼
60年代,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台灣掀起了一股現代主義思潮,文學、電影、音樂等,西方世界的種種都不斷地顛覆原來的想像。
當時資訊傳播尚稱不上便利,電視根本還沒普及。報紙、廣播等媒介,自然是扮演著資訊傳播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廣播,收音機普通家庭還算負擔得起,消息散佈的速度,相對於報紙更為即時,因此,電台是尤為重要的文化介質。
西洋音樂就依著當時許多電台的熱門音樂節目,被引介進入台灣,節目主持人從美國Billboard、Cashbox等音樂排行榜上抓下在西方世界當紅的歌曲,盡可能細緻地將相關知識蒐集完整,在節目中試著講解、播放那些遠在太平洋另一端音樂。
幸虧了廣播,Woodstock發生的當時,台灣青年也正聽著鄉村民謠、爵士搖滾。

但與美國青年不同的是,沒人號召活動讓他們裹上滿身泥漿,高喊愛與和平;台灣青年有的只是在唱片行架上的翻版唱片間、廣播節目裡,試圖翻找這座島上還沒有的世界。
陶曉清是資深廣播人,她另一個名號更為人所知,被稱為「台灣民歌之母」。1965年開始,陶曉清在中廣主持熱門音樂節目,引介西洋音樂。在她職業生涯的中後期,她致力於媒合音樂創作人,並在節目中介紹這些創作人的音樂,成為台灣民歌時期的重要推手。
Woodstock 發生在1969年,正好是陶曉清進了中廣之後的第4年,那一年,她才23、4歲。透過她廣播人的視角,觀察當年的台灣、西洋音樂文化在島內流動的景象,應該非常恰當。
太平洋的兩端
60年代的台灣,當然還活在反共復國的熱血之中,中國共產黨的日益強大,讓台灣島內的壓力緊繃。國民政府在這個時期,自然得以高壓手段控制群眾,以免搞定外患都還沒個頭緒,內憂又在身後扯著腿。
Woodstock 當時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正熱烈展開,美國的青年高舉著反體制、反文化的旗幟,或走上街頭,或走入山林。虛無主義瀰漫,反戰思想高漲,年輕人們以搖滾樂、迷幻藥嘗試從這個什麼都做不了的世界中暫時離線。

陶曉清正是在此時開始廣播生涯,她在60年代中期開始進入播音室,對著麥克風另一頭無數隻的耳朵,介紹遙來自遠海洋另一端的樂音。
2003年滾石文化出版的《Woodstock: The Oral History》裡,陶曉清那個同是廣播人的兒子馬世芳,寫了這麼一段話:
「這樣的時代背景,台灣囡仔竟然可以和英美青年同步聽到排行榜上的暢銷搖滾曲,著實不可思議,只能歸功於司掌文化管制的官員英文太爛,無法領略搖滾樂挾帶的張牙舞爪的訊息。於是這些歌脫離了上下文脈,就這麼硬生生戳進了『自由中國』靜悄悄、冷冰冰的天空。」
活在這個時代的陶曉清,正如她兒子所說,這樣的鏈結中扮演了關鍵的那個角色。陶曉清說,事情是從那個世新偏僻山上的小電台開始的,那是她走入廣播的起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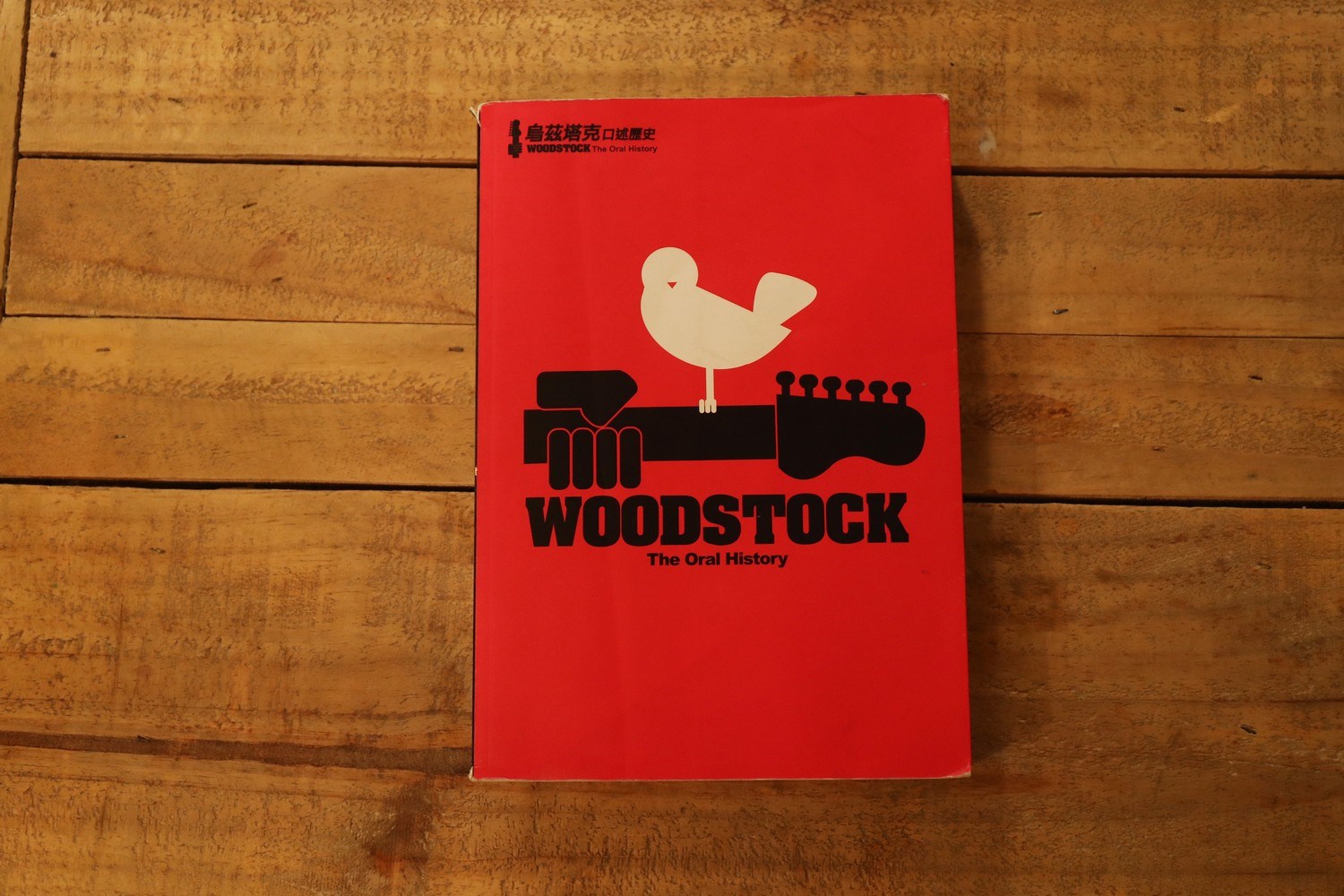
廣播節目、唱片行,20幾歲的日子
那年陶曉清17歲,專二生。「暑假很長,我們有三個月,我就去找我們學校電台的老師我可不可以去實習。」老師沒怎麼想就答應了,陶曉清笑著說:「老師大概看我還蠻可愛的。」
那個夏天她在校園電台裡,什麼雜事都幹,「跟著他們做節目,需要我幫忙我就去幫點忙。」她屬於講話速度快的那種,又快又清楚,過沒多久升上專三,她已經在電台裡主持一個音樂節目,「每天下課都沒回家,就留在學校電台做節目。」 年輕人有點事能做,總是流血流汗的付出,她也不例外,「就很樂啊,年紀輕輕的、那麼小的小孩子,有一件事讓你每天去做。」
但做節目功夫很重要,音樂節目尤其是,剛好陶曉清很認真,同時也有著一份幸運。那幸運是音樂對她而言並不陌生,家裏從小有台唱盤,成堆的唱片,家中大人什麼音樂都聽,「常常就是誰愛聽什麼就放什麼,我們小孩子還沒主權說我要聽什麼,只能就跟著聽。」如此時間一長,雜雜亂亂地也積累了許多旁人無法輕易獲得的音樂知識。

後來有了電台節目,陶曉清更是勤跑唱片行,「金門街、南昌街那一帶就有好幾家唱片行,其中有一間,老闆跟我混很熟,每次唱片出版的時候,他就幫我留。」搞了一年的學生電台,陶曉清靠著努力和熱情,進了中廣開始主持熱門音樂節目。
Woodstock與反叛,國民政府與反戰
中廣是黨營電台,在國民政府時代資源當然多,陶曉清那時靠著熱門音樂的節目,什麼最燙手的資訊她都先拿到,民眾都還在等翻版唱片,她靠著電台能第一時間拿到原版專輯以及西洋音樂雜誌,「我那時候訂的雜誌是Cashbox,這個雜誌跟Billboard等於有點分庭抗禮。」
Woodsstock這事發生的那會兒,陶曉清她第一時間真沒辦法做什麼,「因為基本上是做廣播節目,一定要有音源,就是要有現場實況的唱片。」Woodstock的現場錄音專輯隔年才發行,因此縱使陶曉清看到了事件,也沒辦法告訴聽眾,「我真的不是在這個事情發生,馬上就做報導。」

真正等到Woodstock發酵,大概已經過了4、5年,「我是到後來他們有一些團,出了單曲的唱片,我收到了以後,發現跟它(Woodstock)有一點關聯或幹嘛,我才可能會去提到它。」當時陶曉清的節目,主要就是以介紹排行榜上的熱門音樂為主,Woodstock的那些歌曲,並不一定每首都登上了排行榜。
在當時,美國那邊也不是以正面的態度面對這場音樂會,沒有太多的討論,遑論台灣;而且只有音樂,人們根本難以想像發生了什麼事,要一直到更後來紀錄片傳進來了,台灣人才有了畫面。
國民政府對於思想、言論的管控,在戒嚴時期的力度相當大,陶曉清回憶起那段時間,反而笑了出來:「因為電台還有所謂政令宣導的任務,所以幾乎所有的節目都會有很嚴格的管控。」Woodstock此類的反體制、反戰的文化思想,國民政府當然不會放任其在島內橫行。
陶曉清說尤其越戰那段時期,西方開始出現反戰歌曲,此類歌曲全在禁播清單上,「我的節目也被警告,這些反戰歌曲不能播的。」除了歌曲,當然雜誌也列為管控物,「就算是直接訂國外的雜誌,如果有一個消息是對台灣不利的、或者是他不想讓你知道的,那個雜誌會有一個切口。」

當時電台裡除了陶曉清訂購的單曲唱片,還有一些專輯黑膠,「我不知道是誰買的,不是經過我,但後來因為好奇去借了唱片,發現上面若出現反戰歌曲的,就會被拿膠帶貼起來,所以我就算借了那張唱片,我也不能播啦。」頓了頓,陶曉清說自己其實還是幸運,因為大部分的節目都得經過編審,「但是熱門音樂節目沒人管,我是完全自己負責。」
可是縱使如此,政治力量龐大到不可思議的當時,身為文化人的陶曉清當然得小心,「雖然說沒有人管我的節目,但是我自己也要有一個小小的尺標,講話啊、幹什麼的,不能亂講。」
嬉皮,自由,台灣
Woodstock裡的那些嬉皮,以陶曉清來看,並不是沒有影響到台灣,「因為當時嬉皮文化帶給美國文化影響,但是我們的文化相對弱勢,是屬於全盤接收的。」但她也強調,在那個年代她的熱門音樂節目,其實在引介歌曲上是被動的,「排行榜上有哪些歌,我就放哪些歌。所以你要真的問我年代,我完全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才開始在我的節目裡頭也報導關於這個演唱會。」
台灣年輕人其實聽的是西洋熱門音樂,陶曉清說那個年代只能這樣,太多的資訊傳遞有限制,人們只能囫圇吞棗。可也因為如此,當真正看到Woodstock的紀錄片影像時,所有人受到的衝擊都相當巨大。
「從來沒有過,在一個鳥不拉屎的地方,連路都沒有,居然可以吸引這麼多有名或沒有名的樂團願意去。」陶曉清話又說得更快,眼神如鉤,「我們後來去看紀錄片,或是不管是誰,用各種角度去探索的時候,你就知道這種事情就在那個時候,就發生這麼一次。」
想著那些長髮少年、搖滾樂、毒品,陶曉清嘆了口氣,「再也不會有了 。」然後她笑了,「所以我要講的是,台灣的自由真是得來不易的,年輕人可以享受到如此寬廣的自由度。」
陶曉清在播音間幾乎一輩子,為這座島做了那麼長時間的文化傳遞者。
她告訴我結論,「我們走過那個年代,我們都知道。」




 記者在現場系列文章
記者在現場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