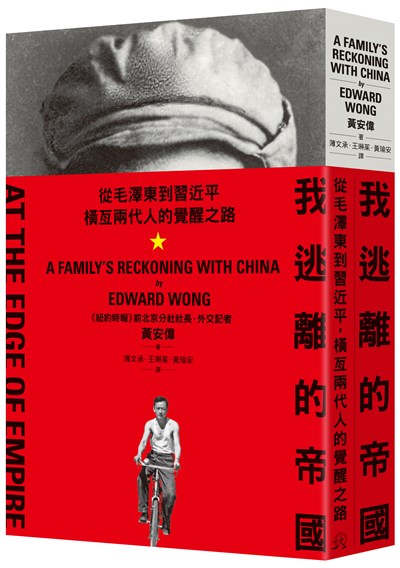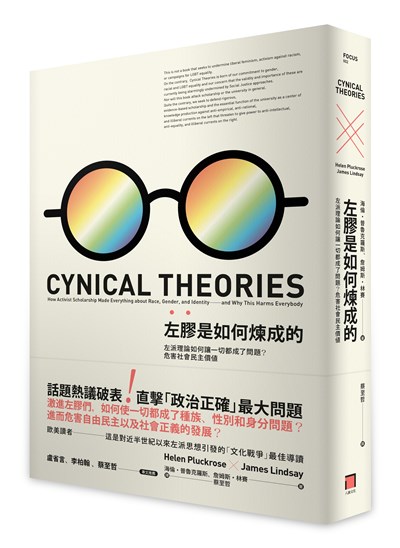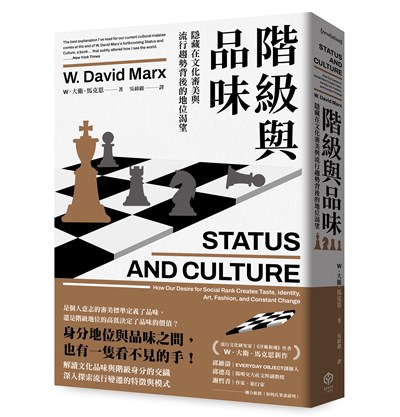這本書探討了榮格如何分析他最著名的病人——開創性物理學家包立——夢的意象。包立非傳統且狂亂的生活,讓他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於是找上當時炙手可熱的榮格為他做夢的分析。他沉迷於自己的夢境,藉此試圖挖掘某些超越物理學的東西。這是兩個特立獨行的人的故事。包立,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家,與同儕不同,他對自己的內心深處非常著迷,他相信人的心靈和物質宇宙源自同一個原型。還有榮格,著名的心理學家,確信科學能回答某些折磨他的問題。這兩人都在自己領域做出巨大且持久的貢獻。在蘇黎世湖畔榮格宅邸的晚宴上,他們的多次對話把他們帶到更遠的地方。這本書是兩個同樣聰穎卻又截然不同的人之間非凡友誼的故事。
文章節錄
《數字與夢:榮格心理學對一個物理學家的夢之分析》
第八章 心靈的暗黑狩獵場
包立向來喜歡充分掌握資訊。準備與榮格首度會面之前,他毫無疑問地已研讀過幾本自己書房裡的榮格著作。在他們合作的過程中,他閱讀了榮格全集的大部分內容。他用鉛筆在書上劃線:一條垂直線標示重要段落,兩條則是很重要,三條就代表非常重要。
《心理類型》一書特別引起他的注意,榮格在這本書中列出分析心理學的詞彙和框架。他在書中分辨人格的兩極特徵――外傾和內傾,以及四個「功能」,思考/情感,直覺/感官。迄今《心理類型》仍是他書房榮格著作中注記最多的一本。榮格將互補功能兩兩對立,這點與玻爾互補原理之間的相似性,毫無疑問地讓包立感到震驚。互補性似乎無處不在。正如他據以澄清物理學議題,也許榮格運用包立熟悉的術語讓他覺得這可能是他瞭解內在自我的關鍵。
包立用三條線標注下面這段內容:「如果某人的人格面具看來是有智之士,我們可以篤定地說這人的靈魂是相當感情用事的……非常陰柔的女性有著男性靈魂,非常陽剛的男性則有女性的靈魂。這種對立事實的基礎在於,比方說,男人並非完全是陽剛的,而是也具有某些女性特徵。」包立當然是知識分子,受到他情感生活創傷的打擊也同樣相當多愁善感。他是個很陽剛的男人,那 他的女性靈魂在哪裡?也許榮格會幫助他發現它。
榮格對內傾思考型的描述,則是令人心驚地精確描述了包立這個人:
他的判斷顯得冷漠、頑固、武斷、不顧他人,只有出現困難時才能說服他自己承認。對他來說,清楚明白的事情可能對其他人來說並不同樣清晰;[如果]身邊的人無法理解他,他會收集進一步的證據,來說明人類的愚蠢不可思議;他可能會成為帶有赤子之心的厭世單身漢;他渾身帶刺、難以接近、傲慢;[他]隱約恐懼異性。
毫無疑問地,當包立走進榮格家時,他心裡知曉所有這一切。
隨著寬廣的迴旋梯來到二樓,接著他沿著走廊右轉,經過榮格有時用來避靜的小型辦公室。這間簡潔的房間內沒有任何書櫃,恰到好處地擺放著一張帶有三個抽屜的桌子、一盞小檯燈和歸檔文件的檔案櫃。柔和的自然光線穿過描繪神話場景的彩繪玻璃窗流洩而下。在此,榮格抽著菸斗、坐在有著舒適靠枕的辦公椅上,寫下報告和文章並回覆信件。
榮格在寬敞的書房接待包立,裡面擺滿了古老的煉金術典籍。地板上鋪著東方風味的地毯。綠色瓷磚的爐子在冬天維持著房間的溫度,夏天則有從湖面上吹拂而來的微風保持涼爽。正對著書房門口有張書桌、直背椅與一盞檯燈,旁邊就是能俯瞰蘇黎世湖的大窗。另一邊則擺張沙發,兩側是兩把安樂椅。患者可以任選椅子,端視他們想要面向書櫃或是湖泊。
榮格運用小房間來分析那些問題並不特別引他興趣的病人。面對自己在情感上有所涉入的病人,則傾向帶他們到書房。在那裡,不僅煉金書籍伸手可得,更如他所說的,房間大小是他稱為離體經驗(out-of-body)的心理空間。這時他會「站起來坐在窗邊,低頭看著自己的一舉一動,直到我看出無意識如何觸動自己,而我又該如何處理。」
榮格醫生就在書房裡,坐在沙發上面對著擺滿書本和筆記的書桌,等待著他的新病人。四年後,榮格描述了當天會見包立時,他處於糟糕的解離狀態:
他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智力發展極為出色的人,這當然就是他煩惱的起源;他太過片面地朝智力和科學發展。他非常聰明而且以此聞名。他不是尋常人。他諮詢我的原因是因為這種非常片面的態度導致他完全解離。不幸的是,這類的知識份子不關心他們生活的情感面向,因而失去與情感世界的聯繫,而生活在一個思考的世界,一個只有思想的世界。因此,無論是與他人或自己的關係中,他都完全迷失了自己。最後他喝了酒,這樣的無謂之舉讓他變得害怕自己、無法理解這一切是怎麼回事、無能適應,加上總是陷入困境。這就是他下定決心諮詢我的原因。
智識追求主宰了包立,他腦袋裡所想的全都是自身以外的世界,幾乎沒意識到他本人――一位著名的科學家發生了什麼事?對於榮格來說,可以與這樣的人合作,似乎是一個難以拒絕的機會,檢視是什麼讓他有如此表現,同時也試圖幫助他獲致平衡。
後來,在《心靈和符號》一書的序言中,榮格如此表達:
我們如何看待一位徹頭徹底的科學理性主義者,在他的夢和清醒時的幻想中都產生曼荼羅呢?他不得不在他即將失去理智時諮詢精神科醫生,因為他突然被最神奇的夢境和異象所圍攻……當上面提到的那位頑固的理性主義者第一次來諮詢我的時候,他的恐慌達到一種狀態,讓他和我都感受到了從瘋人院吹來的風!
「他完全解離了」、「他完全迷失了自己」、「他即將失去理智」,榮格「感覺到了從瘋人院穿來的風!」也許榮格誇大其詞,但是他的措詞清楚說明了此時的包立有多絕望,這種絕望他無法透過工作來解決,也不能與科學界的朋友同事們溝通。為了找到解決方案,他必須走出這個世界,進入榮格極其不同又古怪的宇宙。
包立傾吐煩惱――他的憤怒、寂寞、酒後鬧事、與女人之間的問題,以及他不時與人爭議。他提到自己的夢充滿了數字3與4,和其他似乎源自17世紀科學的事物,而非現代物理學。這些夢境和異象讓他分心。
榮格意識到,這名年輕人不僅需要幫助,而且還「塞滿古老的材料」。問題是,如何「精鍊這些材料,而不要有任何(來自榮格本人的)影響」?方法只有一種。就是榮格不要提出任何建議,而是讓包立自由說話和做夢,為此榮格不得不與包立保持距離。「所以我不會出手」,他寫道。
他的解決方案非常特別。他沒有親自治療包立,而是一開始就讓他年輕活潑的奧地利學生鄂娜.羅森鮑姆(Erna Rosenbaum)來接手包立的個案。羅森鮑姆曾在慕尼黑和柏林習醫,跟隨榮格僅僅九個月的時間,就被指派擔任包立的治療師。包立對於自己被搪塞給一名學生感到失望,但榮格沒有給他選擇的餘地。
包立以他一貫的簡潔筆調寫信給她:「[我聯繫]榮格先生,因為某些神經質現象讓我在女性身上不易獲致我在學術方面的成就。由於榮格先生的情況正好相反,我認為他對我來說是相當合適的醫治者。」但是,包立繼續說道,他吃驚於榮格拒絕治療他並且讓她來接手,不顧事實上「我對女性非常敏感,有些難以信任,並因而導致面對她們時態度有些猶豫。總之,」他總結道,「我希望嘗試所有可能的方式。」
榮格後來透露,他特意挑選了一名女性做為包立的分析師,是因為他確信只有女人才能從男人的無意識深處抽取出思想,特別是面對像包立這樣極富創造力的人。一如他所關注的,羅森鮑姆是鼓勵包立記錄夢境的完美渠道。榮格指示她扮演一個「消極角色」,只做鼓勵並指出包立應該更清楚解決的問題。「這樣就夠了」,榮格寫道。他直覺地認為包立「有視覺化事物的天賦,所以會自發性地出現幻想」以及夢境。事實上,羅森鮑姆完美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