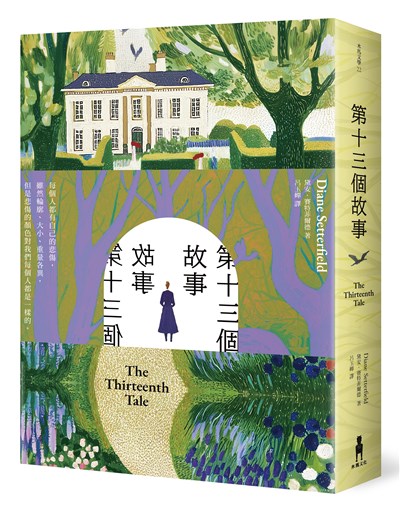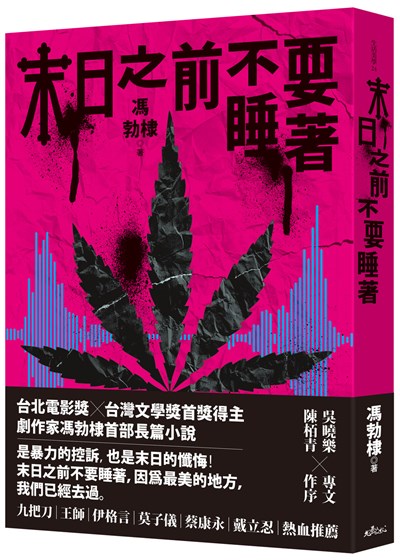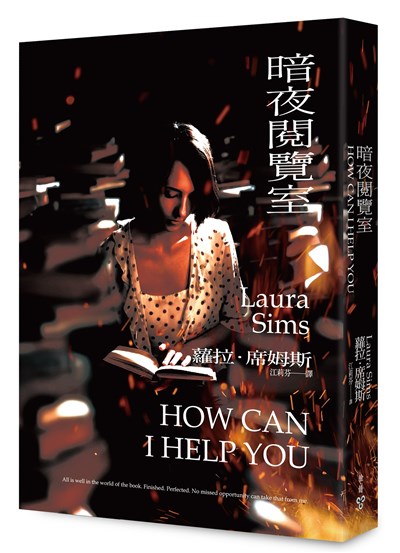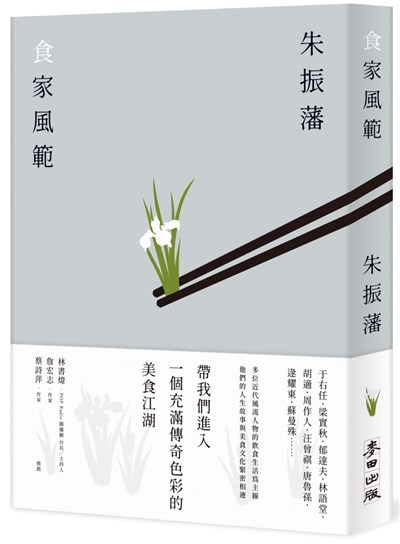過去主要寫短篇小說的作家郭強生推出第一部長篇小說《惑鄉之人》,反映從日治到當代的台灣故事,切入的角度很特別,從一九五○、六○年代的台灣電影發展書寫,因而挖掘到台灣歷史上鮮為人知的一個側面。故事人物涉及兩三代,都在尋找自己的故鄉,也讓讀者看到日本與台灣之間難以割捨的互動和交互影響。
整本小說以花蓮一個日本時代移民村做背景,敘述一個在台灣長大的日本人,二戰後返回日本卻無法認同故鄉,千方百計想回台灣,因為他認為自己在日本反而像異鄉人,台灣才是他的故鄉;他移民美國的孫子,後來回到台灣,找尋祖父留下的點點滴滴。書中即藉由移民故事探討什麼是故鄉?
小說的移民村有日本人、中國大陸來的外省人、台灣本土人,他們的生命交織在一起,呈現面貌多元的台灣本土史觀,並藉由鎮上戲院放映的電影,寫出戰後回日本悶悶不樂而返回台灣的祖父,投入台灣電影工業。作者挖掘出當時確有很多日本導演來台參與電影製作,顯示台日關係1945年二戰結束並未中斷並持續維繫著。
而在全球化趨勢中,台灣位置變得更重要,人來人往,台灣成為很多移民心目中的故鄉,身分認同卻又是台海兩岸分治幾十年來台灣人的一大困擾,書名點出對故鄉的疑惑,並質疑在流離遷徙的時代中,到底那裡才是真正的故鄉?故鄉只有一個,還是可有很多個?故事節奏輕快,筆法簡潔俐落,使此書成為內容豐富,可讀性相當高的一部文學作品。
文章節錄
第一章
一九八四
小鎮上唯一的戲院還是拆了。
時值深秋,日頭依舊灼眼火亮,吉祥街上連圍觀看熱鬧的人都沒有,整個上午僅摩托車一臺經過,橫在路中的黃狗懶懶站起,的的的小碎步讓道,索性穿過煙蒸的陽光朝陰涼處去了。引擎聲漸遠,鐵榔頭敲磚一聲聲,空空空,又被留在了陽光裡,像隱隱的頭疼。
退伍後這些年他都沒再回來小鎮。臺北的電影院都改成小廳了,那天頭一回看見錄放影機這玩藝兒,彩色寬螢幕上的悲歡離合刺激冒險被扁黑匣子吸魂似的壓進膠卷裡,他當下發涼只想到:電影院慘了。
原本巨幅白幕上打出的光影世界是夢想的入口,現在縮了水的夢裝進錄影帶、罩進玻璃箱裡,成了一種標本。院線片上片第一場演完下午就有了盜版錄影帶,小羅不能接受,曾經為了想看場電影他挨了多少打!戲院座椅翻下時的,那一聲帶鏽的呻吟,場子燈光暗去的一刻,先是國歌起立,然後預告片出現,最後正片開始,氣勢萬千的邵氏中影嘉禾片頭商標音樂起,人聲逐漸沉落,那些屬於電影的儀式啊……
老羅寫信來,說到吉祥戲院要拆,奇怪的是小羅沒有任何感傷,只心頭閃過模糊的一點不安。
在他心裡那樓早在多年前就已經塌了。
回來,只是為了一個答案。
吉祥戲院夜夜高朋滿座的年代,每幅海報看板都是小羅他爹的手筆。童年的小羅幾乎成天就在戲院的後倉房蹓出蹓進,瞧他老爹將下了片的看板一塊塊靠牆放好,管他何莉莉還是上官靈鳳,刷刷就被抹上一層白漆,然後老爹將打好格子的新片海報攤平在地上,按著比例也在看板上畫上格線,拿起沾了褐色油彩的細筆,全憑目測勾起輪廓。
小羅總安靜地看著老爹工作,直到姜大衛或陳觀泰的英姿煥發,像降靈術般化身於白畫布上,讓小羅宛如目睹絕世名作欽佩不已。
接近完工的老爹點起一根菸,小羅看準他累得沒脾氣,便要討那張海報納入收藏。上百張的電影海報塑膠袋包好好都被他收在床底,放學後第一件事便是數鈔票似的拿出來點數瀏覽。偶爾小羅猜不準他爹的心情,開口要討新海報時換來一頓斥責:「又要這破紙?咱們家是收破爛?」
不是破紙,小羅把它們全當成寶。老羅雖然為吉祥戲院畫了十幾年看板,自己沒進戲院看過幾次電影。電影這玩藝兒──小羅記得他爹鼻子一皺的表情──可不是什麼好東西!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就是這麼丟的,左派電影一部部攪得人心大亂!
從小他就被禁止溜進戲院裡,他爹警告收票員不准放行,那歐巴桑心軟的結果,便是看著滿臉鬍渣、身上一件染了五顏六色破汗衫的老羅,拖了兒子到她面前把小羅打得求饒。小孩沒記性,過幾天又來求阿姨,那歐巴桑苦著臉直吐舌:轉去啦!你係嘸驚死喔?
等長大些,街坊耳語他才聽出個端倪。母親在電影院裡搭上別的男人,跑了。
早幾天已先卸除的座椅堆在路邊,小卡車一趟運不完,陽光下待載運的座椅像是自己有意志從戲院裡逃出來的,一個個歪斜蹲在那兒,彷彿疲累的候車旅客。接著空空空空,朝西那面牆像炮竹一炸就在他眼前碎了。長年不見天日的放映廳如被武俠片裡的神掌一擊,現出了原形,四面壁紙上的霉斑不知已繁衍了幾代,燈光漆黑從沒有人真正看仔細過。
回到鎮上那天,老羅事先不知情,開著電晶體小收音機倒臥在竹躺椅上,瞇起眼看見夕照中走進院子的年輕人,沒有招呼,父子對望了一會兒,做爹的點了點頭便偏過臉去。小羅輕聲喚了聲爸,在花壇的砌磚上坐下,陪著老人聽著收音機裡嗚嗚咽咽的京劇,在夕陽中一點一點化成灰煙。
小羅記得他爹在畫看板時從來都是開著小收音機,放暑假同學們騎著單車往河邊去,滾動的輪影滑過戲院倉房前的水泥地,記憶中那收音機裡的聲音總混攪著單車的輪影,一吸氣滿腦淨是下午場電影散場後,側門一開噴出的霉冷霧氣。
寂寞,是小羅對活著這檔事最初的印象。
心裡總巴巴地惦著電影。終於上了初中,一下課拚命踩著單車奔向鄰鎮的電影院趕五點那場,七點半晚餐前再飛奔返回。海報已收集了兩大紙箱,看過與沒看過的電影攤在床上時,一個個電影紅星都只為他一人演出他編排的情節。也許,只是也許,青春期的小羅想像著有一天,自己也能與那扁圓鐵盒子裡裝的菲林產生某種命運的聯結……
靜靜站在偏西日頭下,望著自己身長拖曳變形的陰影,小羅想到了十年前一切仍平靜如舊的那個夏天。小鎮上沒有一臺臺卡車停靠,吉祥戲院門前沒有不分晝夜的水銀燈,街上沒有穿著日本服的臨時演員,在一切都沒發生前的那個夏天……
回頭朝著老戲院投望最後一眼,他離家了,憤怒卻又滿是說不出的迷惘。印象裡,小鎮的街道在秋光裡突如水瀑一般漾漾朝自己湧。而「吉祥戲院」四個楷體鐵鑄字,明明釘牢在洋灰磚牆上,紅漆斑駁像被蛀鏽會隨時脫落跌下。聽說外景隊當年看上的就是它那不合時宜的滄桑,典型的昭和年間二戰末期的混洋風格……
此番回老家前,小羅先抽空去看了改行經營起電影院的阿昌。
那日正巧戲院整修內部,阿昌解釋說,觀眾挑剔冷氣太大聲,舊放映機常斷片,沒辦法,不再投點本錢就真的會被淘汰喔!
當年跑片打工的阿昌,不論陰晴,總背著那扁圓鐵盒子,氣喘吁吁騎著鐵馬來回附近鄉鎮,後來果真上了臺北在片場扛燈。來到他們小鎮上出外景的那部電影,就這樣,悄悄改變了多少人的命運。
這個阿昌,國語片的黃金民國六十年代給他趕上了,當年人說西門町電影院大看板掉下來鐵定會砸到一個導演,武昌街漢口街上電影公司更是三步一間。他肯苦幹腦筋也快,從扛燈光劇務場記幹到院線發行業務,存了錢取了妻。就連錄影機興起的危機也成了他的轉機,原本經營困難的這間中型國語片院線戲院,被他廉價租下後,靠著跟本地發行商的多年交情,改做起西片二輪戲院的生意。雖開在西門町一座雜亂的商業大樓裡,一票兩片很受學生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