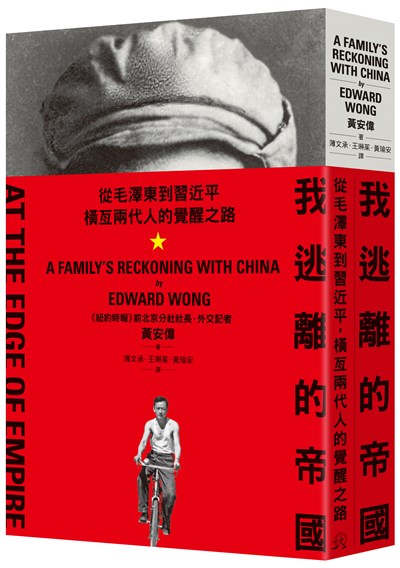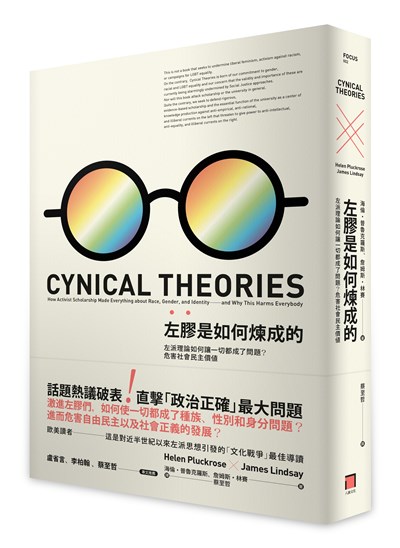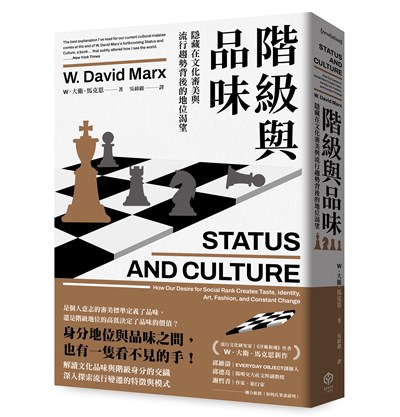本書作者范毅舜說:「我在野台戲場域體會到台灣最底層、卻最有活力的文化面貌。」他投入數年的時間隨著台灣極具代表性的野台戲劇團,走過許多城鎮、鄉野、山海邊,以藝術家的敏銳與朋友的心懷,拍攝四萬張以上的照片,也書寫了所見所感,透過編輯專業在多如繁星的影像中,以野台戲演出的流程及前台、後台生活面貌呈現,也巧妙的搭配著文字,成就這一部滿載影像震撼與文字內蘊的作品。
文章節錄
《野台戲》
後台人生
後台是聆聽故事的好地方,只要開口問,就會聽到令人心為之一緊的故事。昔日,學戲孩子大多來自貧苦人家,現在雖不同於以往,自願從事戲劇的演員仍有聽來甚為蒼涼的心事。明華園天字團的林淑琪從小在明華園學戲,長大嫁了個好丈夫,生了兩個小孩後就在家相夫教子。然而造化弄人,為人老實善良的丈夫好端端地竟罹患絕症而亡,進工廠做工的薪水又低得無法養小孩,無一技之長的小琪回到明華園來,因為阿興的父親陳盛典老團長,生前曾交代他:「『戲棚飯桶咖大,不缺給人一個碗、一雙筷。』有天,小琪若需要幫忙,一定要把人家接回來。」
阿興說,他們從不接花東地區的演出,是因為有一年去花東演出,由於路上有狀況,無法如期歸來,在那個沒有手機的年代,老團長陳盛典坐立難安地一直等到過半夜,他不僅擔心自家小孩,更擔心別人家的孩子。待他終於看到卡車身影,他立下決心,無論對方出價多高,再也不接花東演出。
而現在提起老團長仍是天字團最大的痛,原來老團長六十一歲那年的中秋節,在潮州家中等待孩子們自外地演出歸來,他焦急地在家的對面等著演出的大卡車,當他終於看到卡車蹤影,過馬路準備迎接孩子回家共度中秋時,卻遭一部酒駕車撞上,送醫不治。
千葉興劇團也有位專門跑龍套的演員謝穎松,從外表上看就知道他有腦性麻痺,這位不多話的先生總愛獨坐戲台一角,原來他是貫誌多年前邀來演戲的夥伴。世彬說,從前演戲時就發現穎松有一頓、沒一頓地跟著戲班閒晃,貫誌邀請他來支援演戲,供他吃住,而穎松也很高興自己的薪水能奉養在雲林麥寮生活的老母親。
拍千葉興時,我曾拍到一張我個人相當喜歡的影像,那天劇團在小琉球港口演出日戲後,一位中年婦女躺在戲棚地板上對團長貫誌訴說年輕時的經歷……
這位婦人便是石美玲女士,原來她是世彬的姑姑,我跟著喊聲姑姑,她親切地告訴我她自己的故事。
美玲女士出身於高雄鳳山歌仔戲世家,她當年很氣父親把她嫁給比她大十二歲、在鳳山當兵的外省老芋仔,在她的眼裡,當年只有次一等的人才會嫁給外省老兵,她很不服氣姊姊們都能嫁給本省郎,相形之下自己好像活活矮了一截。然而事實上,最後是她嫁得最好,她的先生朱囿彰,十六歲那年隨軍由貴州山區來到台灣,舉目無親的朱先生娶了美玲後,除了將岳父母視為自己的親爹媽奉養,更對美玲的姊姊、姊夫們畢恭畢敬 。
美玲的父母也講道理,每當與朱先生拌嘴,她的父母一定先教訓美玲:「你到哪去找這樣的女婿?」她還曾陪朱先生回偏遠的貴州探親。高齡的丈夫逝世前曾表達落葉歸根的心願,美玲深情地對他說:「你的老家都沒人了,而你的孩子們都在這兒,逢年過節時起碼有人祭拜你。」朱先生後來釋懷了,過世後就安息於南台灣。
一個場域的生活周遭往往可見文化的縮影,在一個快被現代擠壓到邊緣的野台戲場域,仍可見到傳統文化中的敦厚特質。就在我不停反芻這文化道統的特質與份量時,我到學甲慈濟宮拍野台戲,意外碰上了三年一度的學甲上白醮,這已有數百年歷史的偉大慶典,迄今仍保有全台唯一以人力扛負遶境的蜈蚣陣。傍晚一輛輛大型遊覽車在廟前停了下來,我看到不同於本地的人下車進香,原來他們都是由這裡分香火出去的異鄉華人,趁此機會前來謁祖。這群不是從本地外移出的華人,穿著繡有來自不同地區的團服,只見他們虔誠進得廟來,當廟方人員殷勤以台語探詢來祭祖的團員「甘無通」時,他們誠懇地回答:「通,攏ㄟ通!」頓時鐘鼓齊鳴,廟方禮官在一旁對著保生大帝神像高聲朗讀子弟們打從何處來的疏文。原來他們有的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在他們舉香三叩首後,這群異鄉人竟不約而同地對著保生大帝神像鼓起掌來高聲歡呼:「回來了!回來了!……」
我眼中泛著淚光,猛然想起就學期間,總被我嫌棄像陳腔濫調的「源遠流長」四個字,竟是如此深刻與教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