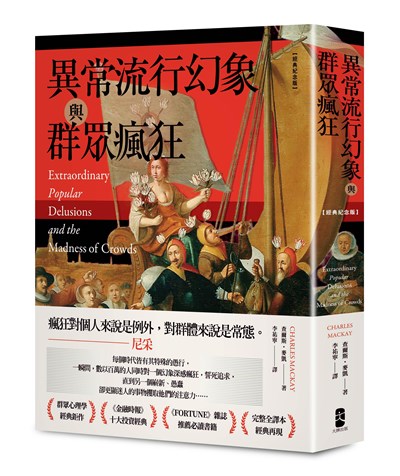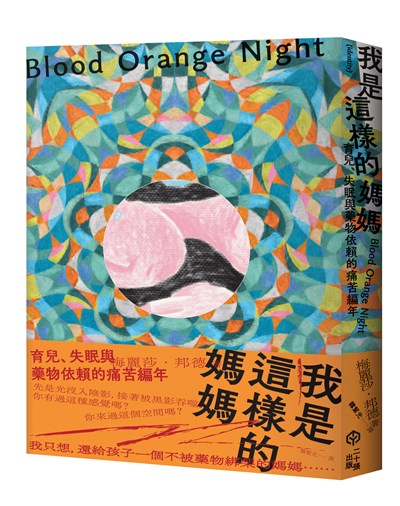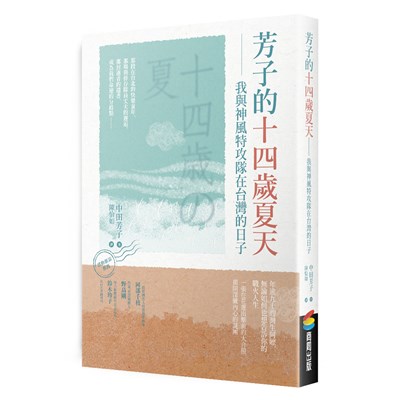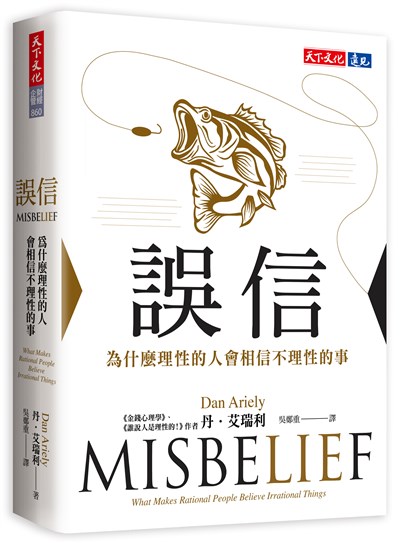美國,是當代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她的建國歷程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膽的一場政治實驗,本書的寫作目的是要記述這場美國實驗四百多年來的源起、過程,以及成果。獨立宣言揭櫫的三項真理:政治平等、自然權利、人民主權,在歷史的過程中不斷受到挑戰。時至今日,2020年對美國及全世界尤為重要的一年,回顧美國的歷史過往顯得更為重要。本書近六十萬字就圍繞在作者懷著那份建國時的理想初衷,叩問這數百年來的種種歷史發展,省思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到底有多遠,美國的未來是會走向共存共榮還是分崩離析。
文章節錄
《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
第五章 人群的民主
一七八七年,當聯邦派和反聯邦派在美國報紙斑駁的頁面上和會議廳破爛不堪的地板上為提出的憲法爭論時,駐英國的代表約翰.亞當斯在他位於倫敦格羅夫納廣場的辦公桌前抱怨,當時駐法國的代表傑佛遜正在巴黎香榭麗舍大街的朗格雅克酒店(Hôtel de Langeac),倚靠著自己那張顯然更時髦的書桌。他們遠離家鄉,這兩個一起草擬了獨立宣言的人,就憲法進行了一場書信辯論,在英吉利海峽上交換了信件,好像他們正在舉行一場雙人批准大會,亞當斯擔心憲法賦予立法機關的太大的權力,傑佛遜對總統一職也有同樣的害怕。亞當斯寫給傑佛遜:「你害怕一個個人的統治,我害怕的是一群少數人的統治」;「你擔心君主政治,我擔心的則是貴族政治」。兩人都對選舉感到掙扎,傑佛遜擔心選舉太少,亞當斯則擔心選舉太多了。亞當斯寫到:「我敬愛的先生,看著選舉,我感到很惶恐」。
亞當斯跟傑佛遜之間的辯論沒有隨著憲法被批准而結束。在華盛頓於一七八八年當選或執政期間,當亞當斯擔任他的副總統,傑佛遜擔任他的國務卿時,也沒有結束,而在一七九二年華盛頓再次當選後,他們之間的辯論仍舊沒有結束。相反地,他們之間的辯論在一七九六年協助建立了這個國家首批穩定的政黨。
傑佛遜一直在擔心憲法允許總統可以一再服務,直到死亡,就像國王一樣。亞當斯喜歡這個觀念。他在一七八七年寫道:「這太好了。」一七九六年當華盛頓宣布他不會競選第三任時,亞當斯跟傑佛遜都希望可以取代他。亞當斯以些微的差距獲勝。這兩個人下次又在另一場傑佛遜稱為「一八○○年革命」的一場選舉中對決。無論這是否是一場革命,一八○○年的這場選舉,十年來亞當斯跟傑佛遜的辯論的高峰,帶來了一場憲政危機。美國憲法中沒有政黨的規定,而選舉總統的方法跟政黨並不相容。儘管如此,亞當斯和他的競選夥伴,曾任法國大使的查爾斯.科特斯沃斯.平克尼(Charles Cotesworth Pinckney)以聯邦黨的身分參選,傑佛遜和他的競選夥伴,前紐約州參議員亞倫.伯爾(Aaron Burr)以共和黨的身分參選,這場選舉如此詭異,無論投票結果如何,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人完全確定結果為何。
傑佛遜聽到傳言說如果他贏了選舉,聯邦黨會「瓦解這個聯盟」,他相信聯邦黨人希望可以修改法律讓亞當斯能終身在這個職位上,因此他提出警告說:「我們在憲法上的敵人正在準備一個可怕的行動計畫。」同時,亞歷山大.漢彌爾頓也提出警告,如果亞當斯連任,維吉尼亞人將「訴諸使用武力」,好讓聯邦黨人無法上任。甚至有傳言說一些國會中的聯邦黨人已經決定,與其選出傑佛遜,他們寧願「擺脫憲法,接受內戰的風險」。一位困惑的國會議員反問:「誰會成為總統?我們的政府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亞當斯和傑佛遜之間持續不斷的爭論,既是兩個野心勃勃之人之間的競爭,尖酸而瑣碎,也是關於美國實驗的本質哲學上的沉重爭論。一八○○年,亞當斯六十四歲,比他年輕的時候更好爭論、更自負、也更有學識。他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的創始人,撰寫了三卷浩大的《為美國政府的憲法辯護》(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解釋了只有精心設計的憲法才能達成富人的貴族制和窮人的民主制之間的脆弱平衡。他寫道:「在每個有財產存在的社會中,永遠都會有富人跟窮人之間的鬥爭」;「在一個議會中將這些人混合在一起,永遠不會有平等的法律。這些法律要不是取決於人數,以掠奪少數富人,就是取決於影響力,以榨取許多窮人」。
傑佛遜此時五十五歲,是美國哲學學會的主席,遊走在情緒化跟發狂之間,這位激烈的作家跟亞當斯一樣富有學識,儘管個性比較矛盾。他相信多數人的統治。他認為,美國實驗的重點是「以身作則,說明人類關心人類事務的理性是充足的,而多數人的意志,即每個社會的自然法則,是人類權利的唯一確實的監護人」。亞當斯相信需要限制多數人的意志,傑佛遜則認為要順從於它。
兩人都贊同亞里斯多德的觀念,即存在三種形式的政府,每種形式都可能腐敗,而最能在這三者中達成平衡的就是完美的政府。亞當斯認為,最「易於改進」的政府形式是政體,如果立法機關能夠透過更確切地反映人民而能更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可以實現這種改善,並避免民主的恐怖。他寫道:「在組成代表大會的過程中,最終要鎖定的目標似乎是人民的意識、公眾的聲音」;「這個描繪的完美程度在於其相似度」。
然而,就亞當斯所談的描繪和相似性來說,兩個人之間的爭論不在於藝術,而在於數學。人民政府最終是一個數學問題:誰來投票?每張票要算作多少?
亞當斯跟傑佛遜生活在一個量化的時代。從測量時間開始。時間曾經是一個轉了又轉的輪子。在科學革命中,時間成了一條線。時間是最容易測量的量,它成為了每一個經驗式探索的發動機,像一根軸、一根箭頭。對時間的這種新用法和理解促成了進步的觀念:如果時間是一條線而不是一個圓,那麼事情會變得愈來愈好,而不是像季節一樣在無止境的循環中起起落落。進步的觀念激發了美國的獨立,也激發了資本主義的前進。時間的量化導致其他一切的量化:計算人數、衡量人的勞動力,以及將利潤當作時間的一個功能來計算。計算時間和累積財富被等同視之。富蘭克林曾經這樣說:「時間就是金錢」。
量化也改變了政治的運作。儘管他們之間存在差異,亞當斯和傑佛遜都同意政府建立在方程式和比率這些數學關係之上。亞當斯堅持認為:「數字或財產,或是這兩者,應該成為規則,而選民和議員所占比例則是計算的問題。」決定要訂下什麼規則是制憲會議的工作,而確立這規則將是一八○○年大選,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改革工作,這些都涉及計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