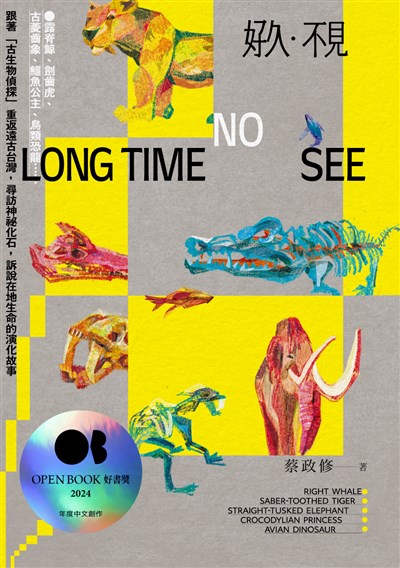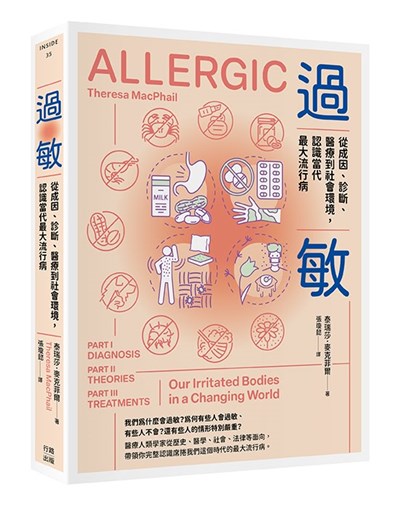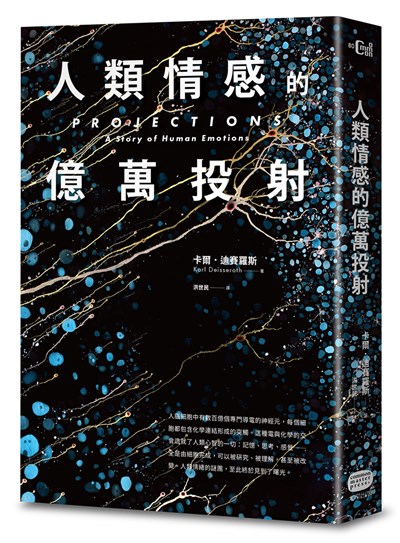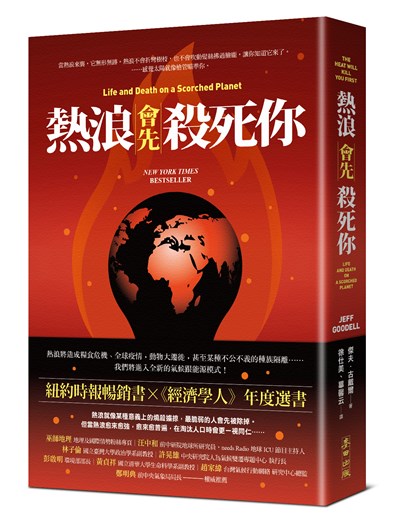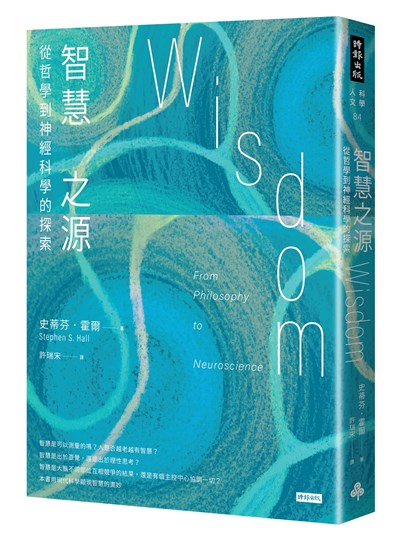
作者霍爾將智慧概念分成八個神經支柱,分別是情緒調節、判斷力、道德推理、憐憫、謙遜、利他、耐心、處理不確定性,然後拜訪了在這些領域做研究的科學家,進行深入的訪談。將過往我們認為無法分析與量化的「有智慧」得以透過作者援引腦科學、心理學及古代智者的言詞得到新的切入觀點。
文章節錄
《智慧之源: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
多個世紀以來,許多頂尖人才曾感歎,正規教育與卓越智慧之間的鴻溝何其大。蒙田就曾如此嘲笑狄奧尼修斯(Dionysius)的一名學生:「你從他身上看到的,只是他在學了拉丁文和希臘文之後,比他上學之前多了些自負和傲慢。他本應帶著充實的心靈回來,結果他的心靈只是變得浮腫;它只是膨脹了,而不是真有增長。」
雖然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很可能希望提高學生的智慧(或至少應該追求這一點),極少院校像塔夫斯大學那麼系統性地努力將智慧的各方面融入課程、招生過程以至學校的日常任務中。這主要是因為該校文理學院現任院長、美國心理學會前主席羅伯.史登堡押上他三十年的學術生涯,決定檢驗這個見解:如果世界有改變的希望,那麼智慧是可以在年輕人的頭腦中培養的──事實上是必須這麼做。
在某種意義上,史登堡成為倡導智慧的鬥士,是因為替他贏得最大學術聲譽的研究工作失敗了。他在耶魯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三十多年,發展出一套全面的人類智能理論。簡而言之,史登堡的理論認為,有才智的成功人士擁有三種關鍵技能──提出新想法的創造能力,辨識真正好想法的分析能力,以及說服其他人相信其價值、使構想得以實行的實踐能力。
但是,一九九○年代中期,史登堡開始認識到他的理論存在致命缺陷。簡而言之,其缺陷可由這個簡潔的問題概括:一些無疑有才智的人,怎麼會做出極其愚蠢、有時甚至極其邪惡的事?史登堡重視大型公共舞臺上出現的智慧(和智能),他因此受這個不方便的事實困擾:希特勒和史達林之類的人完全符合他的智能標準──他們很有想像力、聰明、長袖善舞,而且具有實踐自身想法的意志。但這些人是魔頭。
史登堡某次受訪時說:「真正偉大的領袖與沒那麼偉大的領袖,差別在哪裡?我檢視甘地、馬丁.路德.金恩、德蕾莎修女和曼德拉等人,如果你拿他們與史達林、希特勒和毛澤東等人比較,他們的智商很可能相差不多。他們的差別看來在於智慧。」 他意識到,史達林等人欠缺的是運用所有智能要素服務「公共利益」的能力。正如史登堡最近與塔夫斯大學的琳達.賈文(Linda Jarvin)和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的阿琳娜.雷茲尼茨卡亞(Alina Reznitskaya)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重要的不僅是你有多少知識,還在於你如何運用那些知識。」
重視如何運用知識,當然就是承認關注公共利益非常重要──如果你接受利他精神的演化史,這可說是個非常古老的觀念。但史登堡也意識到,智慧代表一種超越標準智力指標的精神狀態,而此一認識迫使他看到了教育系統和教育檢測理念固有的不足,以及智商之類的狹隘指標在預測人生滿意度方面的可悲表現。(他後來成為智慧研究領域的大師之一,一九九○年編輯了關於智慧的第一本正規學術著作。)
那麼,史登堡究竟認為智慧是什麼?他和他的同事將智慧定義為(請各位包涵下面的學術表達方式)「以價值觀為中介的智力、創造力和知識的應用,致力於實現某種公共利益,藉由在(a)短期和(b)長期內平衡(a)自身(intrapersonal)、(b)人際(interpersonal)和(c)自身外(extrapersonal)的利益,以達至(a)適應現有環境、(b)塑造現有環境和(c)選擇新環境之間的平衡。」
沒錯,這個定義讀起來像某種你永遠不想買的東西的購買契約,但如果你分析它的要素,會發現它極有彈性,而且適用範圍遠遠超出教育領域。史登堡談到平衡短期與長期目標,這涉及我們未來的自己與當前欲望的永恆角力,以及造就明智規劃和審慎精神的成熟。他談到適應現有環境,這關係到運用必要的情緒彈性以應對婚姻中的困難時期或令人生畏的財務狀況。他談到「塑造」環境,這表示智慧可以成為變革的推動力,利用決定和行動重塑家庭或商業狀況。他談到選擇一種新環境,這是承認在某些情況下,智慧的運用者會尋求改變環境,無論是結束一種虐人的關係還是決定換工作。最重要的是,智慧是一種尋求平衡的努力,是一種精神陀螺儀,在不斷變化的力量和利益面前尋求和要求平衡。
——摘自第14章 教室、會議室、臥室、密室 教育領域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