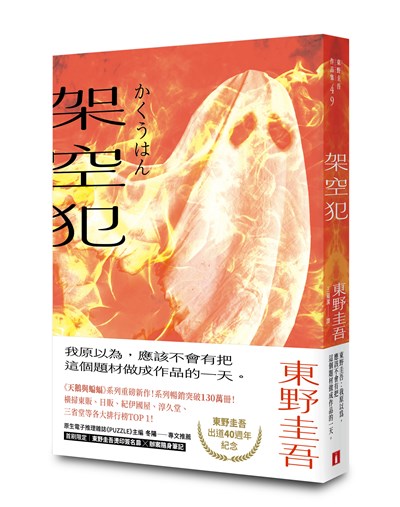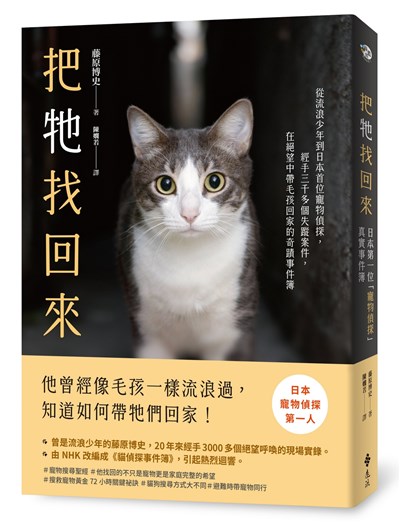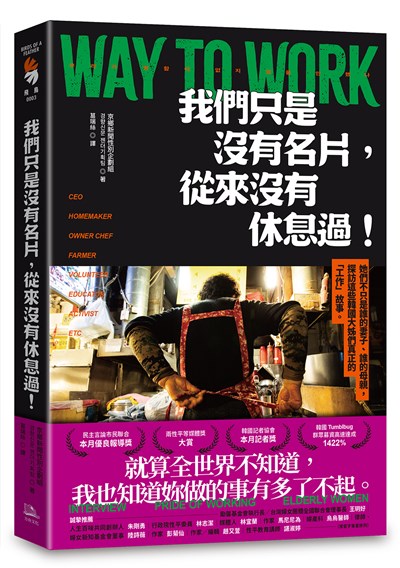
「我們遇到的女性說她們沒有名片,但她們從未休息過。只是社會從未將她們的勞動視為『工作』。」京鄉新聞性別企劃團隊訪談了數十位女性,這是一本從「工作」的視角,記錄高齡女性們一生努力的訪談集,講述了終其一生往返家中與外面、身兼多職的女性們。但比起姓名,人們更常稱她們為「誰的妻子或媽媽」……女性們吃苦打拚的故事太常見,常見到甚至被視為無關緊要,現在,透過這本書,我們想為這些女性找回「一張名片」。
內容節錄
《我們只是沒有名片,從來沒有休息過!》
我叫張喜子,1960年出生,是戰後的世代。原本住在江原道,你聽說過以蒸包聞名的安興吧?我的胎盤就埋在那裡。我3歲左右搬到忠南公州,在那裡讀到小學兩年級,以前爸爸賣米,媽媽經營一間叫做「忠南商會」的小雜貨店,在路旁賣車票等各種東西。那時的生活比較寬裕,因為我記得當時同學揹的是布制的書包,但我揹的是真正的皮革書包,還穿著皮鞋上學。
後來因為父親事業不順,我們搬到水原,住在水原的那兩個月,父母把哥哥和我寄養在隔壁人家家裡。當時我很害怕,擔心父母不會來接我們。
那時大家都快活不下去了,有些孩子會被送到孤兒院,或是送給別人領養。我大概9歲就開始懂事了,我跟哥哥寄人籬下時,是由我來照顧大我3歲的哥哥;即使後來和父母住在一起,我還是覺得要好好表現,似乎是從那時開始得了「乖孩子病」,從不會喊累,總是以身作則。村裡的長輩們總說,喜子體內住著一條蟒蛇。
我下面還有跟我分別差3歲、6歲、9歲的弟弟妹妹,因此,身為五個兄弟姊妹的長女,我長大後還要照顧他們。59歲的妹妹現在打電話給我時,還是會說「好的,姊姊」,我真的是像媽媽一樣的姊姊。我最近經常在大腿上扎蜂針,真的很痛,但我總是一聲都不吭。中醫師說,第一次看到這麼能忍的人。我想可能是因為我從小就習慣忍耐。
-
我曾在下班後參加YWCA的手語講座,現在也常和當初上班認識的姊姊們約出來見面,一起聊天時,會聊到當初真的忍了很多。那時社會的風氣相當重男輕女,要是發生在現在,大家會說那是#MeToo事件,但當時我常聽到的卻是「因為你是女人啊⋯⋯」;走路走到一半被拍屁股、摸肩膀這種事屢見不鮮,就算很討厭也沒能抗議。
我叔叔幫我做媒,帶我去相親。媽媽說她沒臉見人,因為兒女還沒嫁出去很丟臉,當時我27歲,哥哥30歲。我透過相親認識先生後,他那一個月內每天都來找我、向我求婚,他從位於仁川的公司開兩個半小時的車到水原;最後,我們在認識一個月又二十天後就結婚了,等於是跟陌生人結婚(笑)。
那時似乎是在逃避,因為如果想要搬出來住,除了結婚之外沒有別的方法。我那個月天天都看到他,對他的印象僅止於「他感覺是個老實人」。不過在那個年代,人們常常沒見過幾次面就結婚。
結婚後辭職是理所當然的,連穿的衣服都變得不一樣了,每天都穿著家居服做家事、照顧小孩,很自然地走上了賢妻良母的道路。第一次當媽媽、當媳婦⋯⋯真的很難,根本沒有人教我「如何當一個母親」!
-
我從沒想過要跟先生分攤家務或育兒,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準備早餐,送兩個兒子上學後就開始打掃家裡,忙得沒時間睡午覺,晚上也沒辦法早睡。孩子們還在念書時,會讀到晚上十二點,所以我都要開車去接他們。雖然家務也是工作,但我好像不覺得那是「工作」,久而久之,我的生活變成以孩子們的上學時間、丈夫的下班時間為分界點;而且婆家在京畿道華城務農,我週末也會去幫忙農活,那時候還為了能幫忙農活而考了駕照。
我也不是沒做過賺錢的工作,社區裡的媽媽們會一起做很多手工藝,作為一種副業⋯⋯我妹妹開了一家照片沖洗店,我也會去那裡繞繞,幫忙顧店,做了十年左右;趁白天做家務的空檔去幫忙,這樣一個月可以賺120萬韓元,我存下這些錢,居住環境也因此改善了,但是先生仍不認可我。
每次先生打電話來,劈頭就問:「孩子呢?」那時我覺得自己做的與其說是工作,倒不如說是在幫妹妹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