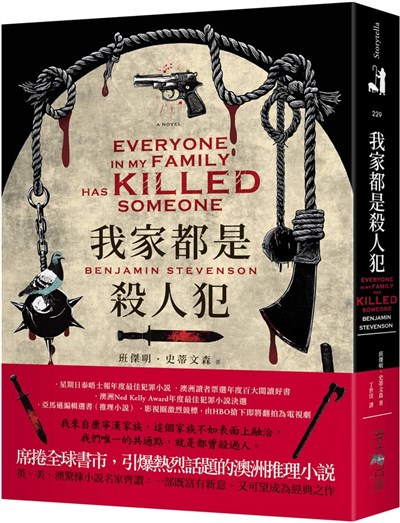自從鍾愛的女兒因車禍成為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席瑞絲無所適從,日夜守在女兒床邊,朗讀女兒最愛的童話故事,她決定,只要女兒還活著,她就會繼續念下去,希望能將女兒喚回。隨著女兒病情惡化,悲傷至極的席瑞絲試圖逃離那個孩子成了空殼的世界,她穿越荒宅,進入《失物之書》的世界──一個有女巫、樹精、長髮公主、巨人,也有駝背人的國度。在這個奇異國度重返十六歲的席瑞絲,展開一段尋回孩子的旅程,譜寫屬於她的青春故事……席瑞絲能平安走出危險重重的故事,回到女兒身邊嗎?
暌違十九年,約翰.康納利走到人生中段,重拾初心寫下《失物之國》,帶領讀者再次重返《失物之書》。在故事裡,我們一起面對可能痛失摯愛的悲傷與矛盾,一起咀嚼始終懷抱的希望況味。
內容節錄
《失物之國(全球暢銷破百萬冊《失物之書》系列最新魔幻大作)》
後來——因為有些故事就該這樣繼續下去——有位母親的女兒被偷走了。噢,她依然見得到那女孩,能夠碰觸她的肌膚、梳她的頭髮,也可以看著她的胸膛緩緩起伏;若是她將手放在孩子的胸口,也感覺得到心臟跳動。但那孩子沉默無聲,雙眼也不曾張開。她靠管子呼吸、進食,但對這位母親而言,感覺就像心肝寶貝的本體在他處,床上的形體只是一個空殼,一具人體模型,等待著離體的靈魂歸來,將其啟動。
剛開始,這位母親相信自己的女兒還在,只是睡著,聽見深情的聲音講述故事、分享新聞,她或許有可能醒來。不過隨著日子過去,一天天化為一週週,一週週又化為一月月,母親愈來愈難對女兒的內隱懷抱信念,於是她愈來愈擔心,害怕構成她孩子的所有、賦予她意義的一切可能都回不來了——包含她的談笑,甚至是哭泣;而身為母親的她束手無策。
母親名叫席瑞絲,女兒的名字則是菲比。以前也有過一個男人——但並非父親,因為席瑞絲拒絕以這個稱謂抬高他的身價;女孩甚至還沒出生,他就拋下母女倆,讓她們自生自滅。就席瑞絲所知,他住在澳洲的某個角落,不曾顯現出想參與女兒人生的丁點欲望。說實在的,席瑞絲對這情況很滿意。她對那男人毫不留戀,他的離去正合她意。她為他協助創造菲比而懷抱些許謝意,偶爾會在女兒的眼睛、微笑中看見一點點他,但稍縱即逝,就好像火車經過時在月台上瞥見、好像記得又不太記得的人影;看見了,但旋即遺忘。菲比對他也只展現出最低限度的好奇;儘管席瑞絲總是向她保證,只要她想,就可以跟他聯絡,但她不曾表達有此希望。他認為社交媒體平台皆出自惡魔之手,因此拒絕碰觸,但他的幾個熟人慣用臉書,席瑞絲知道若有需要,他們可以協助傳遞消息。
但不曾有此需要,直到那場意外。席瑞絲希望他知道發生什麼事,至少有部分是因為她無法單獨承擔那麼大的創傷,就算所有分享的企圖都無法稍減傷痛也沒關係。最終,她只透過共同朋友收到草草回音:簡單的一行字,通知她他為這場「不幸事故」感到遺憾、希望菲比很快康復,彷彿身為他骨肉的這個孩子只是感冒或出麻疹,而非在一場八歲女孩的嬌弱軀體與汽車相撞的重大事故之後重傷未癒。
席瑞絲頭一遭對菲比的父親萌生恨意,而且程度幾乎堪比那個一邊開車一邊傳訊息的白痴——傳訊息的對象還不是他妻子,而是女朋友,因此他不僅是個白痴,還是個騙子。他在車禍後幾天來過醫院,迫使席瑞絲在他有機會開口前就要求將他掃地出門。從那時起,他試過直接和透過他的律師聯絡她,但她不想跟他扯上任何關係,甚至不想告他,剛開始不想,不過旁人勸她非告不可,就算只是為了付女兒的醫藥費也好,因為誰知道菲比可能這樣半死不活地過多久:護士定期為她翻身,以免她脆弱的肌膚生褥瘡,而且她只能靠機器維生。菲比的頭在碰撞後撞地,於是,她身上的其他傷漸漸癒合,腦中的某個地方卻依然受損,沒人說得準她的大腦何時或到底會不會自行修復。
自此,一整套新詞彙呈現在席瑞絲眼前,一種解讀一個人在這世上存續與否的陌生方式:腦水腫、突軸損傷,還有對母親和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格拉斯哥昏迷指數,現在就是以此標準判別菲比的意識——延伸而言,或許還有她活下去的權利。睜眼、語言與運動反應低於五分,死亡或維持植物人狀態的機率就是百分之八十。得分高於十一,預估復原的機率則高達百分之九十。若是像菲比一樣介於這兩個數值之間,那……
菲比並沒有腦幹死亡;這很關鍵。她的大腦仍有忽隱忽現的微弱反應。醫師們相信菲比並不痛苦,但誰說得準呢?(這些話總是說得輕柔,最終還會像後來才想到一樣追加一句:誰說得準呢?我們真的不確定,妳知道的。大腦是個如此複雜的組織。我們不認為她會痛,但……)醫院內有過一場談話,過程中有人提議,若後續菲比沒有改善的跡象,或許放手——說到這裡時改變語氣,露出悲傷的淺淺微笑——才是仁慈的作法。
席瑞絲會在他們的表情之中找尋希望,但只找到同情。她不想要同情。她只想要女兒回到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