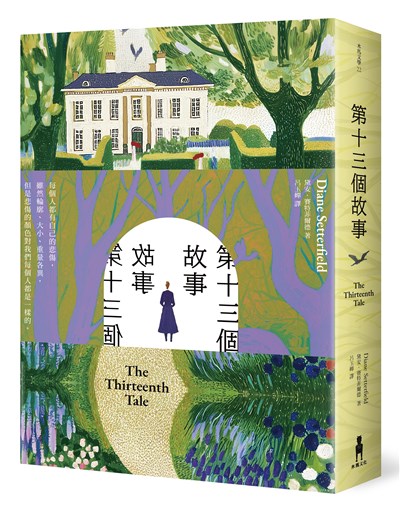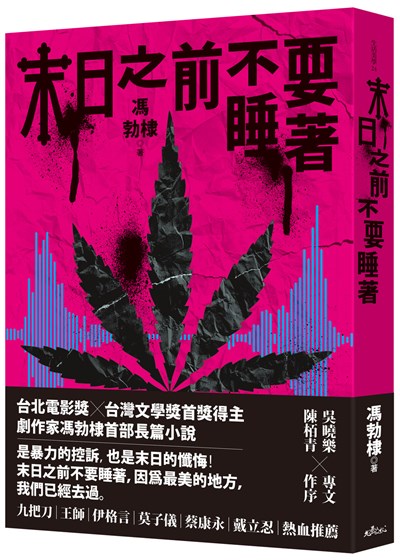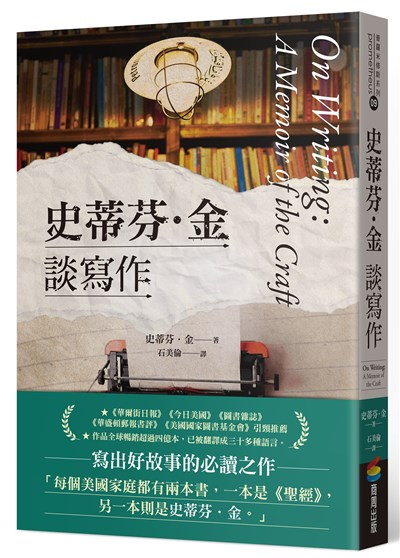
過去的史蒂芬.金和現在的史蒂芬.金兩個自我的精采互動,本書看到作者的成長背景、家庭文化,及自我磨練下的點點滴滴;前三章以作者回憶中所建構的幻想與兒時世界為主,並提及如何獲得靈感,從第四章開始為寫作技巧和寫作訓練。
與他以往的著作不同的是,這本書用回憶的方式,提供大家透視史蒂芬.金內心的機會,就好像他站在書房中引導我們如何構思情節,如何將主角帶入生活,何時該做研究,怎麼組織文章。他以說話的式來教導我們,不只是他如何執著寫作練習,還有他寫作的習慣和有些近乎病態的固執。
內容節錄
《史蒂芬.金談寫作》
瑪麗‧卡爾(Mary Karr)的回憶錄《大說謊家俱樂部》(The Liar’s Club)令我目眩神迷,不只是因為它的殘忍、優美,以及她對方言運用的精準描述,而是它呈獻出來的完整性。她是一位能記住自己早年生活中「每一件芝麻小事」的女性。
我就不是那樣,我有一個詭異又雞飛狗跳的童年,生長在單親家庭的我,小時候四處搬家。雖然我不是很確定,但我母親似乎曾經因為經濟和情緒因素無法應付,把我和我哥送到阿姨家住過一陣子。但也許她只是去尋找那個欠了一屁股債,最後在我兩歲、大衛四歲時逃之夭夭的父親。如果事情真是這樣的話,我媽終究沒有成功地找到他。我媽尼莉‧露絲‧皮爾斯貝瑞‧金,是一名美國早期自由解放運動中的婦女,不過那並不是出於她自己的選擇。
瑪麗‧卡爾近乎完整無缺地描述她童年的全景,而我的童年記憶卻像是霧中的風景畫,零星的記憶片段像是一棵棵與世隔絕的樹木—那種看起來好像會把你抓起來吃掉的樹。
接下來就是一些這樣的記憶,加上我對青春期和青年時期一些比較完整的短暫回顧。這並不是我的自傳,反而比較像是履歷—用意是讓大家瞭解一個作家是如何形成的,而不是一個作家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我不相信作家是「能夠」被製造出來的東西,不管是因為時機的因素,或是個人的志向(雖然我也曾一度相信這些東西)。「才華」其實是來自原始的本能,但並非是一種不平凡的天分。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多少都有一些寫作或說故事的能力,而這些能力是可以被加強和磨練的。如果我不相信這樣的說法,那寫這樣一本書只是在浪費時間。
對我個人來說,事情就是這樣—一種集結成長的過程讓企圖心、欲望、運氣,和少許的才華各自扮演一部分的要素。不用試著去解讀字裡行間的意義,也不用想要找到一句完整明確的句子。這裡沒有必須依循的線條—只有一些片段的回顧,而且大部分還焦點模糊。
1
我最早的記憶是把自己幻想成另外一個人—老實說,是幻想自己是瑞麟兄弟馬戲團(編按:創於十九世紀的美國著名馬戲團)中的大力士,事情是發生在緬因州艾瑟琳阿姨與歐瑞姨丈家,阿姨對此事記得非常清楚,她說那年我大概兩歲半或三歲左右。
在車庫角落裡我發現了一個水泥空心磚,並設法將它撿起。我抬著磚塊緩緩地穿越車庫裡平滑的水泥地板,但是在心裡,我幻想自己身上裹著獸皮背心(也許是豹皮吧),抬著磚塊穿過馬戲團的中央圓心;周圍群眾鴉雀無聲,一盞藍白色的聚光燈打在我引人注目的動作上。觀眾驚訝的表情說明了整個故事:他們從沒有見過如此強壯的小孩。「這孩子才兩歲大而已!」有人不可置信地竊竊私語。
然而我渾然不知當時黃蜂已在那空心磚的下半部築了個小小的巢,其中一隻黃蜂因為移動而被激怒,飛出來螫我的耳朵,那痛是如此鮮明,有如一個惡毒的啟示,也是我小小生命中所經歷過最大的痛,但那只在最初幾秒鐘。當我將空心磚砸在我光溜溜的腳上,壓傷了五隻腳趾頭時,我已經把黃蜂螫咬的痛完全拋諸腦後。我不記得我是否有被送去看醫生,艾瑟琳阿姨對此也沒有印象(歐瑞姨丈,那邪惡空心磚的主人已去世快二十年),但是她仍記得我被黃蜂螫傷、被砸爛的腳趾頭,和我當時的反應。「史蒂芬,你那天叫得多慘啊!」她說,「你那天的嗓音真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