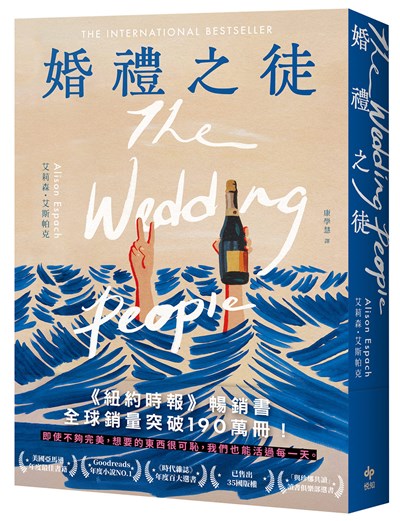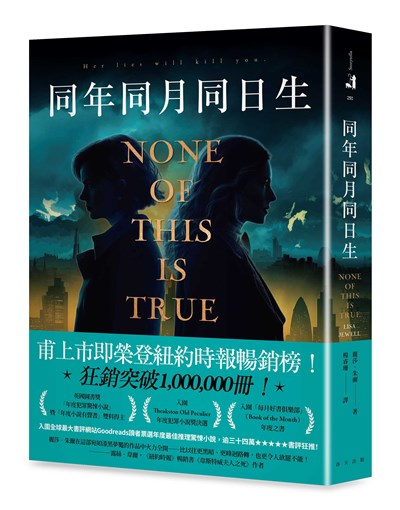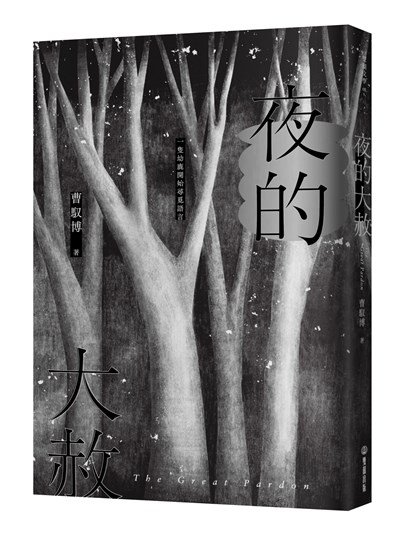
2022 Openbook好書獎-年度中文創作
評審推薦語/王榆鈞(決選評審,音樂創作者、歌者)
在刺眼的陽光下,讀著詩句,在躁熱中找到一處黑暗可以容身,也許那也是自己的影子。好像有另一個輕盈的身體遠遠地看著現實中在時間縫隙裡追趕著時間狼狽的身心,而能感覺到真實,因為真實而清醒。在無盡的夜與晨之間,讀著詩句,全然地擁抱一整片的黑暗,讀著詩句,靜謐地凝結成音符,無懼於死亡的晚禱,還有寬容。在通勤往返,司機大聲放著AM電台的背景中,讀著詩句,一字一句的叩問,特寫著與現實疊合的場景,在行間空白的地方,每一回再填上只能低下頭的致歉。
從「鑽石孔眼的複述」、「幽靈的複述」到「當幼鹿尋覓語言」與世界詩人交會的魔幻時空,或最後一輯「人工的光」,可以依序也可以跳耀著,或者反覆。尋著自己的韻律疊上一層又一層複述的黑,潛入一片黑色的汪洋裡,帶著哲思。突然發現空中飄散的灰塵,從窗口透亮的光中,成了房間裡的一條銀河。
曹馭博的作品像一團火焰,時而火紅、時而炙熱、時而溫暖,我只能一直凝視它們,深深入迷!靠近或者遠觀,端坐在一旁,看著這團火的變化,也在心裡點上一盞蠟燭,給世界,也同時給心靈的幽靈。
英文標題The Great Pardon.,Pardon這個字在英語與法語的意思非常不同,不知道詩人是否有潛藏的心意在裡面?夜的大赦,不用擔心讀不懂詩,不用急著找到詩,我深信會找到彼此指認的,無法言說卻可以辨識的,在容納一切的漆黑裡。
內容節錄
《夜的大赦》
橫的再移植 ◎唐捐
1
一隻好奇的幼鹿逸離棲息的母地,越山嶺,度溪流,來到一塊異地。
嗅聞陌生的枝葉,連空氣都換了一層新皮,那麼新穎、刺激而危險……。
問此鹿是誰?詩人曹馭博。問所覓者何?詩語與詩境也。在戰後展開的現代詩運動裡,「橫的移植」總括一套詩學觀念,「縱的繼承」則近乎拿來湊對子的廢話。於是十五年間(1956-1970),許多詩人競相投入「語言大煉鋼」的狂潮,煉成破銅爛鐵的固然不少,卓有成就者亦所在多有。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初,文化界與社會對先前的現代詩做了一場大審判,其結論大約是功過三七開。於是,詩的主潮遂從「西化」及其症侯群中痊癒,迎向健康的下半生;向陽曾將當時的新潮流總括為「回歸」二字,堪稱精準而明快。
曹馭博及其同代人開始寫詩的時候,我大華麗島的詩的星空已經十分燦爛了。我姑且取其影響力較大者而將眾星分為三大區塊:一是從洛夫到楊牧的黃金世代,二是以夏宇為核心的石油世代,三是以鯨向海為代表的晶片世代。這時如果有人要喇咧什麼「縱的繼承」的話,我想,馭博世代主要取法的對象斷不是灌滿抒情傳統的中國詩詞或未經轉化的鄉土民謠,而是臺灣現代詩自身的血脈。
更精確地說,這三家皆以各自的方式為我們示範了如何超越橫與縱,主知與抒情,自我與社會的糾葛。楊牧濡染現代派餘光,卻跑到「波特萊爾以前」去融貫中西傳統,遺世而獨立(其實頗不合群)。夏宇奇妙地契合世界性的後現代思維,成為「地球村的而不只是華麗島的」漢語詩人。鯨向海極熟稔各時期的台灣詩經典,但崛起於網路,展現出新世紀青年的價值、感受與趣味,在筆法上是一大解放。
自家藏經閣裡祕笈盈滿,學詩者目不暇給,得其若干招式已可表達萬千題材,進而形塑自己的風格。因而「西化」,或「橫的移植」的口訣,久矣不被最新世代視為突破的要訣。──我的意思不是說,年輕寫詩者不知我大華麗島外有詩,不知世界詩壇萬紫千紅競開;而是說像曹馭博這樣,不無誇張地,吸收西洋當代詩(或稱為翻譯詩)的句法、情調與題材,還是極為醒目提神的新鮮事。
2
不甘平凡的新詩人都是「修正主義者」,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2019)早言之矣。從前的人向西方借火,是在寂寥的星空裡布置自己的星座;遲到的詩人重新開機,則是為了消解今夜星空燦爛的重量。這一回,馭博的新詩集罕見本地大師乃至學長們的腔調,但多諾獎詩人們的身影。他在相當程度上擺脫了前者,但恐怕還須面對被後者加持的焦慮。若是放回五十年前,大力討伐洋腔中文詩的關傑明博士必然會說,同學,你這樣不行。
我覺得可以,頭好壯壯的幼鹿舉起新興的角枝,自信地應答。非但可以,曹馭博根本是明著來,他拜請域外的神明,並與祂們展開無盡的遊戲:
博拉紐朝我開了三槍
他堅持我抄了他的點子
我們一路追逐
城市,荒漠,濱海小鎮。
在大口徑手槍的眼睛下
我說:「帕拉已經過去找你了。」
博拉紐放下手槍
哭聲像中提琴的聲響
絃聲每拉長一次
寂寞上漲一尺
你看,神明A來夢中跟阿博索討綵筆的時候,他的回答竟是你自己那支的筆毛也有一撮偷偷剪自神明B家的狼與兔……。但這裡用的不是筆的隱喻,而是更可怕的槍,看來前後詩人之間的債務真是不好清理。
輯三「當幼鹿尋覓語言」,共提到十九位詩人的名字,簡直如「點鬼簿」(很多神明是鬼去當的)。我想,馭博做了一場「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式的大夢:他像一個時空穿越者,陪這個詩人逛書店、聽德布西、剝橘子,又與那個詩人一起焚滅手稿,體驗憂鬱的毒箭;有時忙著爬到樹上看阿赫瑪托娃在冷身體與熱石頭之間,閒來便奪取策蘭的惡夢如借走一件黑色的大衣……。這樣的作品似乎只是讀書札記或意象與句法的練習,但又不僅於此。馭博無意間展示了一種無邊的「共時性」,世界經典詩篇中的情境與感受,皆可以是「我」的現在與這裡;或者反過來說,一個勤讀世界詩歌的台灣青年詩人,覺得自己可以穿梭於異國異時的詩意脈絡,體會其獨特性,並共享其普遍性。
在這樣的思維與之下,詩人彷彿取得神奇的「鑽石孔眼」,可以窺破各種隱祕的情境;又好像是「幽靈」,可以襲取他人的經驗。這本詩集裡的大部分篇章,都出現了「我」,但不知道為什麼有些句子(在我聽起來)像是飽歷劫難的外國詩人在說話。比方說〈餘像〉,意象與句式皆不俗,但閃爍其辭,似乎還須多給一點背景或提示。又比如說〈憂傷給了我太陽〉,顫慄不知因何而起,「你」又是因何而閃現。我是這樣猜想的:馭博詩裡的「我」,可能是一個集合體,他在諸多奇妙瞬間分享了各種倖存者、流亡者、耽思者、孤獨者、垂危者的體驗。
3
這本詩集有好些詩篇都採用了雙行體與三行體,富於均衡簡潔之美。但由於分段頻繁,「空白行」也比較多。馭博充分利用這樣的體裁,營造出碎片化風格,例如〈將死之人〉裡的這個片段:
車燈:面對大地的廣角鏡
黑影釋放了黑狗
使牠飛奔回屋子裡
句法緩急有度,意象飽滿,且能夠為題旨而服務。光影之靜與動,恰恰扣合「將死之人」腦海裡的浮光掠影。這個畫面自給自足,儼如小詩。後面的幾個段落也都有各自發展的態勢,好在題目比較明確,讀者不致失去理解的方向。
空白行隔開詩意單位,留下想像空間;但在馭博的詩裡,「空白」已躍為重要的技巧,乃至詩意元素。他不太說明或闡釋,或者說,他比較願意通過意象來表演。我姑且從〈早晨的暴力〉中間摘取四個段落:
幽靈為了解釋世界
誕生的引文
我對這份光明充滿感激
於是我保留眼睛
直到黎明的卡車
將街道像瓷器一樣震碎
一隻蜻蜓陷入柏油
裂痕的手將它拖回黑暗底部
句子很厲害,自不在話下,但這裡好像有種不連貫性。幽靈、卡車、蜻蜓,那樣紛紜地展布開來。也許空白行給詩人帶來機會,使他更猛於切斷意脈,跳到另一個畫面。這便造就了此集極端鮮明的風格:聲調冷峻,思維沉重,意象濃度高,敷衍性的語句降低至極。
風格來自詩人的性格、文學血脈與審美期待,但也關乎時代、社會與題材。老式現代主義吞吞吐吐,隱晦其言以便觸及性與死與虛無,蓄積巨大的反諷去描摹社會,或有其表現上之需要,或緣於外部的壓力。馭博敏於吸收二十世紀大師的技術,同時也感染了他們的思維與憂患;但做為一位當代青年詩人,他關懷所及,自應包含眼下的世界。以〈死於溝渠〉為例,根據首段,似乎是為「許多孩童正在逝去」而發的悲悼,其中幾個段落是這樣:
喪失乖違的舌頭,失去重量,再度跌進內部
一個胚胎漸漸擴張光亮,君臨水底的青石頭
閃耀的水宅,幽閉的泥底,一具屍體
他的十字吊墜懸盪於喉頸,金屬聲
發狂地向缺席者哭泣,也許是一位母親
正在旁觀審判,但又涉入其中。
明明可以說得直爽些,但我們看到詩人依然選擇了一種老現代主義的腔調。我猜想,這是一幕溺死的畫面,沒什麼不能說的,但詩人不想說明白。他或許這樣想,惟有這樣隱晦、斷裂、宏偉的語言才能建造出意想中的詩境,並表達最深刻的悲痛。沒錯,任何一首唐詩都不可能精準地以白話譯寫出來,馭博這類詩篇也不容易用散文加以複述。它們反口語,反敘述,可能也反寫實,近於一種新的文言詩語。馭博選擇了這種高難度的唱腔,自有其美學堅持,而他確實也唱出迷魅,令人讚歎。
4
以馭博句法之犀利,我覺得多點敘述,多點口語,多點事實,必能橫空一世。輯二「幽靈的複述」有不少作品,或許已臻此境,有些則仍在試探中。〈石頭裡有沉默的巨僧〉後面兩段,設想奇詭,意象頗驚人。但坐在車廂裡沒事去想軌道顫動都是「對死亡的抵觸」,終非良策,事情撐不起這麼隆重的語言。相對之下,〈貝莫加醫院〉寫遭疫情慘虐的異國醫院,雖亦著迷於意象表演,但以時事為背景,具體可感,又能臻及象徵的層次。
接下來的四首詩,都具有極鮮明的敘述性與在地性。詩人不再穿越到異時他方,而只是凝神捕捉眼前的現實,自有一股奇幻的韻味。各取一段為例:
入伍後的第一個清晨
隔壁的鄰兵說
他的父親病危,就要走了
金色的手拉起影子
遮滿了集合場
我分不清誰是誰的影子──〈記事〉
例如叔叔。二十年前
卡車載走了他的脊椎
但依舊保留他的引擎──〈人的引擎〉
他對自己說,沒什麼好傷心的
只要玄孫出生,他就成了祖宗
或是神龕上永遠苦悶的面孔──〈影印店〉
我看著她,眼對著眼
發現她的眼睛已經死了
像她母親的靈魂──〈吃冰淇淋的女孩〉
第一例意象讓位於敘述,這種退讓使得詩的情境空間變大,意象還是有機會回來。第二例很神,完全寓意象於敘述之中,舉重若輕,近乎完美。第三例為故事之一幕,明朗可辨。第四例以句法取勝,淺白而有深意,同時故做鎮定。有了這樣從容的語句來調度情節,一切想像都有了依憑,那些詭異奧妙的意象也就會呼吸、可感應、能伸展了。
曹馭博於西洋詩看得廣,想得深,他能夠掌握的句型也是多端的。這一輯有首詩就叫〈小說〉,裡面有血有肉,還真像小說;但結尾處若有機心的安排,又使它成為寓言。這兩種成份(小說與寓言)在敘述體中各有千秋,但我感覺馭博似乎較著迷於寓言(雖然他其實頗具小說的能力)。像〈交流道〉裡的母子對話,空間、對白、象徵物是那麼精密地布置開來。更詭異的是〈我的屋子裡空了一間房〉,詩人在「房東」的位置說話,歷數各式奇葩房客,敘述性很顯著,同時具有寓言假託的力量。
寫詩有種技法,可簡稱為「我不是我」,馭博頗優為之。這不同於角色明確的戲劇獨白,而是流轉八方,介於虛實之間。剛才提過的那首〈交流道〉固然如此,即便是在〈前往二樓手術室〉,我們也搞不清楚這是取材自切身的體驗,還是假借、代言、託寓。從這個角度來說,逃離或者虛懸詩的「自傳性」,使得曹馭博詩的涵容量遠較同世代更為廣大,但可能也是他的詩不好詮解的原因之一。有能力當「幽靈」,出入於神人的客廳,習得奇功妙技,固然是極令人羡慕的事情。但偶爾回來試穿自己的肉身,使體驗優先於意象,感發優先於句法,那也是不錯的。
馭博的「橫的再移植」,未必已竟全功;但他打破穩定與習慣,注入新資源,練得神乎其技的詩法,預告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鮮美消息。歷史上的「橫的移植」自有一種偏激任性之意,但那也正是詩藝狂飆的年代,很快就要佳作紛陳了。今世之人,愛讀清甜的素人詩,渾不知「藝術之所以能偉大的呈現在我們眼裏正是由於技巧的偉大」(白萩語)。我讀《夜的大赦》,深識這是極難得的技巧之復興,未來的詩壇英豪航向遠洋的前夕,一場華美的文字的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