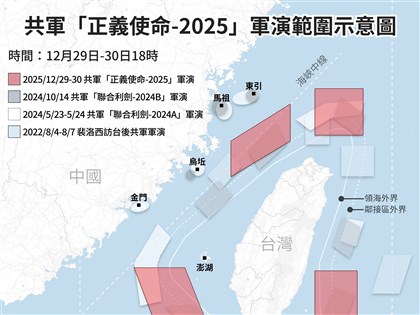芥川賞小說家平野啓一郎:文學應為世界帶來希望【專訪上篇】
文:黃淑芳
今年春天,日本「芥川賞」得主平野啓一郎終於來到台灣。這趟原本排在2020年年初的行程,因為COVID-19疫情,足足延遲了3年。3天旋風式訪台期間,平野面對的是已經讀了長篇小說《日間演奏會散場時》《那個男人》、看完改編電影,正在讀台灣剛出版的《分人》,把握每個公開活動機會向他提問、捧著書來簽名、眼神會發光的讀者。仔細觀察平野的創作歷程,你會發現他非常看重讀者的反應,不是為了迎合讀者而寫或不寫,但讀者的閱讀體驗、反饋意見背後顯示的意涵與情緒,他都會在思考、沉澱後,以創作來回應。
平野啓一郎在官方網站首頁寫著:「我一直希望寫出讓讀者『想翻頁又不想翻,想永遠沉浸在那個世界裡』,而不是『翻頁停不下來』的小說。」進入他筆下的世界,你確實會有這樣的感受,他把小說料理得很容易入口,但第一次讀、第二次第三次讀,你會在不同的地方停留、回顧,忍不住去接他拋給你的問題,不斷思索,然後實踐他的信念:現在可以改變過去(的閱讀經驗)。
這一次,他來台分享貫串自己十餘年來創作主旨的文集《分人》,這是他大力推廣的思考架構,若把個人分為面對各種不同對象時的更小單位「分人」,就有機會透過有意識地調整不同分人占比,找到自我認同與生存的力量;這本書在日本確實拯救了許多遭受霸凌的痛苦靈魂,甚至被選為中學教材。
中央社專訪這位日本中生代重量級作家,聽他談談大受好評的改編電影「那個男人」、出道以來背負「三島由紀夫再世」封號的心情,以及讓許多讀者氣到不行的《日演》男女主角分手理由到底為什麼這樣安排。平野也大方分享了他的思路與創作技巧,值得讀者與寫作者細細品味。
中央社(以下簡為「問」):電影「那個男人」正在台灣上映,這部電影獲得不少國際影展好評、日本奧斯卡13項入圍。您近年兩部長篇小說拍成電影,製作陣容都很華麗。我個人更偏愛「那個男人」一點,那幅「禁止複製」畫作的處理令人印象深刻。這部電影您已經看了好幾次,可否與我們分享您最喜歡的一幕?您有多部作品陸續被影視化,授權改編時,您最在意的是什麼?
平野(以下簡為「答」):《那個男人》有多家電影公司來談合作翻拍,我最重視的是導演跟電影公司用什麼樣的企圖心翻拍,在眾多組合中挑選了後來大家看到的石川慶導演跟松竹電影公司這個組合。若看過原著會知道,它的推理性很強,可以拍成較有娛樂性質的電影,但小說強調歧視、什麼是真正的自我等哲學性議題,石川導演一開始來提案就告訴我,他們對翻拍最重視這一點,這也是我看中他們的原因。
一般要把長篇小說改編成電影,勢必需要刪減,若只用簡單的擷取刪減,往往會跟原作有出入,需要透過導演的巧思去做連結甚至改變,這一點石川處理得很高明。「禁止複製」這幅畫在原著裡只有一句話,也許很容易被忽略掉,但它是很重要的象徵,象徵了人如何從他者之中找到或映照自我,導演巧妙利用這個象徵,把它在影像裡表現出來,我非常喜歡。
另外,電影裡有比較多篇幅描述里枝與X婚後幸福時光,原作裡沒有這麼多。藉由這個幸福的描述,讓X過世後的悲傷感,對比更加明顯,這個改動我也很喜歡。
影視化的過程相當複雜,一旦影視化它就是獨立的作品,尊重導演的意願與創作自由。當然我希望導演在確實理解原著的前提下發揮創作自由,因此我會在合作初期了解這點,確認之後,我就不會有太多意見。
問:讀完《分人》,我試著用分人的角度重讀《日間演奏會散場時》《那個男人》,得到一些新體會。這兩部小說讓個人意志碰撞宿命論,主題不同,卻有很多共通元素:倖存者罪惡感、魂斷威尼斯症候群;即使不像上世紀戰爭不斷,現代人的苦難並沒有比較少、生存挑戰也沒有比較小。不過,兩個故事最後都開出帶著愛與希望的花朵,這是您想透過文學傳達的信念嗎?
答:每次寫小說,都會非常煩惱結尾到底要怎麼收束。我過去有一部小說《決壞》,描寫一個悲傷的故事,收在一個絕望的結尾,很多讀者說讀完雖然很感動,但不知道拿那個絕望的感受怎麼辦。也是在寫這本書時,我發現「個人」這個想法來到極限,沒辦法再推展下去,所以在下一部作品《曙光號》提出「分人」的概念。
常有人批判說寫快樂結局(happy end)是商業取向、只是為了討好讀者,但我不這麼認為。既然有這麼多讀者在讀虛構小說時期待一個快樂的結局,就表示大家有這樣的需求,想要在作品裡追求一些希望、比較光明的東西。我過去也曾和其他作家對談提到此問題,對方說所謂的快樂結局,是人類經歷漫長的時間一直在追尋的主題,我很同意這點,所以小說的最後,我還是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希望。
當然,如果小說結尾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未免太過理想化、不切實際,但一本小說裡有非常多的人、非常多的問題存在,不是只處理一件事。例如《那個男人》里枝的丈夫死了,她必須一個人帶孩子長大,是很不幸的結局,但在不幸的結局當中,我們看到她的兒子對未來有了正向的期待,似乎可以從少年的成長中看到一些希望。
故事到最後,我會讓它變成有些問題解決了、有些問題沒有解決,呈現對讀者來說整體而言可以接受的狀況。我也希望即使不是快樂結局,仍然可以找到一點正向的收尾。
問:《日演》相愛的兩人面對對方的分人如此相像,既幸福又自卑,想要仰仗對方擺脫當下的困境,又怕成為對方的負擔。蒔野與洋子分開的理由,我和幾個朋友讀完第一個反應是生氣,竟然是因為這種肥皂劇般的理由,再讀第二次、第三次,就比較能夠接受,正因為是兩個中年人,才會出現這樣的結果。您為什麼選擇這樣的設定?
答:世界上有很多讀者跟你有相同的感想。有位美國的讀者在Instagram這樣寫:「一開始讀很感動,看到中間我實在看不下去了,決定把書合起來,但過一陣子重新把書拿起來看,感動到落淚。」這也許可以總結大家的閱讀經驗。
一般人讀小說都會希望裡面的東西是自己接受、認同的,但若一本小說全部都是你認同的東西,讀者就會相當被動,被動地接受這本書傳達的東西。如果在書中加入讓人覺得「這個角色怎麼那麼蠢啊」「怎麼可能有這樣的事啊」的情節,讀者就會本能地想跳進書裡面跟他們對話、搖他的肩膀說「怎麼可以為這麼小的事分手啊」,產生這種自發性的情緒,這樣一來讀者不是只接受故事,甚至會跳進故事,或跟朋友討論,書與讀者就會產生連結。所以我不太喜歡在書裡寫一些大家都覺得合理、可以接受的事情,我認為加入一點大家覺得莫名其妙的事,會激發讀者想要參與,主動跟這本書建立關係的可能。
寫這種橋段時,重要的不是讓讀者抱怨作者怎會這樣寫,而是讓讀者想跟書中的角色講些什麼。這種情境有點像我們在現實生活裡聽朋友聊戀情,會冒出「有必要為了這麼小的事分手嗎?」或者「這樣不行喔,趕快分手」等意見。如果我的意圖成功的話,讀者會想要跟我書中的角色對話。
另外,我特別關注宿命論與自由意志,人都希望可以憑自由意志開創自己的人生,但有時候會因為陰錯陽差,或做了事後會覺得荒唐的決定,改變了一生。這是《日演》的主題,它也被濃縮在這個橋段裡。
問:《日演》最後看似開放式的結局,您心裡有自己的答案嗎?
答:這部作品當時在報紙和網路同步連載,留言非常踴躍。這個連載很像馬拉松,接近終點時,有很多人在為你加油吶喊,我聽到非常多讀者的聲音。讀者很關心蒔野和洋子到底會不會重逢,甚至有人直接來問我說:「他們會重逢吧!」「如果他們不會重逢,到底怎麼收尾」,反應很熱烈。
這些反應該我有種很奇怪的感覺。如果你身邊有朋友遇到戀愛問題,他們到底要不要分手,跟我們其實沒什麼關係,可是讀者相當認真地希望男女主角重逢,比自己的事還關切,我覺得這樣的現象實在相當有趣。
我原本對他們倆重逢之後的故事是有一些構思的,但讀者對重逢之後的故事意見分成兩派,一派認為蒔野應該離婚跟洋子在一起,一派認為他們不應該再見面,總之對於兩人之後的故事有很多很多討論。我覺得難得一本書可以讓大家這麼熱烈的討論,我不想用我自己的結局破壞大家的想像,所以就讓故事停在這邊。(編輯:簡莉庭)1120220
- 2025/08/27 15:06
- 2023/02/28 10:26
- 2023/02/19 15:07
- 芥川賞小說家平野啓一郎:文學應為世界帶來希望【專訪上篇】2023/02/19 15:07
- 2023/02/12 09:59
- 2023/02/06 10:19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