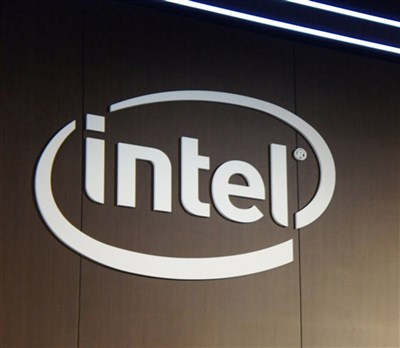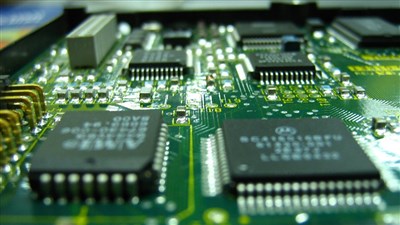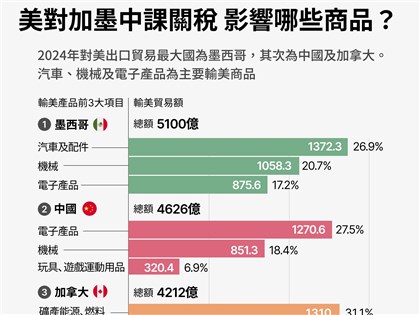余英時憶哈佛盛世 一語中的評費正清、杭廷頓與福山【書摘】
(中央社網站)史學大師余英時今年8月1日辭世,讀者再也等不到《余英時回憶錄》續集。2018年出版的回憶錄僅寫到他在哈佛大學求學階段,幸而當年前往普林斯頓拜訪余英時,與他暢談多日的作家李懷宇留下大量談話紀錄,兩人持續聯絡往來,余英時後半生治學、與學界大儒的往來與所見所思,可從李懷宇的筆記窺見一二。
允晨文化在余英時過世百日之際整理出版《余英時談話錄》,余英時弟子、中研院副院長黃進興形容這本談話錄「披沙揀金」,有系統地整理余英時對近代學術人物的觀察、個人的學思及時代的見證,可視為《回憶錄》的續編,價值甚高。
讀史學家臧否人物很有意思。《余英時談話錄》白話、簡潔,彷彿聽著余英時面對面聊天,他評論以「文明衝突論」一砲而紅的杭廷頓,以及提出「歷史的終結」的福山,可以說是一針見血,精闢中的。中央社取得授權,刊載部分內容與您分享。
哈佛名家雲集
1967年,我拿到哈佛大學的長期聘約,1969年拿到正教授。哈佛大學在美國學術界是很重要的學校。學生、教授多,現在哈佛還是比其他學校更有資源。那時候倒有一些特殊的人物都集中在哈佛。包括日本學也是一樣,賴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 1910-1990)是當時受公認的高峰。中國史方面有楊聯陞、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費正清,都是「不世出」的人物,以後就沒有了。同時,也要承認華盛頓大學也有很好的學者,像蕭公權、李方桂,不過影響沒有像哈佛大學那麼大。
薩繆爾·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1927-2008)是政治系的教授。當然史華慈也在政治系,他們兩人之間沒有好多交往。我跟杭廷頓的關係,就像「但是先生」史華慈跟他一樣,我認為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好好消化,不大準的。史華慈不會做這些概括性的討論。兩人的路數完全不一樣。從歷史觀點來看,我們不會找一個大理論籠罩一切。杭廷頓在公眾層面影響很大,但是在學術界來看,一半是學術,一半是新聞。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講「歷史的終結」也有一半是新聞的觀察。這種提法容易引起討論。歷史有沒有終結?根本就難講。福山的「歷史的終結」是講從前蘇聯是很大的威脅,以為民主自由不行,現在看來,只有民主自由這一套可以繼承下去。原來歷史概括像馬克思主義沒有了,這是他講的「歷史的終結」。這種觀點主要是有刺激性。
我跟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21-2002)沒有交往。他是哲學系的教授。羅爾斯的《正義論》是經典著作,那是劃時代的,百年不見出一本。他後來的東西超過《正義論》很多,講政治自由主義等其他的論文也是很重要的。他的基本功夫在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從康德的歷史慢慢發展出來。普通人去聽羅爾斯的課,是聽不懂的,只能聽到表面的東西。
1966年到1977年的哈佛大學是盛世。我離開哈佛大學以後,費正清退休了,楊先生也退休了,便換了朝代。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沒有大師。還不光是哈佛大學一校,各行各門的學問多元發展。隔行如隔山,很難產生大家公認的大師。這倒不一定是衰落,而是變化了,多元了,沒有人能籠罩一切。這是時代的關係。
費正清的中國研究 開風氣之先
在哈佛大學,我和費正清認識了幾十年,一直到他退休。費正清最初研究中美外交史,研究從海洋上的溝通是怎麼開始的,主要用的都是西方檔案材料,或者英國國會的領事館報告。當然,蔣廷黻參考的《籌辦夷務始末》是從清朝衙門出來的歷史檔案,費正清也運用《籌辦夷務始末》的檔案,但他主要是靠西方材料。後來他研究傳教士,也是以西方材料為主,不需要那麼多的中國材料。他也研究清朝本身的制度,這樣往往就跟中國人合作,譬如,早期跟鄧嗣禹合作,研究清朝的制度,後來最得利的人是現代史專家劉廣京。他翻譯中國對西方的反應,都是從晚清專家寫的文章裡面挑出來,跟鄧嗣禹合作翻譯成英文。如果用西方的觀念看,費正清絕對是第一流專家,不能說他中文不好,就不能講中國史,他主要是靠西方的原始材料配合中國方面的研究。當然,他在語言上是有些限制,但是他的貢獻不是在這裡。他是領導型的人物,不但研究近代史,還把它往前推。
因為在哈佛大學的關係,費正清利用哈佛圖書館的資料,與重要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洛克斐勒基金會建立關係。他為哈佛大學拿到的錢大概比任何學校都多,這樣他才可以成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他是創始人,一直到差不多退休才讓出來。在這中間,他有許多錢可以請好的學者來做研究,像黃仁宇到那兒研究了一年,寫了明代的稅制。同樣的例子很多,重要的學者大概都在那個研究中心待過。在那個研究中心一兩年,拿了博士學位,再把博士論文變成書,這是很重要的。
費正清很有風度,很客氣。費正清的岳父堪農(Walter B. Cannon, 1871-1945)是哈佛醫學院最有名的學者,常常到中國去。費正清的妻子費慰梅(Wilma Cannon Fairbank, 1909- 2002)對中國書畫、銅器、雕刻都有興趣。費正清先跟她交朋友,波士頓藝術館是世界有名,收藏中國古畫多得很,他從看中國古董開始,慢慢發展到對中國研究有興趣了。所以, 費正清研究中國,確實是對中國有情感的投入,有理智的投入,情感和理智基本上相合。很少有人勉強去念中國史,這樣是念不好的。
我和費正清私人交往不是很多,就是去對方家裡吃過飯,他忙得很,我如果沒什麼事不會上門找他,想和他談,可以去辦公室。我到耶魯大學之後,有一度他讓我和他合作,改寫中國教科書,我嫌麻煩,沒參加。後來他和賴世和一起寫的,是很權威的書。
最好玩的是,鄧小平去白宮訪問,費正清收到請帖,要去陪鄧小平吃國宴。當時我已經在耶魯大學任教了,他收到請帖之後從哈佛打電話到耶魯,用英文問我: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中文原文是什麼?我告訴了他,知道他大概是要跟鄧小平說。我心裡想:可能那時候楊聯陞先生身體不好,不方便問他,本來費正清是應該問楊先生的。
我們不把費正清當作純學者來看待,而是學術界的領導人。他提倡學術研究,是開風氣的人,不是純粹念書的書呆子型和學者型,是事業型。因為他的中文到底還是不夠好,看資料沒那麼快,他早期寫的中國沿海貿易之類的東西,都是靠英國、美國、法國和香港的英文檔案。早期中國的英文材料很少,後來用到中國資料,很多都是助手幫他忙。他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基本上是靠中國的助手幫忙。當然他自己也努力不懈,主編了很多西方在中國傳教的歷史,規模很大,推動了整個近代史的研究。他這種人只有在特殊狀態下才能產生的,像現在就出不了這樣的人了。
在美國,如果要說「漢學」,人家就知道是在18世紀以前,不是近代。近代不叫「漢學」,像費正清的研究不叫「漢學」,一般通用名稱叫「中國研究」。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也可以說從前歐洲有「漢學家」。從前有研究各種語言的學者,特別是像法國人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是歐洲最有代表性也是影響最大的漢學家,懂得13種語言,敦煌的卷子就是他去挑的。伯希和在北京法國大使館住了很久,能自由進出中國,就到敦煌去挑。他懂許多種語言,不但有漢文的,也有非漢文的,他精選了許多經卷,經過北京,就告訴中國學者像羅振玉有這樣的寶貝,這樣清朝人才到敦煌去收拾卷子,運到北京來,一路上中國官員偷的偷,搶的搶。所以,當年敦煌的卷子留在倫敦和巴黎是運氣的,當然可以說帝國主義搶了,但是這個搶是對文化有利的。
在哈佛大學,日本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賴世和當過日本大使,他太太是日本貴族。費正清和賴世和,一個是中國研究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是日本研究的最高領導人。美國各大學教中國史的人,很多都是費正清的徒子徒孫,現在是曾孫一輩了。(書摘由允晨文化授權,編輯:黃淑芳、簡莉庭)1101110
書名:余英時談話錄
作者:余英時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21/11/12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