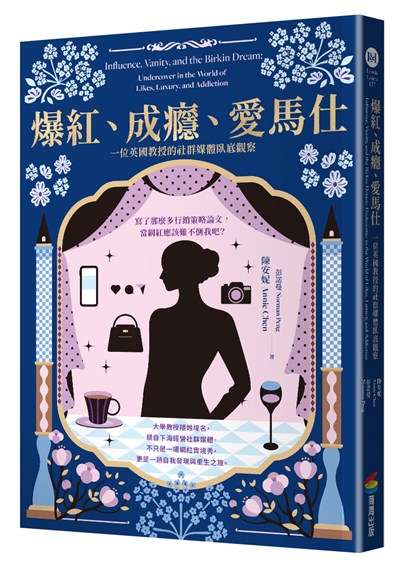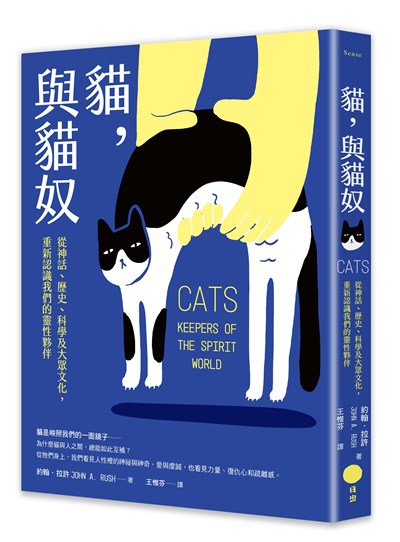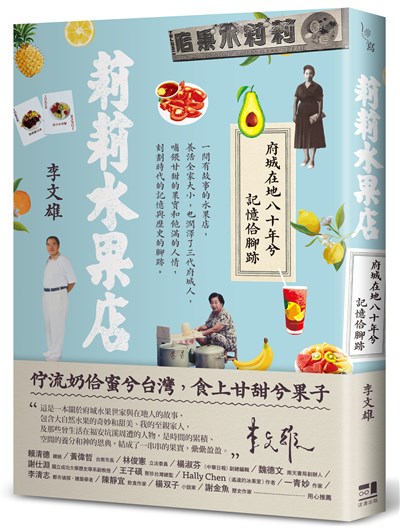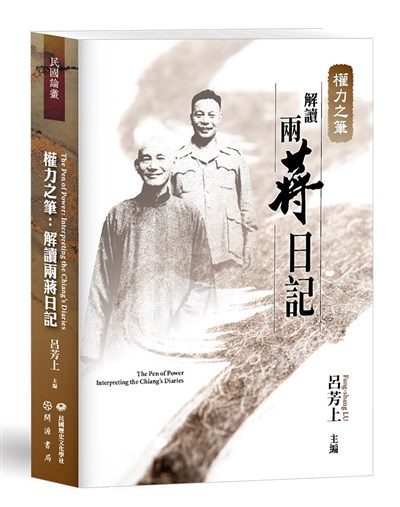人們談論當今最大的挑戰時,不論是環境污染、錯誤資訊、AI、愚昧的執行長和政客時,往往都說是「壞人」做了「壞事」。
但其實情況並不這麼單純。說穿了,人類天生就會為了短期成功而犧牲長期福祉。曾在英國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任職的企業家羅恩,把這種根深蒂固的衝動稱為「達爾文式惡魔」。
這些力量是天擇的副產物,會引導我們做出傷害他人的短視行為,甚至阻礙人類的續存。若這種演化缺陷沒有受到控制,後果會隨著科技進展而更加嚴重。
在這本令人大開眼界又振奮人心的書中,羅恩指出我們必須合作,才能夠避開這些日常生活中的演化陷阱,並且解決最嚴重的生存危機。
陷阱雖然是演化設下的,但是人類沒有必要踩進去。解救方式是創造出一個新系統,讓系統本身激勵人們做出有長期利益的選擇。羅恩稱這樣的新動力為「達爾文式天使」,能夠理解、追蹤和實現人類最為看重的核心價值。
《達爾文陷阱》的文字率直,充滿樂觀,能讓讀者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我們所處的世界和其中的問題。並且讓人重新思考對於後世子孫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內容節錄
《達爾文陷阱:人類該如何擺脫自掘墳墓的命運?》
隱藏在《汪汪隊立大功》背後的惡魔
2017 年,《紐約時報》的一篇頭版文章詳細說明了YouTube Kids 上令人不安的趨勢。那是廣受歡迎的影片分享服務的兒童版,每個星期的點閱次數超過一千一百萬次,絕大部分來自於幼兒。因為家長相信,平臺提供的影片適合兒童觀看,能夠讓孩子轉移注意力,並且得到娛樂。但是在卡通與教育影片之下,隱藏了數量驚人的詭異且不當的短片,並且以適合闔家觀賞的內容,加以包裝。
那些影片通常是走紅卡通的廉價未授權仿冒品、備受喜愛角色的拙劣仿製品,做出了極度偏離期待的行動。《紐約時報》報導在其中一支影片中,以大受兒童喜愛的《汪汪隊立大功》角色的「粗俗」版本為噱頭,那些角色會在車子撞上燈柱並且著火時尖叫。其他的影片還包括「黏土蜘蛛人尿尿在《冰雪奇緣》的艾莎身上,以及小尼克兒童頻道中的角色出現在脫衣舞酒吧中。」
這些不恰當的影片一開始是怎麼出現在YouTube Kids 上?問題的答案和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達爾文式惡魔,有直接關聯。上一章提到,這些惡魔般的選擇壓力會鼓勵我們盡力完成狹隘的目標,並且以非常特定的方式進行評估。在這些惡魔的影響之下,我們採取的選擇與策略可能提高短期的生存機會,但同時也會以出乎意料的方式傷害環境。
要瞭解這些目標狹隘的最佳化策略是怎麼嚴重傷害YouTube Kids,先得瞭解一下應用程式(App)強大的演算法。絕大部分的觀眾在使用YouTube 時,一開始是搜尋特定的上傳者或是影片。但是在看完了想看的內容之後,YouTube 希望你能夠留下來看更多影片。為了達成這個目的,網站利用了複雜的推薦引擎。人類在推薦時,根據的是內容品質和原創性,但是YouTube的演算法則多少有點不受內容所限。YouTube 是納入了其他許多因素,例如影片的標題,或是今天流行的話題,甚至是使用者以前看過哪些影片,就此來決定哪些影片要推薦上來,哪些要隱藏起來。也因此,許多專業的YouTube 影片製作者,覺得被迫要為演算法飄忽的好惡來製作影片,畢竟演算法握有生殺大權,決定了影片是否能吸引到夠多的點閱,以便賺取那微薄的廣告收入。換句話說,觀看YouTube Kids 的兒童並不是那些恐怖影片的目標受眾,演算法才是。
觀看YouTube Kids 的兒童,可能一開始看的是合法的《汪汪隊立大功》,但是接下來,應用程式可能會開始給兒童觀看那些在演算法看來是相似的內容:表面上看起來和最初的影片相似,但實質上是不同的。最後,兒童看到的可能是廉價的仿冒影片,其中假造的《汪汪隊立大功》角色遭受到嚴重車禍。與成人及青少年不同,幼兒可能無法區別這兩類影片的差異。也由於正牌影片和仿冒影片都正中演算法的紅心,YouTube Kids 也無法區分這兩類影片。
所以想像一下,現在是2017 年,你是上傳了影片到YouTubeKids 的創作者,想要盡可能滿足演算法的需求,以便把獲利提到最高。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合理的方式是搞出高利潤、低成本的垃圾影片,而不是投入許多心力製作出原創影片。
事實上,一如作家布萊德爾(James Bridle)於2017 年在網路平臺上發表過的文章所說,顯然許多造成問題的影片,根本是由AI 軟體做出來的,生成方式是根據提示,產生了大量影片,其中某些便剛好有超出法律規範的內容。那些是AI 軟體為了AI 演算法所打造出來的內容,受到池魚之殃的是不幸看到影片而遭受心理創傷的兒童。
達爾文式惡魔如何統治世界
《紐約時報》採訪的家長對這類造成不安的影片出現在自己孩子的螢幕上,大為火光,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位母親說:「我可憐的小男生是那麼的可愛,而有些可怕邪惡的人製造出那類的玩意,折磨了小孩。」
製作這些影片的人當中,當然有些人可能真的具有反社會人格。但是我認為,這些不當影片與其說是邪惡之人的作品,不如說是YouTube Kids 扭曲的激勵措施造成的產物。
用我之前提到的達爾文學說來看,這裡的選擇壓力是廣告收入。看某支影片的人愈多,製作這支影片的人就賺得愈多。製作者為了增加點閱數量,必須遵守演算法的規則,這樣影片才會浮起來,推薦給觀眾。
因此,對於影片製作者而言,適應行為便是盡可能大量製作能夠受到YouTube 演算法挑選的影片。而負面影響是:製作這些影片顯然是為了娛樂兒童,到最後卻讓兒童恐懼不安,這使得父母從此不想讓小孩觀看YouTube Kids。
在適應選擇壓力的過程中,影片製作者的個人生存問題和普世的社會價值觀,兩者之間並不相契合,最終將為整體社會環境帶來不小的破壞。
從比較巨觀的角度來看,YouTube Kids 的問題也發生在其他當今最受歡迎的社交平臺上。這些平臺為了要吸引更多閱聽人,演算法往往會偏好有害的內容,帶來的結果包括了自殺、激進行為、助長陰謀論等。如果這些社交平臺沒有大規模修改演算法,那麼演算法將會持續刺激生產有害的內容,類似的結果就會持續發生。
摘自天下文化《達爾文陷阱》P.42-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