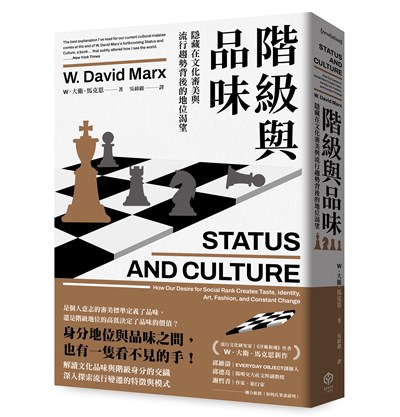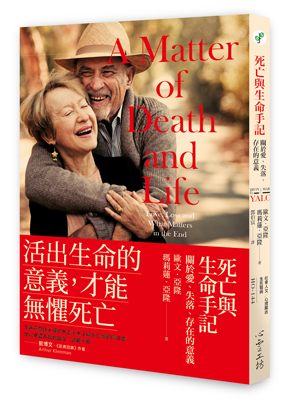
本書是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及哀傷輔導大師歐文‧亞隆與作家妻子瑪莉蓮合寫的作品,內容關於生命、死亡和對伴侶的依戀。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最佳的醫療照顧,家人及朋友的感情支持,以及沒有痛苦的善終。結褵六十五年的亞隆夫婦恩愛一生,在確定瑪莉蓮因病將不久人世時,兩人攜手將橫在眼前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所希望的是,這樣的經歷及觀察不僅有助於自己,更能化身為小小的光,為有同樣經歷的人們帶來輔慰和指引。
文章節錄
《死亡與生命手記:關於愛、失落、存在的意義》
哀傷治療的七個進階課題
一百天之後
知道我在尋找好小說的朋友,最近給了我許多有趣的建議,但為了使讀自己作品的療效得以持續,我便挑了《媽媽和生命的意義》(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出來,這是一本故事書,二十年前寫就,迄今未再讀過。掃過目錄,看到第四個故事的題目〈哀傷治療的七個進階課題〉,我大吃一驚,簡直就是震撼。啊,八十八歲的悲哀!這個故事與我現在的哀傷如此關係密切,我怎麼居然給忘了。何況那還是書裡篇幅最長的故事。我立刻開始閱讀。才讀幾行就勾起了回憶,整個故事湧進腦海裡。
故事開始,是我和一位好友也是系上同事的對話,他請我治療艾琳。艾琳也是朋友,史丹佛外科醫師,由於丈夫腦部有惡性腫瘤,無法動手術。幫朋友的忙,我義不容辭,但把朋友當成病人卻有些棘手:我會掉進每個有經驗的治療師都避之惟恐不及的麻煩裡。雖然聽到警鈴在響,卻又有心幫助朋友,我便把警鈴音量轉低。此外,這樣的要求也不是不合理:那段時間我正深入做一項研究,探討八十名喪偶者團體治療的效果,朋友和我自己都相信,治療師當中,瞭解喪偶如我者恐怕沒有幾個。另外還有一點更具說服力:艾琳告訴我朋友,以我的靈光,治療她不作第二人想──一擊中的,正中我虛榮心的要害。
第一次諮商,艾琳就一躍而入深水,講了她前一晚上作的一個夢,一個令人震驚的夢:「我準備上課的教材有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本:一是古代的,一是現代的,題目相同。要上的課我還沒準備,因為兩個文本我都還沒看,尤其是古代的那個,那是為第二個文本準備的。」
「記得文本的名稱嗎?」我問。
「當然。」她立刻回道:「記得很清楚:兩個都叫枉死。」
這夢讓我想到「智力的珍饈」,諸神所賜的一份禮物──一個有腦筋的偵探白日夢成真。我直截了當問道:「妳說第一個文本是為第二個準備的。這些文本都講些什麼,妳都心裡有數囉?」
「豈止心裡有數!我完全知道它們在講什麼。」
我等她繼續講下去,她卻一聲不吭。我又哄又勸:「文本講的是……?」
「我弟弟死於二十歲是古代文本,我先生將不久人世是現代版本。」
後來我們多次談到這個「枉死」的夢,也談過她決心不讓別人跟她親近以免傷到自己。年輕的時候,為這個原因她就決心斷絕親密關係。不管怎麼說,她到底還是把自己委身給一個四年級就認識了的男人,嫁給他,而如今,他卻要死了,這未免也太快了。第一次會面時,從她的生硬、冷淡及說話有所保留,我就清楚意識到,她有意與我保持距離。
她的丈夫去世後,也是第一次諮商幾個星期之後,艾琳講了另外一個夢,力道十足──我聽過最生動最怪異而又恐怖的夢:「我在您的辦公室,坐在這張椅子上,但屋子中間有一面牆。我看不到您……我檢視著這道牆,看到一小塊紅方格子布,然後,認出一隻手,接下來是腳和膝蓋。突然間,我明白了,那是一堵由屍體堆疊起來的牆,一具疊一具。」
「紅格子布,我們中間有一道由屍體堆疊起來的牆,部分軀幹──艾琳,妳怎麼解釋?」我問。
「沒什麼難解的……我先生死時穿紅格子睡衣……至於您看不到我,那是因為死人的屍體,所有死去的。這您是想像不到的。壞事情您從沒碰到過。」
後來幾次會面,她又說,我的人生不真實:「溫暖,舒適,家人隨時圍繞著您。什麼叫失去,您真的知道嗎?您以為您可以處理得比較好嗎?假設您的妻子或一個孩子現在死去,您要怎麼辦?甚至您這件粉紅條紋襯衫──我都覺得刺眼。我不喜歡它傳達的訊息。」
「它傳達什麼訊息?」
「它在說,我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告訴我,您有嗎?」
艾琳講起那些她所認識的失去配偶的人。「他們全都知道,妳是走不出來的……地底下一片死寂,只有他們知道……所有那些活著的人……那些失去親人的人……您要我不要再依戀我先生……要我回頭面對生活……那根本就是錯誤……一種像您這種從未失去過任何人的人才有的錯誤──沾沾自喜……」
如此這般,她一連講了好幾個星期,終於把我給惹毛了,我完全失去了耐性。「那妳是說,只有失親的人才能幫助失親的人嗎?」
「曾經經歷過的人吧。」艾琳平靜回答。
「打我進這一行以來,今天總算開了眼界了!」我吼回去。「那麼,只有毒癮才治得了毒癮了,對嗎?難道妳必須先飲食失調才治得了厭食症?或是憂鬱症才治得了憂鬱?……那麼,思覺失調治得了思覺失調嗎?」
後來,我把我的研究發現告訴她:每個失去配偶的人都會漸漸地走出來,不再依戀死去的先生或妻子,婚姻最美滿的夫妻比較容易完成這個過程,倒是那些婚姻比較不美滿的人,反而會為他們糟蹋掉了的歲月而悲傷。
聽了我的這番話,艾琳無動於衷,平靜回答道:「你們做研究的人想要的答案,我們失去親人的人已經都懂得了。」
事情就這樣又繼續了幾個月。我們角力,我們爭執,但我們鍥而不捨。艾琳漸漸改善,在我們治療第三年的初期,她認識了一位男士,愛苗漸生,終於結為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