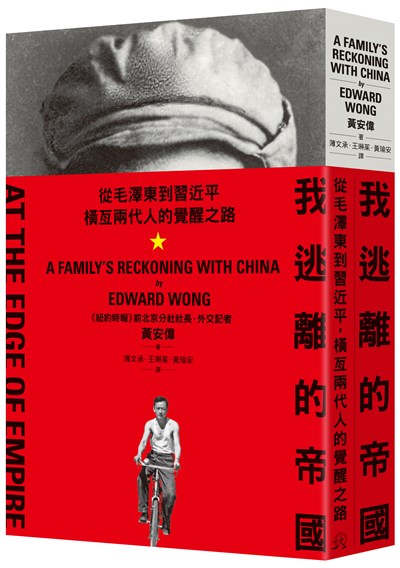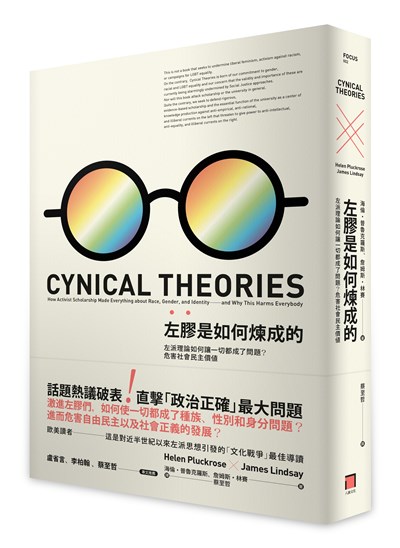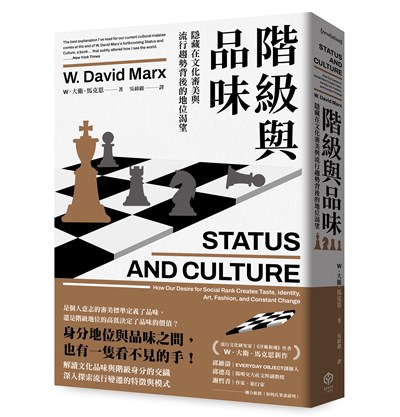《學做工》是英國文化研究大師保羅•威利斯深刻描繪與解析當代勞工階級生活處境的經典之作,於四十五年前出版時,引發了跨領域的巨大迴響。作者採用人類學民族誌調查方法,近身參與觀察勞工階級子弟在校園與社區裡的實際互動,據此得出深具啟發的反思貢獻。
本書試圖理清階級流動或再製的矛盾套路,並提出尖銳而根本的質疑:勞工階級的後代是「自願」選擇接繼父業,還是被迫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無限迴路似地「學習」階級複製的文化?環視今日階級衝突不減反增的社會結構,四十年前擲地有聲的探問,此刻依然體現年輕世代追尋平等自由的急切呼喚。
內容節錄
《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解析階級流動困境經典之作、教育社會學必讀民族誌)》
〈序言〉節錄
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處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
單說他們別無選擇,未免太過簡單。在不同社會體制下,使人們進行體力勞動的方法有很多:從以機槍、子彈和卡車威脅,到灌輸集體意識、使他們自願加入產業工人大軍。我們所在的自由民主社會可能正處於這兩者之間──沒有明顯的武力威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導向的結果。然而,體力勞動報酬低下,社會地位不高,且其本身也日益單調無聊;簡單來說,體力勞動者處於我們階級社會的底層。這本書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闡明這一令人驚訝的過程。
人們通常認為,工作能力和學習才能在不同人群中是逐步遞減的,而工人階級處於底層,從事著糟糕的工作,以至於他們認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下半輩子就應該待在汽車廠裡把螺帽一個個旋上輪子,這公平合理。」當然,這種逐步遞減的模型須假設其底層的刻度為零或接近於零。然而生活在底層的真實個體很少會給生活打分數,更別說給人生評分。既然這些個體遠非行屍走肉,而且使整個系統陷入危機,那麼我們顯然有必要重新審視這個模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工作的市場經濟斷然不會延伸到滿意度的市場經濟中去。
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失敗的」工人階級子弟並不是隨便撿個中產階級與成功的工人階級子弟不肯做的糟糕工作就去做的。我們不應當假設在職業、階級結構裡面有一條連續下滑的能力曲線,相反地,我們應該要看到在不同文化形式銜接裡顯現出的徹底斷裂。我們應該觀察工人階級「失敗」的文化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有何不同,以及兩者是如何中斷的。儘管處於既定的環境中,它與其他傳統意義上被視為更成功的群體相比,有自己的過程、自己的定義和自己的看法。這種階級文化不是中立的典範(paradigm),不是心理範疇,也不是一套外界灌輸給學校的變數。它包含了各種經歷、關係,以及關係的系統類型總和,這些不僅設定了孩子們在特定時間的「選擇」和「決定」,而且在實際和經驗的範疇內,設定了這些「選擇」一開始是如何出現和被定義的。
本書另一相關、次要的目的,是通過具體研究工人階級文化中最有啟迪意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來探討工人階級文化的重要及核心方面。事實上,我最初的研究興趣是整個工人階級文化,但我逐漸被導引到那些心懷不滿、不求進取的男青年身上,他們適應工作的過程正是工人階級文化形式不斷更新的關鍵時刻,而這些文化形式關係到勞動關係這個最基本的社會結構。
事實上,上述兩組關注的話題均指向了勞動力這個重要概念,以及在我們的社會中它是如何被準備、以應用到體力勞動中的。勞動力是人類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生產物品以滿足需求和繁衍的能力。勞動不是一項普世、永恆、不變的人類活動。它在不同的社會具有特殊的形式和意義。勞動力被主觀理解、客觀應用的過程,以及過程間的相互關係,對於所生成的社會類型和該社會各階級的身分及構成具有深遠的意義。這些過程不僅在經濟和結構的層面,而且在文化和象徵層面,都有助於建構特定主體的身分和鮮明的階級形式。
只有當階級身分在個體和群體中被傳遞、在個人和集體自主意識的情境中得以再現時,階級身分才真正被再生產。當賦予人們之物被重塑、強化並應用於新目標時,人們才真正活出了、而不是借用他們的階級命運。勞動力是這一切的重要樞紐,因為它是人們主動聯繫這個世界的方式──用外部現實表達自我的最佳方式。這事實上就是透過現實世界的自我實現與自我的辯證。一旦達成這種與未來的基本契約,其他一切就能作為常識被接受。
我認為,對體力勞動力的某種主觀意識,以及將體力勞動力應用到體力工作中的客觀決定,是在工人階級反學校文化的特定背景中產生的。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的主題在確定的環境裡被調和到個人和群體中;也是在這種背景下,工人階級子弟在自己的實踐中,創造性地發展、改變,並最終再生產了大文化環境的某些方面,以至於他們最終被導向某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