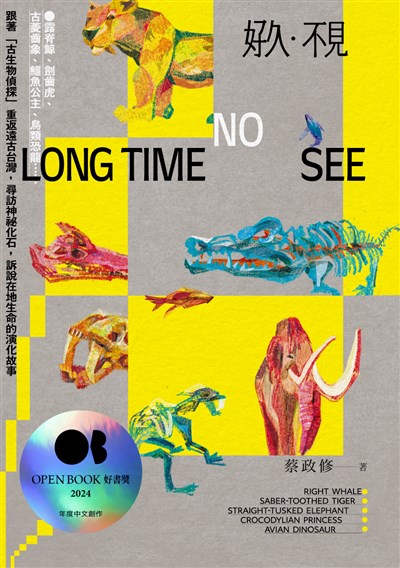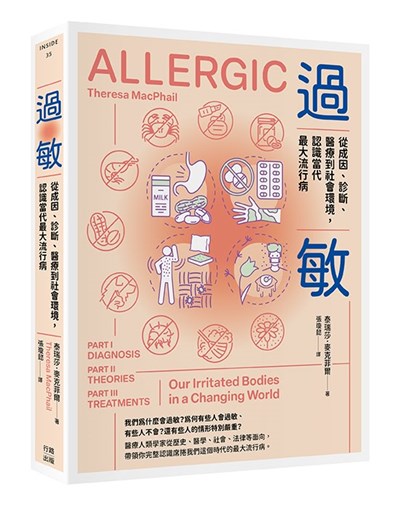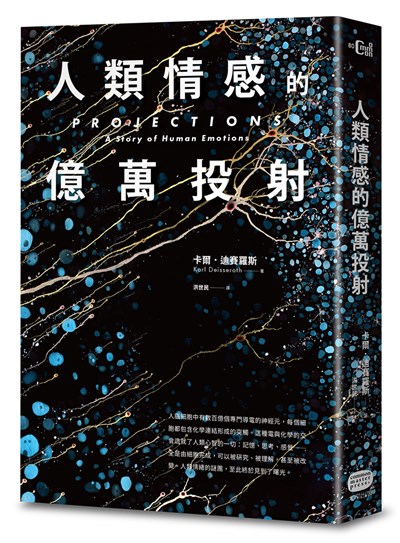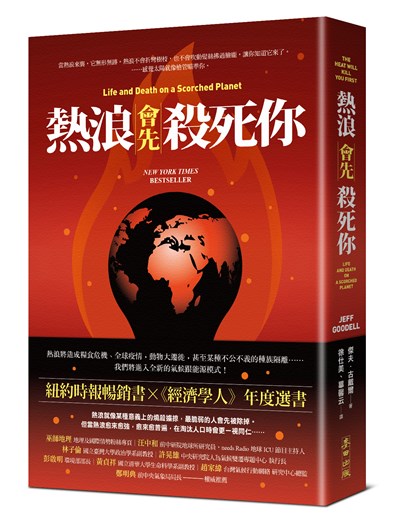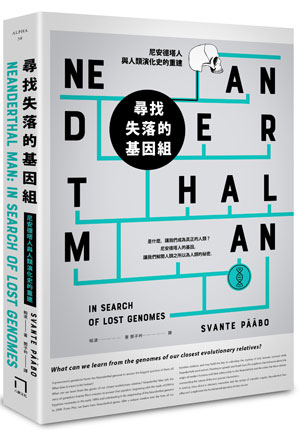
由於演化人類學及古生物學家對於現代人類起源以及與尼安德塔人的關係,一向頗多爭議,在本書中,帕波描述自己在二十五年漫長的研究中所進行的工作,並敘述為了找出人類和近親尼安德塔人之間遺傳差異,帕波的研究透過基因組的分析,打破許多人對遺傳學真能對人類學有所貢獻的疑慮,解開人類演化之謎。
文章節錄
《尋找失落的基因組:尼安德塔人與人類演化史的重建》
第二章 木乃伊與分子
我的研究生涯不是從尼安德塔人開始的,而是埃及古代的木乃伊。我十三歲的時候,母親帶我去埃及,自此我就著迷於埃及的古老歷史。不過我是在祖國瑞典的烏普沙拉大學(University of Uppsala)唸書的時候,才開始認真做研究。這時我逐漸瞭解我對於法老王、金字塔和木乃伊的狂熱,是我青少年時期的浪漫夢想。我自己做了功課,背下象形文字的意義和歷史內容,我甚至連著兩個夏天在斯德哥爾摩的地中海博物館(Mediterranean Museum)整理陶器碎片和其他古文物的目錄。那裡有可能成為我將來工作的地點,我又或許能成為瑞典的古埃及學家。不過我後來發現,同樣的人在第二個夏天所做的事情和第一個夏天非常相似,而且他們在同樣的時間到同樣的餐廳、吃同樣內容的午餐,討論同樣的古埃及之謎和學術八卦。基本上,我開始瞭解到,對我而言,埃及古物學這個領域進展得非常慢,這不是我所想像的專業生涯。我希望能有更多令人興奮的事情,和周遭的世界的聯繫更緊密。
覺醒之後,我一度陷入危機。我的父親曾經是醫師,後來變成生物化學家。面對危機,我以他為前例,決定讀醫學,然後從事基礎研究。我進入了烏普沙拉大學的醫學院就讀,過了一些年後才驚覺,我還滿喜歡看診的。這是少數能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又能在他們的生活中扮演正面角色的職業。和人們互動的能力是意料之外的才能。經過四年的醫學研究生活,我又面臨了另一個小小的危機:我應該成為醫生,還是一本初衷從事基礎研究呢?我選擇後者,當時我想我能夠(應該是我想)在讀完博士班之後再回到醫院。我加入了當時烏普沙拉大學最熱門的科學家之一彼得森(Per Pettersson)的實驗室。才在沒多久之前,他的實驗室首先找到了某一個移植抗體(transplantation antigen)的遺傳序列。這種抗體是一種蛋白質,位於細胞的表面,負責調控免疫細胞對於病毒和細菌蛋白質的辨識。彼得森不但作出了讓人興奮的生物學發現,也與臨床醫學有關係,而且他的實驗室還是烏普沙拉大學中少數擅長利用細菌來選殖和操縱DNA的實驗室之一,這個技術在當時是很新穎的。
彼得森要我加入實驗室的團隊,研究腺病毒(adenovirus)上的一個蛋白質。這種病毒會引起腹瀉、感冒般的症狀,以及其他讓人不舒服的症狀。當時我們認為,這種病毒蛋白質進入細胞中會和移植抗體結合,這樣一來,當這個蛋白質傳送到細胞表面後,免疫系統中的細胞就會認出它來,接著免疫細胞就會活化,殺死身體中其他受到這種病毒感染的細胞。接下來的三年,我和其他人研究這種蛋白質,才發現我們對這種蛋白質的看法完全錯誤,它非但不是免疫系統攻擊的倒楣目標,反而能夠在細胞中找到移植抗體並與之結合,讓移植抗體無法輸送到細胞表面,這樣受感染的細胞表面就沒有移植抗體,免疫系統就無法認出它而受到感染了。換句話說,這種蛋白質遮掩了腺病毒。事實上,這種狀況使得細胞中的腺病毒能夠存活得非常久,可能有受感染者的一輩子那麼長。病毒能夠以這種方式阻止宿主免疫系統的作用,是一種啟示。我們工作的結果成為許多篇在一流期刊上備受矚目的論文。後來發現,事實上其他種類的病毒也利用類似的機制躲避免疫系統的攻擊。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研究尖端科學,令人著迷,這也是我第一次(但非最後一次)瞭解到,科學的進步往往得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瞭解到自己和同儕的想法是錯誤的,而且之後還要花更長的時間,努力說服自己最密切的合作伙伴以及世界上大部分的人,接受新的想法。
不過,雖然我身處於生物學的興奮發現之中,但卻無法完全擺脫對於古埃及的浪漫迷戀。只要時間允許,我會去聽埃及古物學研究所的演講,也持續古埃及語(Coptic)的課程,學習西元時代法老王治下埃及人所說的語言。我和天性快活的芬蘭埃及古文物學家何特爾(Rostislav Holthoer)交上了朋友,他具有奇特的能力,能夠和三教九流的人建立友誼。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和一九八○年代初期,我和他在他烏普沙拉的家中吃晚餐,聊天到深夜,經常向他抱怨自己熱愛埃及古文物學,但是這個領域的未來有限。我也喜歡分子生物學,而這門學問似乎可以永無止盡地增進人類的福利。我得在這兩條有著同樣吸引力的生涯規畫中做出決定,這是讓人煎熬的難題,一個年輕人在兩項極佳的選項中苦惱的時候,旁觀的人可能不會有多少同情心。
不過何特爾對我很有耐心,他聽我解釋說,科學家現在能夠從任何的生物(可以是真菌、病毒、植物、動物或人類)取出DNA,然後插入質體(從細菌的病毒DNA製成,能夠攜帶其他DNA),把質體再放入細菌中。細菌繁殖,質體也跟著增加,使得外來的DNA能夠複製出千百份。我也解釋了,我們可以定出這外來DNA的四種核苷酸序列,找出兩個人或兩個物種之間DNA序列的差異。兩個序列越相似(兩者之間相異的核苷酸少),兩者的親緣關係就越相近。事實上,從共有的突變,我們可以推測這段特殊的序列在百千萬年來,是如何從共同祖先DNA序列演化而來的,而且還可以大約判斷這段共同祖先DNA序列存在的年代。例如在一九八一年,英國的分子生物學家傑弗里斯(Alec Jeffreys)分析了人類和猿類血液中血紅素蛋白質的基因,推論出這個基因在人類和猿類中各自分開演化的時間點。我解釋道,這個方法很快就會應用到許多基因上,任何物種的個體都能取出基因來研究,然後科學家就能知道過去有多少物種是彼此相關的,以及他們在歷史中何時開始各自獨立的。這個方法,比以研究形態和化石的結果要精確多了。
在我解釋給何特爾聽的當下,心中慢慢浮現一個問題:這種方法只能應用在從現存的人類和動物上取得的血液或組織樣本嗎?能應用到那些埃及木乃伊嗎?那些木乃伊中有DNA殘留著嗎?這些DNA一樣能夠插入質體,然後在細菌中複製嗎?有可能經由研究這些古代的DNA序列,釐清古代埃及人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以及和現代人類的血緣關係嗎?如果辦得到,就能夠回答以傳統方式從事古埃及文物學研究的人無法回答的問題。例如現代的埃及人和五千至兩千年前法老王治下的埃及人,彼此之間的血緣關係有多密切?公元前四世紀亞歷山大大帝攻下埃及,公元七世紀又受阿拉伯人入侵,這樣巨大的政治與文化變化,使得原來的埃及人大部分都被取代了嗎?或是這些軍事與政治事件只是讓當地人接納了新的語言、宗教以及生活方式呢?重點就是,現在住在埃及的人是和那些蓋金字塔的人一樣嗎?或是他們的祖先已經和許多入侵者混血,現在已經完全和古代埃及人不同了?這些問題令人屏息,其他人應該也想到了。
我到大學的圖書館查閱相關的期刊和書籍,但是沒有發現從古物中取得DNA的報告。似乎沒有人曾經取得古代的DNA。就算是有也沒成功,如果成功了當然就會發表結果。我和彼得森實驗室中比較有經驗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談及此事。他們說,由於DNA非常脆弱,你怎能預期能夠續存數千年呢?交談的結果令人沮喪,但我沒放棄希望。我衝去查閱文獻時,發現一些文章的作者宣稱,他們從藏在博物館中數百年的動物身上發現了蛋白質,抗體能夠偵測到這些蛋白質。我也發現有些研究宣稱,用顯微鏡觀察到了古代埃及木乃伊的細胞輪廓。因此,有些東西的確能夠留存一些時間。我決定開始進行幾個實驗。
第一個問題應該是在人死後,組織中的DNA是否能夠保留一段長時間。我推測,如果組織脫水了,DNA就能夠保存比較長的時間,因為分解DNA的酵素需要水分。古代埃及為屍體防腐的人處理木乃伊時,就會進行脫水。這是第一個要測試的事情。所以在一九八一年夏天,當實驗室的人不太多時,我到超級市場買了一塊小牛肝,然後把從市場上取得的收據貼在新實驗筆記本上的第一頁,這本是要來記錄這些實驗的,不過我想盡量保密,因此本子封面除了我的名字之外,別無記號。免疫系統分子層面運作的研究,競爭非常激烈,這是我應該做的事情。如果彼得森知道了我分心去做了這些事,他可能會禁止。而且不論如何,我都希望事情能夠保密,這樣一旦失敗了,才不會被實驗室的同事奚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