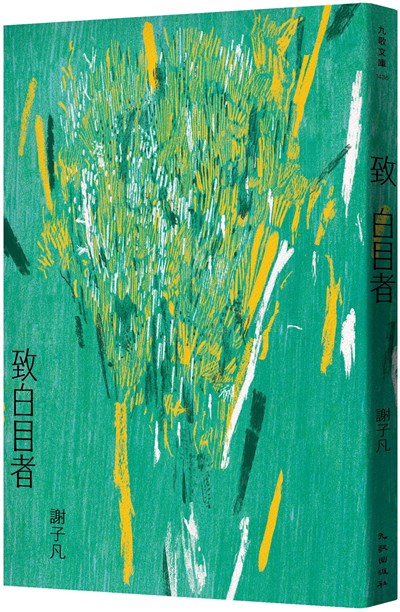──美食沒有消失,只是變成記憶的形狀──
從小說家張國立的童年記憶出發,以味蕾穿過回憶、跨越國境;在作者筆下,食物不單單滿足口腹之慾,更是承載著對母親的追憶、人生的感悟。
與擅長料理又熱愛旅行的妻子結婚後,更加開拓小說家對美食的探索,「紅燒肉」、「南瓜餺飥」、「馬鈴薯燉肉」、「蘋果煎餅」……透過旅行,將異國佳餚延伸進自家廚房,經由妻子的巧手,成為張家的經典食單。
嚐遍美味的張國立說:最好的一定藏在記憶裡,而非在遙遠的未來。
文章節錄
《大碗另加:小說家的飲食滋味》
〈紅燒肉與赤豆鬆糕的回億〉
小時候最期待星期日,這天老媽不用上班,一早上菜場,我對她返家時的菜籃充滿好奇與期待,等翻到籃底找出一大塊五花肉,便是滿足的結束。
「高興了?不鬧了?」老媽說。
一上午小廚房內傳出爆蔥、煮肉,乃至於甜甜的醬油味,不待老媽呼喚,我已乖巧懂事手持筷子坐在飯桌旁,看著陶鍋從她手裡移至桌面,看著她以抹布掀開冒蒸氣的鍋蓋,看著煙霧散去後的圓滿人生。
是的,紅燒肉代表成長過程裡某段重要記憶。它的存在一如父母流在我體內的血液,一如櫻花與春天的關係。
紅燒肉無非濃油赤醬,紹興酒絕不能少,最後以冰糖增添光彩。有時加進燉得入味的雞蛋,有時加進墨魚一起燒,若是墨魚,就海陸雙鮮啦。
母親早逝,之後尋找紅燒肉成為我旅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得找到又香又嫩又帶些許甜味的紅燒肉—我想,我的靈魂可能在醬油的黑乎乎鍋底,才能得到平靜。
第一次吃到老媽味道是在浙江南潯,二十多年前了吧,國營酒店的餐廳,光氣味我即知道,這就對了。那晚吃的是鹹魚燒肉,整鍋老媽的味道。
朋友知道我非紅燒肉不罷休,上海的老出版人邵敏請我進老克勒餐廳,他整晚只說兩句話:「國立,諾,你就是個老克勒,帶你吃老克勒的菜。」
克勒指的是英語中的衣領,「collar」大意是有點文化與貴氣的上流階級。邵老師客氣,其實我不是老克勒,是老嗑啦,愛吃而已。
第二句,他照樣以「國立,諾」開頭:「你要的紅燒肉。」
上海人關於料理的動詞是「燒」,不講煮飯,講燒飯,光是「燒」,我聯想到當年中山北路二段台北新村內每戶人家傍晚時擺在門口的煤球爐,我家由我負責搧火,火得大、火得旺。燒呀,不燒哪來得晚飯。
問北京人哪家麵館的炸醬麵好吃,百分之九十的老北京人會說:「我姥姥的。」「我嬸嬸的。」「我爸的。」問上海人哪家餐廳的紅燒肉好吃,老吳直截了當:「哎呀,什麼館子,紅燒肉我燒的最好吃。」
於是我坐進老吳家的飯廳,見到一大鍋紅燒肉朝我面前一擺:「吃,吃不完打包。」
尋找老媽手藝的旅程當中,得到熱量,也得到感情,新的經歷累積在舊的回憶上,一整鍋朋友的熱情。紅燒肉狂的名號傳出去,朋友根本不必費事為我安排餐廳,老盧聽說我要到上海,這麼說:「紅燒肉又來了。」
上海周邊許多小鎮,多年前遊到某個尚不出名的古鎮,一戶人家將爐子放在門口,鍋裡燒著紅燒肉,香得我幾乎想向那家人討塊肉、討碗飯。
強調一下,紅燒肉和東坡肉雖師出同門,但究竟味道不同,前者家常,後者不免透著些要人掏鈔票的貴氣。
紅燒肉外還有一道我尋尋覓覓、永遠在旅途中追索的菜—赤豆鬆糕。
民國五○年代的台灣用一個字形容:「窮」?不太對,那時的人雖沒錢進館子,吃的方面並不委屈。應該用這個字形容:「想」。想吃到更好的、想過更好的日子、想到美國去念書。
想吃便當(那時很難買到麵包,也沒有便利超商)、想有五毛錢(買皮球糖或尪仔仙)、想考進大學(文組的錄取率一度僅有百分之二十七)、想有台電視機(寧可不要冰箱)。
班上有位同學過生日,他家裡經濟環境允許超前布署,爸媽買了個蛋糕送到學校,意思是與同學分享。不是現在的鮮奶油蛋糕,是外殼堅硬得若用湯匙敲敲會崩潰的老式海綿蛋糕。我吃到一小塊,覺得簡直人間美味。如今回想,不就是糖分高點、外觀美點。
回家後我意志堅定對母親說,我生日的時候也要蛋糕。
我當然不知道那時台北的西點店以個位數計算,南京西路與中山北路口的「美而廉」,美雖美矣卻未必廉;「莎莉文」的洋貨多,甚至有起司,我媽恐怕不太願意進去花新台幣。
不過我生日那天她的確做了個大蛋糕,幾個好同學也來分享。白白嫩嫩的蛋糕甚至冒著蒸氣。母親費了好幾天準備了餡再準備糯米,以蒸籠蒸出好大個鬆糕。圓的,像蛋糕。鬆軟,像蛋糕。裡面是紅豆沙的餡,甜甜的,像蛋糕,但它絕對不是我期望的蛋糕,於是我指著剛出籠的赤豆鬆糕喊:「那不是蛋糕。」
幸好我同學捧場,個個吃得抹嘴、吸口水。其中一人說:「張媽媽,好好吃喔。」的確好吃,糯米香氣遠勝過麵粉。
我一生最棒的生日蛋糕是那個,不知誰說過,最好的一定藏在記憶裡,而非吊人胃口說什麼在遙遠的未來。
—打個岔,我相信過去,不相信未來—
我媽是廚房內的魔術師,什麼都變得出來,糯米生日蛋糕確定了她的永恆,不論哪種未來也無法超越母親留下的舌尖上的記憶。
讀大同中學夜間部時,我養成睡到中午的習慣,這個年紀的男生尤其懶。當我十二點以後醒來,打開電鍋看母親留下午餐,當然得先按下鍵,蒸熱了再吃,可是實在餓得慌也懶得可以,冷的照吃。
這事被她發現,於是在大同電鍋加了水,並且拎著我耳朵到電鍋前說:「諾,就是這個開關,往下一按,半個小時內就有得吃。」
接著她再發現,我照樣連按也懶得按。沒關係,她有的是辦法,她指著電鍋裡的食物說:「下面那碗是飯,上面是鯧魚,蔥、薑都加好,你得按了鍵,魚才蒸得熟,否則就吃生魚。」
那時鯧魚便宜,她知道我愛吃魚,買小的,恰好能放進電鍋。那次開始我終於懂怎麼用電鍋,也吃到熱的中飯。
我媽在我二十八歲那年離世,從此我尋找紅燒肉至今,且明確的知道,最好的一定在記憶裡,而非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