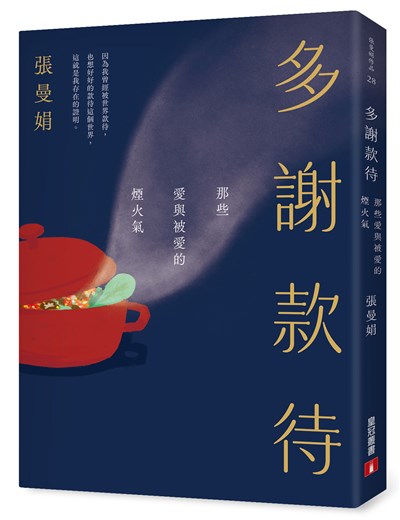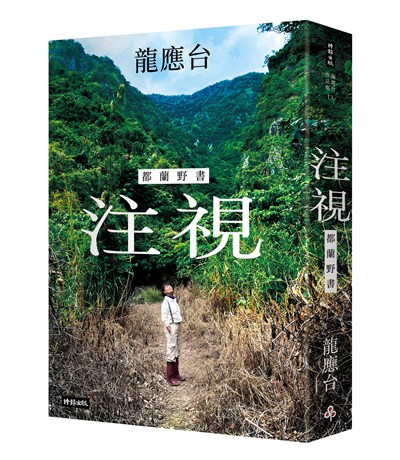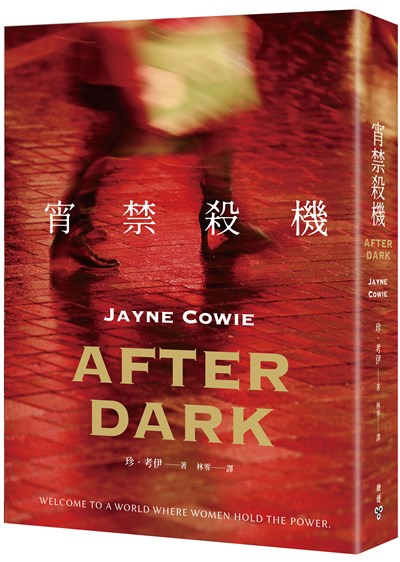這是一本呈現荒謬劇場風格的黑色小說,讀者注意力通常會關注在書中故事情節的爆笑和尖銳的嘲諷性上,但是,作者想描述的是許多對待生命持有不同角度看法的人如何感受自己活著的意義。
作者是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畢業的才女作家成英姝,經常發表小說、散文、書評等,一向以黑色幽默文筆著稱,曾獲媒體舉辦的小說獎首獎、獲選行政院文建會公元2000年十大文學人,她後來的小說逐漸不使用嘲諷的幽默手法,但仍表達生命在痛苦中燦爛絕美,《人間異色》則再回到過去搞怪、諷刺、尖銳的尖酸刻薄,不同的是賦予人物可愛的本質。
故事可說相當KUSO,各懷不同目的來到深山一座神秘旅館的8個人,包括有戀母情結的大學教授、清純與刁鑽的2男1女大學生、2個喜歡記錄台灣風情的紀錄片拍攝者、失魂落魄的作家、自認很有風情的酒家女,卻發現兩個陌生人的屍體,看似都會男女殉情的案件,8個人卻有不同的離奇推理。
書中人物超現實又寫實,例如,大學教授高高在上,仍有不為人知的一面;女大學生看來清純,卻曾翹課太凶以致成績被當,又為了成績而不擇手段;作家思考貼近哲學式,有理想,但不被肯定,所寫的書賣的不好;與作家一起到深山的酒女,年紀已大,外表保養的很好,還引誘大學生,沒什麼道德感;8個人對命案的推理,與各自個性若合符節,也某種程度貼近社會現況,讀者好似看電影或荒謬劇場,也不妨輕鬆的思考什麼樣的人生是自己想要的。
文章節錄
女人的目光落在男人握著方向盤的手,那手掌看起來似乎很大。據說手掌大的男人心臟也大,而心臟大的男人那話兒也大。要是真這樣就好啦!
若被知道心中忖的是這種事,恐怕會被認定為淫蕩的女人……什麼恐怕,九成六是這樣!為何世人總認為討厭的女人必定淫蕩呢?也許你以為世人的邏輯乃淫蕩的女人必然無恥下賤,其實是反過來,世人若把一個女人看作低劣,管她是厚臉皮也好,愚笨也好,低俗也好,或是潑辣,或是惡毒,或吵鬧或陰沉或傲慢,隨便什麼,只要不順眼,就是慾求不滿、寡廉鮮恥的女人,換言之,必然是淫娃蕩婦。
只是這麼一來,一個性慾缺乏的石女若是被人討厭,不就也淫蕩起來了嗎?哈哈哈!這邏輯多麼不堪一擊!但是這麼簡單的道理也說服不了頑固的世人的,凡是女人,隨時都會墮落,隨時都會變得淫蕩的嘛!
反觀男人,明明是性無能的可悲傢伙,如果被看不順眼的對手宣稱為風流色鬼、毫不節制地到處亂搞、搞得昏天黑地,說不定還正中下懷地竊喜。真有此事也就算了,但因為是性無能,當然就是空穴來風,無異是給加上了頂天上掉下的皇冠啊!只可惜,男人彼此知道這種心理,豈會放這般讓你稱心如意的謠言。
其實女人耿耿於懷坐在她身旁的男人那玩意兒是否可觀,全然是務實的想法,要說春心蕩漾真是言過其實,既不覺得身上哪裡有毛蟲在爬,也不覺得心跳加快、脖子發熱,那裡可是冷靜又乾燥,就像秋天的石頭吧!
話說只要往顛簸的交通工具一坐,她馬上就會睡著,近午明明睡飽了起床,至今還沒一個鐘頭,她就打起呵欠了。
老闆娘發現自己沒上班,也沒請假,一定會氣壞了吧?想到此她心中哈哈大笑。只不過是沒請假,就在心中勝利地哈哈大笑,實在可悲,怪不得在這心中的笑聲背後,暗藏了某種焦煩。
說到老闆娘,一天到晚強調自己才二十七歲呦,還是大學畢業,討不討厭啊!那黃毛丫頭把店頂下來後,每天上班都令她不舒服,可不是奇檬子的不舒服而已,是頭也痛,肚子也痛,腳也莫名其妙地痛起來。以前呢,若是工作的環境裡有女大學生,都會被她這樣的女人們給聯合起來氣跑的,但是這個老闆娘來了以後,其他原來的小姐都離開了,就只有她留下,老闆娘帶來的幾個女服務生,都是女大學生。
世人幹啥有女大學生就高等的迷思呢?以前她也是困在這迷思中的,只不過越想越搞不懂,越想就越困惑;諸位啊,您一定沒動腦筋想過這問題,您只要稍稍想想,那專門耍玩低級下流言詞的週刊裡,好好的文雅話不講,偏偏故意要挑最粗鄙不堪連咱才中學畢業的人都不用的言詞的,那些記者啊編輯啊,可不都是女大學畢業生咧?這麼一想還不嚇死人嗎!咱若公然寫這種文章,爹娘都會哭,但咱的學歷背景,還不給咱吃這行高級的飯哩!
老客人沒有跑,還多了新客人,都說是因為老闆娘漂亮的緣故(哼,那個女人哪算漂亮啊?)。老闆娘是個大鼻子大眼睛的洋人臉型,嗓音粗嗓門又大,這種嗓門似乎該搭配豪爽的個性,老闆娘也的確擺出一種豪爽作風,但實際一點都不豪爽,不但心眼小,老是疑神疑鬼,還喜歡裝作少女嬌柔的模樣。雖說跟三十九歲的自己比起來,二十七歲是很小,但也不至於叫作少女吧?未免太過份嘛!
老闆娘喜歡把兩隻手擺在頭頂上作兔耳狀,唉,難看,連她只是站在旁邊都感覺丟人。還有,老闆娘到客人身邊的時候,要小跑步,跑到定點原地跳兩下,再噘起屁股,客人都說老闆娘這樣「很有活力」,相較之下,她好像快踏進棺材的死人。
她本是生性囉唆的女人,她自己當然不稱之為囉唆,而是「健談」,但是跟老闆娘一比,她甘拜下風。老闆娘不只整天嘴巴停不了,說話的內容也讓人反感,總在那裡誇耀自己有學識、人面廣、有才幹,唉,真希望自己是聾子,聾子這時就有福了,啥都聽不見。
因為老闆娘這麼大嘴巴,害她從此變得沉默,當她想跟人說話時,不自覺變得會附到別人耳朵旁小聲低語,一副鬼鬼祟祟的樣子。
今天出發時心情特好,渾身上下感染了少女清新奔放的風情,見到那男人的一瞬間差點蹦過去跳兩下,手放在頭頂作可愛小兔耳,好在,好在還是壓下了這個衝動,保持了可貴的衿持。可惜坐上車以後,就開始有種不祥的洩氣感,瞄了一眼坐在旁邊的男人,心想之前為什麼會覺得和這男人出來旅行是件愉快的事?頓時心生煩悶。
回想男人第一次來店裡,是個老客人帶來的,介紹說是位作家,她聽了睜大了眼睛問:「你是吳若權?」其他人大笑,對那男人說些譏諷的話,她不知那笑是什麼意思,也聽不懂他們譏諷他什麼,她又問:「你是蔡詩萍?」其他人笑得更大聲。她聳聳肩,她就只知道這兩個男作家,也可以說,她大抵認為全國總共就只有兩個男作家。
「我就說嘛,長得不像。」她噘著嘴說。
雖然,他們都說他是「有名的作家」,可是她問店裡另外兩個女孩,她們也沒聽過他的名字,其中一個女孩還是正在讀碩士班、忙著寫她那個永遠寫不出來的論文的研究生哩!連這麼有學養智識的女青年都不認得的人,哪會是什麼高級的作家啊!
店裡連她在內有三個女服務生,雖然常陪客人喝酒,但老闆娘說這算不上陪酒,只是增加客人的「愉悅感」而已,酒吧裡的酒保不也常陪客人聊天?她們也不硬定小費的規矩,只是小費收得也沒少。女研究生用的名字叫葛妮絲,而且都用英文發音,她覺得那聲音聽起來不該翻譯作「葛妮絲」,應該是「龜黏絲」較貼切。另一個年紀較大,三十出頭,叫可俐。可俐是個小氣女人,包包裡總會帶一套新的內衣褲,平常穿在身上的是陳年不換的老舊內衣褲,要跟客人出場的時候才會換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