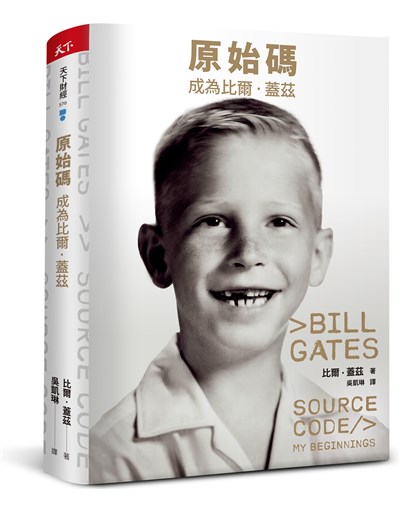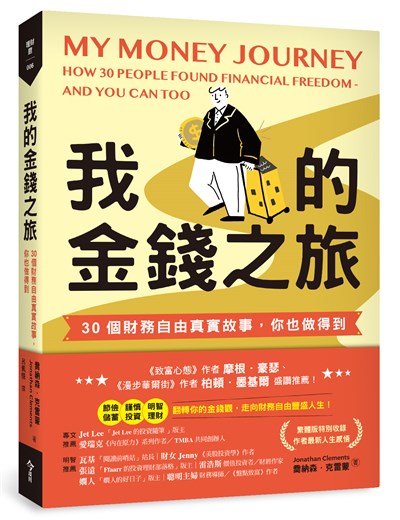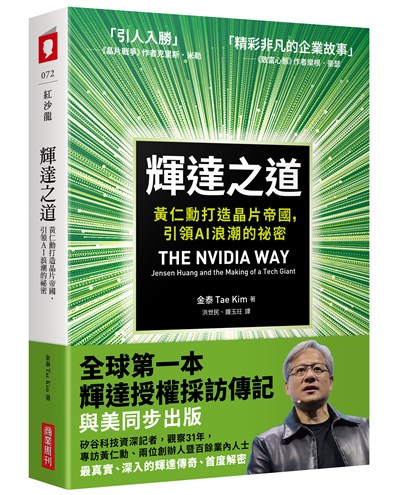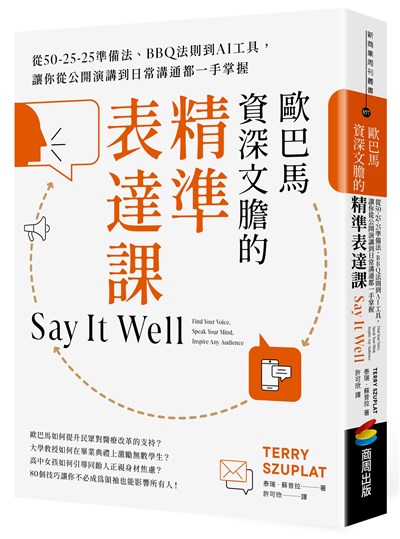銀行只要不做三件事,就能安穩保障所有人的錢。這「三不」是不做假帳,不借錢給沒有能力償還的人,限制專業經理人的薪酬在合理範圍內。看完這本書,我們才知道,華爾街從以前到現在,都不斷重複前述三項致命錯誤。還好有此書作者,不然,我們永遠看不到華爾街的陰暗面。
文章節錄
《華爾街的放逐者:要撈多少錢,他們才肯罷手?》
第三章
那一天,我投下股市震撼彈
不識相,終於付出了代價
一九九○年代末期,工作愈來愈上手,而我也開始有種責任愈來愈大的感覺。
這幾年來的每一份工作,都提升了我在華爾街的名氣,愈來愈多客戶向我諮詢銀行業的真實狀況。我的分析不錯,我也對自己的工作很有信心,但我每天實際看到的狀況,和我心中想像的華爾街應有的樣子,兩者之間的落差愈來愈大。如果我真想工作得有意義--繼續對銀行業提出客觀的看法--就得有所取捨。我在接下來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的工作時,就面臨了這樣的挑戰,也引發了我始料未及的結果。
在瑞士信貸,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這裡與客戶之間的娛樂活動,不但跟我之前的工作一樣頻繁,甚至還更奢華,或者我該說,到了近乎荒謬的程度。
別傻了,銀行會買單啦
我們公司會花錢租直升機,載著經理人和客戶去打高爾夫球;瑞士信貸的分析師可以預定公司裡的私人用餐室,裡面有紐約最棒的廚師為你服務。當研究助理們在底下幾層樓辛苦工作時,我們卻在安靜的房間裡跟客戶大啖美食,我可以邀請老婆和另外六個人(有時是比較像朋友而非客戶的投資人)一起來。飯後那些名廚還會出來,致贈他們的簽名食譜。我留了一份紐約餐飲業的巨星、米其林星級餐廳主廚大衛‧布雷(David Bouley)送我的菜單。在燙金的牛皮紙菜單上,列有鮪魚生魚片搭配淺綠萊姆醃製的維代利亞春洋蔥、查塔姆龍蝦、淋上罌粟雅馬邑醬的鵝肝,還有一道名叫「塔芬史楚索雲」的甜點,上面綴著野莓。你可能會問,酒呢?這還用說嗎!
然而,每次當我抹除嘴角的甜點屑時,內心又更矛盾了。因為我知道,這些好康的來源--又是來自投銀那邊的銀行家,主要是科技類股部門。我的工作跟科技類股沒有關係,但瑞士信貸在科技類股可是一大要角,當時那斯達克(NASDAQ)屢創新高,科技業者搶著掛牌上市。一九九八年,瑞士信貸找來十八位科技類股的分析師及他們的老闆法蘭克‧奎特隆(Frank Quattrone)。從他們一九九八年加入到二○○○年,公司總共辦了七十九件科技類股的首次公開發行(IPO),占瑞士信貸總IPO件數的四分之三,總值高達八十七億美元。IPO第一天交易的平均獲利是93%,為瑞士信貸帶進了數十億元的費用收入,也給了公司一種絕佳的工具(熱門IPO的股票),拿來回饋客戶。
我在瑞士信貸晉升為常務董事──相當於合夥人的資格;我之前所做的準確分析,也讓我在客戶圈中擁有一些影響力。當時我覺得自己和投資銀行部門有不錯的關係,其中一位是奧利弗‧薩科齊(Oliver Sarkozy),他老哥尼古拉‧薩科齊,後來當上了法國總統。
他們不會逼我一定要給正面的評級,我感覺他們是真的想要我比較客觀的看法。有一次我寫了第一聯合銀行(First Union,如今併入富國銀行)的報告,措辭相當嚴厲,但是他們的反應和我以前所待的公司不同,有兩位高階的投資銀行家直接拿著我的報告去第一聯合銀行,告訴他們需要如何改善問題。第一聯合銀行也認同我的分析及銀行家的建議,最後也和我們公司合作。這個系統本來就應該這樣運作才對,不靠浮誇吹捧,而是靠清楚透明的分析,大家公開陳述看法,由市場判斷誰對誰錯。
但是,相較於科技類股的團隊,我依舊只是小咖中的小咖。我和某些科技股分析師講話時,他們都把我當隱形人。有一次,我在一位網路股助理分析師的辦公室外頭等候,他居然對我吼:「你想要幹嘛?」另一位追蹤網路銀行的分析師則根本不回我電話,我聽說他只回奎特隆和《紐約時報》的電話。
我第一次參加瑞士信貸的常務董事會議(結果那也成了唯一的一次),受邀致詞的主講人是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他是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將領,後來當上美國國務卿。他來我們的會議上演講時,一些坐後排的常務董事竟然彼此嬉鬧,像朝會時的高中生一樣。看到公司同仁對一位從貧窮的南布朗克斯區(South Bronx)力爭上游,成為卓越領導者及政治家的人如此不敬,我實在覺得很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