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通往「全球」,無法抵達「本土」的飛機,該如何降落:評《面對蓋婭》
2017年中,法國學者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訪問台灣。他在幾場演說裡,既談到「人類世」以及當今眾多地球科學的研究,又提到前一年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議題。演講雖簡短,卻牽連甚廣,聽眾也許聽完仍覺有點莫名其妙,搞不懂其間究竟有何關聯。《面對蓋婭》一書在台灣出版,也許能提供大家一些回答。
「蓋婭」是希臘神話裡的大地女神,英國科學家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借用這名字,描述地球(嚴格來說是地球表層大約十多公里寬的薄膜)如何因為各種生命間的回饋作用,能夠長期保持在熱力學非平衡的狀態。他因此大膽宣稱:「地球是活的」。

面對環境議題,洛夫洛克的蓋婭理論引發了各種不同的詮釋,比方說新世紀運動便從中汲取不少靈感,此外,也有人把蓋婭解讀成巨大的控制系統,從而相信一旦人類可以把各種參數都搞清楚,「科學調節氣」(語出生祥樂隊〈藤纏樹〉一曲)便不再是夢。
但蓋婭不只是精神性的,更未必得是科學主義式的。研究人類世的科學家告訴我們,工業革命、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的全球大開發,已大幅改變蓋婭的構成,也讓她變得對人類的作為相當敏感。在拉圖眼中,蓋婭一點也不溫柔,甚至由於她怕癢、易怒,而且說實話,她不怎麼在乎人類的未來,因此任何想要操控她的企圖都有危險。
面對這樣的蓋婭,意味著什麼呢?這本書的副標題有點怪,叫作「新氣候體制」。其實拉圖用這組詞彙,是為了把當前的處境,比作1789年大革命前後法國舊體制面臨瓦解的時刻。
可以說,在拉圖眼裡,蓋婭其實有更強的政治意涵。這不是說應該把環境議題放到政治裡討論——這類呼籲已經太多了,而效果有多麼微小,也是眾所皆知。拉圖想說的反而是:蓋婭的闖入,已經徹底瓦解了西方現代人長久以來習慣的政治體制。當前,舊體制已經崩毀,但新體制仍有待發明。
因此所謂的面對蓋婭,重要的意義便是要著手發明適合的新政治。本文便試著從這個角度,提供讀者一條理解《面對蓋婭》的線索。我一開始將先說明,在什麼意義下,蓋婭瓦解了「現代」的政治體制。接著,我們將看到拉圖如何解讀《面對蓋婭》原著出版後,歐美國家所遭遇到的一些政治變局,如「極右派」、「疑歐派」的興起或者「黃背心運動」。最後我會簡單介紹,對於發明新氣候體制,拉圖有什麼具體的建議。
對「現代人」的人類學調查:事實與價值區分明確
在進入正文前,也許有必要先說明,這裡的政治指的是「誰」的政治。一直以來,拉圖的對話對象都是一個叫作「現代人」的新興民族,他們大約成形於17世紀的歐洲。這個民族由於歷史際會,發明了某種很有效的政治策略,於是很快便向世界各處擴張,同時也鼓舞或強迫其他被波及的民族一同加入現代化的行列。
三、四十年來,拉圖很大部分的研究即是在對「現代人」這個民族做人類學調查。他發現「現代人」有個與眾不同的特殊習慣,即:儘管實際上不容易辦到,但他們認為理論上應該要把「事實」(實然)和「價值」(應然)二者區分清楚。
比方說,碰到「吃素」這樣的議題,現代人便會認為應該要把這個問題分成兩部分,一方面是「吃素是否對個人(或社會、環境)有影響」,另一方面則是「應不應該吃素」。前者是科學家研究的事實問題,而在民主社會裡,後者則是需要公民討論、選擇的價值議題。
把科學及其研究的對象(包括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nature)以及人文科學研究的自然[human nature])放到價值領域、公共討論之外,是現代人很重要的發明。這個發明讓現代人在討論價值問題時,不必向「事物」詢問意見,畢竟政治只處理「眾人」的事務。同樣地,現代科學家在做研究時,也不必向他的研究對象詢問應不應該做這項研究。科學家研究的對象儘管複雜,卻很安靜。
區分「事實」與「價值」,既是現代科學的主要特徵,也是一項政治發明。如同拉圖在書中所提,現代人的科學和現代民族國家,根本是相輔相成的同一套政治發明。因為,如果說政治是一種商量生存空間(條件)的活動,現代人的科學便是一種有效的工具,讓民族國家得以擴展其生存空間。
每個人都是(即將是)氣候難民
按照拉圖的說法,歐洲、乃至於全世界現在的民族國家制度,多少是16、17世紀歐洲殘暴的宗教戰爭所造成的結果。作為政治語彙,「戰爭」是不同集體之間為爭奪生存空間而區別敵友的過程。粗略地說:為解決歐洲境內難以調解的集體衝突,歐洲人便去占取境外無歐洲人(儘管還有別人)的土地,開始一段血腥的殖民史;到了二戰後,儘管殖民統治的正當性不再,土地占取卻變得更加全面——所有想繼續(或效法)歐美經驗的人,全都卯起來鑽到地下、航向海中,奪取那些不管有沒有人(儘管總有別的生命)的土地與資源,開始另一段血腥程度不遑多讓的「大加速」史。
在占領土地這件事上,現代人之所以比其他人更有效率,正是因為他們懂得把土地(以及其他被占有的人事物)變成被動的資源,靜待人探勘。換句話說,現代人懂得不去理會、感受土地的情緒、意願或者「行動能力」。現代人發明的政治體制,便是視萬物為被動的背景,舞台上演的政治戲碼,從而只有人類的行動。
然而,全球氣候變遷顯示出,人類的行為可以大幅度改變生態圈,而這樣的改變,又轉過頭成為限制人類行為的條件。這徹底瓦解了拉圖稱之為「舊氣候體制」的政治體制。一來,民族國家之所以可以擱置戰爭,是因為預設了「在外面,還有土地可以占用」,但當所有土地都被現代人占滿後,這樣的休戰協定便失效了。
二來,再無感的現代人也都發現,自己腳下的土地不只會動,蓋婭女神還很容易激動。總之,現代人發現自己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已發生質變,變化之大,彷彿他們正在失去自己的土地。也許在10年前,氣候懷疑論者還可以找藉口延後面對全球暖化的事實(用的正是區分「應然」與「實然」的託辭),但今天,愈來愈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世代,已明顯感受到舊氣候體制毫無能力處理全球暖化問題。如今,每個人都是(即將是)氣候難民。
拉圖在最近的訪談中,便比較瑞典16歲女孩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週五拚未來」運動,和法國六八學運之間的差別。
我們現在知道,1968年時地球已經進入人類世了,但當時的年輕人(也就是跟著「大加速」一起成長的戰後嬰兒潮)追求的仍是自由與解放,亦即法國大革命以來政治運動向來的目標。儘管兩百年間,人類的物質生存條件已發生質變,但在政治想像裡仍沒有此問題的位置。六八世代當初要求的是「世代交替」、「權力下放」,然而如今年輕人的提問卻更令人憂傷。桑伯格向成年人說:「我們是你們的小孩,但我們很懷疑,是不是還應該要再生小孩。」年輕世代對人類生命延續的疑惑,反應的是舊氣候體制的無力。
如果說舊氣候制度鼓勵現代人加速擺脫一切可能侷限自由的條件,那麼新氣候制度所下的挑戰便是:如今一切都被通用化、抽象化(全都可換算成金錢)了,而且很矛盾地,因為這自由化過程,所有人(以及所有被人占取的事物)反而都徹底糾纏在一起。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還能放慢腳步,講清楚自己所依賴的是什麼?
從追求「自由」到面對「依賴」,兩種政治的差異不可謂不大。
脫歐公投與川普當選,脫韁的自由經濟和惡化的生態環境
出版於2015年的《面對蓋婭》,便是試圖回應上述問題。
拉圖寫作此書時,還不知道巴黎協議的內容(甚至不確定能否達成協議),當時國際地質學學會也還猶豫不決,不知是否該把「人類世」正式訂為新的地質年代(註)。在這等待的氣氛中,拉圖盡量保持冷靜地追蹤可能的理由,說明為何儘管科學家對全球暖化問題早已達成「共識」,這些知識的效果卻是如此有限。同時,他也嘗試用戲劇的方式,模擬不只有民族國家在場的氣候談判現場。
如果說《面對蓋婭》是舊氣候體制的探源和新氣候體制的初步實驗,對拉圖來說,這本書出版後歐美發生的幾個政治事件,更顯示出體制的變換已是現在進行式。
第一件事是英國通過脫歐公投:第一個帶領世界各國邁向全球化的國家,竟然決定放棄這事業,打算回家過自己的生活。第二件事則是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並很快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因為這不符合「美國優先」的政策。同時間,極端的本土派也在歐洲各國紛紛崛起。
怎麼突然間,鼓吹經濟自由化、貿易全球化的現代國家,紛紛提倡起極端的本土保守主義了?許多分析說這是因為全球經濟(強迫性的)去管制政策造成的後果。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造成國內與國際的貧富差距都急遽擴大,於是經濟難民增多,對難民的恐懼也不斷放大。
儘管這類政治經濟分析很重要,但拉圖認為,如果不同時考慮脫韁的自由經濟和惡化的生態環境兩件事,便無法真正處理目前的政治難題。事實上,兩件事的同時性並非偶然。因此,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與美國選出川普政府後,拉圖便著手開始寫《降落何處?》(Où atterrir ?, 2017)一書。

陰謀論:均富已知不可能,權貴極盡掠奪之能事
拉圖說,這本小書可當作是《面對蓋婭》的第九章。在裡頭,他一改行文風格,以直白到有點尖銳的口氣,學氣候懷疑論者構想「氣候門」那樣,也設想了一套「陰謀論」:背後支持川普的人,其實是一小撮最早認清事實的菁英權貴,他們很清楚(在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之時便知道了)氣候變遷是真的,它帶來的限制也是真的,全球化終究只是泡影,這個世界的物質條件根本無法讓所有人享受跟他們一樣的生活。於是他們決定不再管別人死活,想盡辦法掠奪,再鎖起門來保護自己的財產。
換句話說,氣候懷疑論者根本就知道氣候變遷的事實,他們之所以否認,只是為了拖延時間,好讓別人在發現真相之前,藉由去管制的經濟政策,快速幫自己準備好末日來臨時的救難物資。至於「美國優先」一詞,便是利用民族國家的侷限,一方面明白告訴外國人「我們不再和你們共享土地」,另一方面則是障眼法,因為一旦全球暖化繼續加劇,國內最受全球化所苦的民眾顯然不會在「優先」保護名單上!
儘管拉圖說這是他的「陰謀論」,但歷史學家也的確指出氣候變遷研究和跨國工業的關係。例如最早認真看待環境議題的羅馬俱樂部,便由菁英工業鉅子支持。無論如何,如今幾乎所有的證據都顯示全球均富是不可能的。
比方說,要是按照無政府組織「全球碳足跡網絡」2017年的推算,要讓全世界的人都過美式生活,得要有5.2個地球(註)。很顯然,如果「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沒得商量」,而且如果其他人也想過美式(或台式、法式、中式)生活,那麼一定有「多餘人口」得被排除。問題在於大家相信自己屬於1%的菁英,或是50-80%的多餘人口。
通往全球,無法降落本土的飛機
拉圖接著提出一個很簡單的模型。現代化的敘事向來都走在一條帶箭頭的特殊軸線上,這條軸線從本土(local)的一端指向另一端全球(globe),箭頭所指便是「進步」的方向。西方政府的治理方式,不管是左、右派,都是在此軸線上游移,調整在此軸線上的位置。左、右派的差別只在於:如果談的是經濟,右派就是鼓勵全球化自由經濟的進步派,左派則是號召留守本土的反動派;如果談的是社會平等,就換左派鼓吹普世價值,右派堅守本土價值。
但氣候制度的變換切斷了這條從本土通往全球的軸線。近年來歐洲各國或歐洲議會傳統左派與右派政黨的潰敗,或許說明了舊氣候體制已失效。另一方面,少數率先發現事實的菁英權貴已離開這條軸線,走向拉圖所謂的「離地」狀態。這種狀態有點像在太空艙,需要很昂貴的維生設備,自然不能和太多人分享,於是只能把絕大多數其他人拋下(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覺),任由大家在這斷掉的全球化軸線上茫然無措。
「全球」化為泡影,難道就不能回到「本土」嗎?拉圖說,其實連「本土」都不復存在了。一來,經過幾百年的「現代化」,原有小型並且相對自足的社群已被掏空;再加上二十世紀的「大加速」,所有生命與物質都已極其複雜的方式纏成一團、難分難解,很難說哪些東西是真正本土的。歐洲「極右本土派」的興起,也許更多是反映失去土地的焦慮,而非解決困局的方案。2016年英國公投決定脫歐,至今仍擺脫不掉歐洲,亦是難回「本土」的明證。或者照拉圖的說法,英國人是在表達國家認同情感後才發現,如今想要自治(autonomy),有多麼需要考慮到與別人的牽絆,考慮到受制於他人(heteronomy)的問題。
總之,對於這個既無法到達全球、又無法回到本土的情境,拉圖用了一個比喻:大家好像搭上了一班從「本土」出發、飛往「全球」的班機;飛機起飛後,赫然被告知目的地並不存在,而想要返航,卻發現連出發地也不見了。該降落何處,尚不可知,不過至少該知道必須降落。同時,飛機上的乘客必須避免「離地」的誘惑(太空艙只保留給1%的權貴,沒有你的位置!),但尤其必須避免把同機乘客推到離地權貴的身後——那些正在失去土地的人之所以還相信「涓滴效應」,絕望地跟在權貴後頭、期盼擠進太空艙窄門,是因為根本沒有人提出別的選項!因此,光用「無知好騙」描述投「發大財」口號一票的人,恐怕會讓人感受不到裡頭有多少人是因為發現自己被全球化泡影所騙,而感到氣憤、慌張與無措。
也就是在這意義下,拉圖試著提出另一個選項,用《面對蓋婭》裡出現過的「在地」(terrestre)一詞,表達跟「離地」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地的「地族」跟「現代人」不同,前者在全球化夢醒後,決定改變航道尋找降落的土地。「在地」與「離地」這兩端所畫出的軸線,因此完全不同原先「本土」與「全球」的軸線,但這個將長得跟「全球」或「本土」完全不一樣的生存空間,必須要靠「在地人」自己打造出來。由於現代化的進程瓦解了人們原有的集結方式(家庭、聚落、行會、甚至民族國家等),在這個缺乏既有集體的時刻,試圖降落的「在地人」必須重新找出新氣候制度下可能(或應該)有哪些集體,同時勾勒它們居住所需的生存空間。

黃背心運動的啟示:我們必須說得出自己的牽掛與依賴
為此,首先必須了解受困在全球化班機上,大家當前各自的牽絆。在《降落何處?》一書裡,拉圖再度拿法國大革命前後的情況作參考。在大革命前,法國人民曾一度集體地實驗形成新體制的可能性。1789年因為稅制問題,法國民怨沸騰,法王路易十六不得不召開三級會議。由於前次召開三級會議已是一百七十多年前,這期間法國社會已發生很大變化(尤其是資產階級的壯大),因此面對眼前問題,路易十六坦承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國王便要求做一次全國性的調查,要人民在三級會議召開前,具體描述自己的困境,再由各村鎮識字的人彙整集結成《陳情書》(cahier de doléance)。
《陳情書》的最大特點在於把每個村莊、甚至個人的困境都記載得非常具體,比方說誰家搶誰家的水、哪個稅吏貪污等等。拉圖認為,這些《陳情書》大概是法國新、舊制度交替期間最重要的政治發明,因為它讓每個人具體地表達自身的牽絆、依賴與困難。《陳情書》從最小的單元逐步拼湊、繪製法國內部各集體之間相依的牽絆或相斥的利益,從而繪製出一張由下而上的法國人意見地圖。唯有先畫出這張關係地圖,才有可能走到下一步的談判(或戰爭)。
沒想到,率先被迫撰寫「新陳情書」的族群,還是法國人自己。
2018年秋天,法國再度因為稅的問題,激起民怨。馬克宏政府以貫徹巴黎氣候協議之名,調漲運輸燃料稅,觸發了也許是六八學運以後最激烈的「黃背心」運動,至今尚未真正平息。儘管法國政府被憤怒的規模嚇到而延後稅金調漲,卻仍無法阻止黃背心們占領圓環,週週上街頭抗議。
拉圖把黃背心運動稱之為「新氣候制度下的第一場政治危機」,因為它反應出,儘管意識到舊氣候體制不再可行,法國人卻仍不知道在政治上應該如何因應。不只是因為黃背心運動從一開始就透露出「氣候」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今再也無法脫勾,還因為:就算大家都知道不能再按照原來的生產方式過活,但即使只是調整燃料稅這樣單一的政策措施,如今都變得無比困難。所有事情如今都綁在一起,比方說,調漲燃料稅勢必要改變交通習慣,但法國幾十年的郊區化過程,早已讓多數中間階級離不開汽車;要離開汽車,恐怕得離開自己原有的家。儘管上述描述還太過簡略,但牽一髮而動全身確實令政府政策進退維谷。

為解除黃背心危機,總統馬克宏宣布為期三個月的全國大辯論:各地方政府召集民眾,辯論法國人到底要追求什麼價值。然而,儘管法國人向來愛辯論,拉圖對此卻有所保留。因為如同前面所說,價值辯論無法獨立於對現實處境的描述。甚至,如果辯論只是表達空泛的意見,只是表達「我認為應該⋯⋯」,那麼這場辯論不過是民意調查(代表性還很可疑),甚至還會讓政府誤以為辯論完,真的就會知道該怎麼做的錯覺。
對拉圖來說,如今馬克宏政府的處境,有點像路易十六,兩者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眼前的新政治。事實上,至少對民主共和政體來說,新政治體制原本就只能靠公民社會發明出來,政府能做的,只是執行已經發明出來的政治。但另一方面,如果抗議民眾只是重複「馬克宏下台」的口號,這樣的失語狀態也顯示出,在全球化的夢想幻滅後,法國公民社會尚不知道如何描述自己所處的具體情境。學會寫《陳情書》,也許是發明新氣候體制的第一步工作。
在《降落何處?》一書最後一節,拉圖其實已經寫過他自己的「陳情書」。除了簡單描述自己的出身和職業,他也在美國與英國相繼(暫時) 棄歐洲而去之時,表達出對「歐洲」這塊土地的依賴。對他來說,歐洲既然失去軍事和經濟的領導地位,不再有帝國妄想,便正好有機會讓自己「在地化」;況且,身為現代化大冒險以及「全球」想像的始作俑者,歐洲更有責任率先面對蓋婭,接待因此而被失去居所的難民。另一方面,歐洲作為一個可能的領土範圍,也讓其居民再難以躲在民族國家的保護殼裡,儘管歐盟的官僚組織問題重重,但既然人類世複雜的反饋關係早已遠遠超出國家的能耐,唯有造出有別於民族國家的空間,才可能成為蓋婭政治的實驗室。
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除了極端本土派勢力仍繼續上揚,關注環境議題的綠黨支持度也大幅提升。這兩個同步、方向卻相反的變化,一方面顯示面對舊氣候體制的困境,許多人仍想逃回不存在的本土;另一方面,卻也開始有人嘗試改變航道,尋找「在地」的生存空間。
***
一本書談論的主題再恢宏,仍有其成書的特定脈絡和面對的具體問題。本文便是掛一漏萬地把《面對蓋婭》放到歐洲當前搖搖晃晃的政治處境裡。另一個此處無法細談的脈絡,則是「末世感」。儘管從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的暢銷書《大崩壞》出版後,生態破壞與文明崩毀之間的關係便再度成為大家關注的主題,但近年在法國的生態政治討論裡,關於「世界末日」或「現代文明崩毀」的討論卻特別踴躍,除了是媒體熱門的辯論主題,甚至還出現了「崩壞學」(collapsologie)這樣新興的類學科,仔細討論現代文明崩毀後可以採取的作為。
不過這種瀰漫的「末世感」也引發不少辯論。有人認為這種快要完蛋的感覺有助於激發同舟共濟的集體行動;有人則批評宿命的「末日感」反而會降低政治行動的意願,甚至這種感覺,正是現代人盲目前進的動力。拉圖在《面對蓋婭》裡花了不少篇幅談「世界末日」,談現代人「解除抑制」的心理狀態,並追溯到基督宗教的「完結時間觀」,多少可說是在回應這樣的集體氣氛。
話又說回來,一本書儘管總是來自特定脈絡,卻不表示讀者不能在別的情境裡讀出別的意義。台灣當前面臨嚴峻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s)問題,大家的「亡國感」似乎更甚於「末世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將有多大的興趣面對拉圖所說的「蓋婭政治」(gaïa-politics)?今天全球的政治情勢讓人擔心民主政體將要衰退,但也許這種情況反而意味著,至少有些公民社會,儘管不見得自願,總算開始正視其所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所發生的質變。換句話說,民主的價值已與具體描述自身牽掛的能力綁在一起。那麼,以珍視民主價值自豪的台灣人,我們準備好面對蓋婭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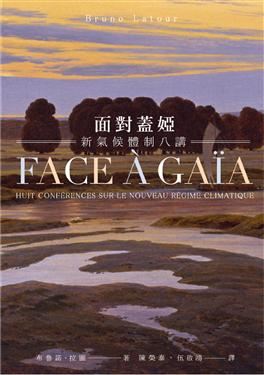
面對蓋婭:新氣候體制八講
Face Á Gaïa: Huit conférences sur le 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
作者:布魯諾.拉圖 (Bruno Latour)
譯者: 陳榮泰、伍啟鴻
出版社:群學
定價:660元
【內容簡介➤】
作者簡介: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
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哲學是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之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1982年起,拉圖任職於巴黎高等礦冶學院的創新社會學研究中心(CSI)。在CSI他與同僚發展並奠定「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的基礎。在2005年底從CSI轉至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的組織社會學研究中心(CSO),2013年起擔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Médialab)負責人。拉圖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