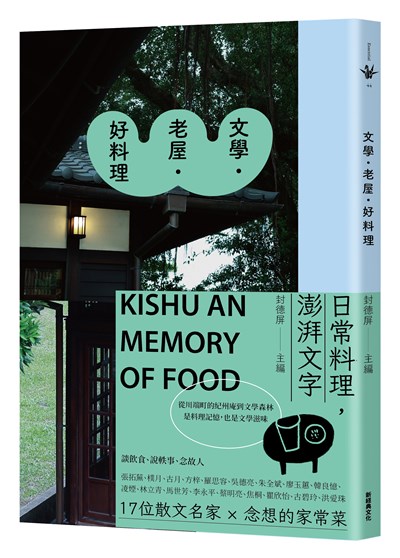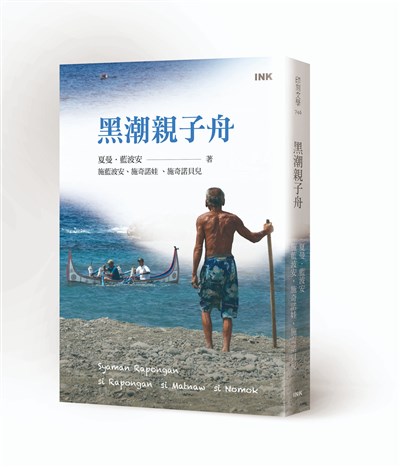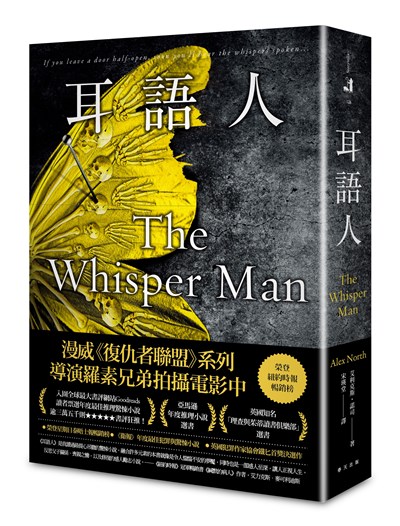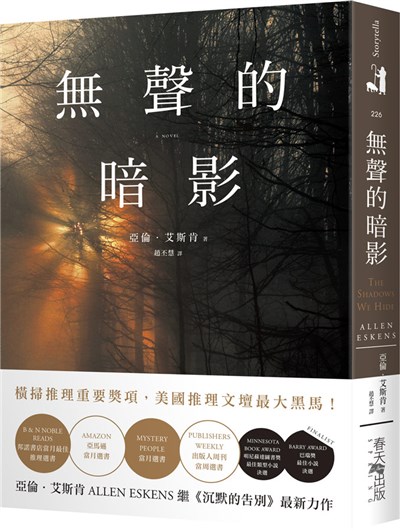
喬沒有見過與他同名的父親。如今大學畢業的他,成為明尼蘇達州美聯社的新進記者,無意發現了一篇報導:內容敘述一名與他同名的男人在南明尼蘇達州的一處小鎮被殺害。
喬對這個人是否是他的父親充滿好奇,卻驚愕地發現小鎮居民對這個已死之人一句好話也沒有,只覺得他早就該死了。喬發現這名死者是個可厭的卑鄙小人,欺騙鄰居,威脅自己的女兒,在妻子也過世後浪擲她的遺產──而這份遺產喬現在可能即將繼承。
喬深陷不確定的泥淖,又被他和母親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弄得焦頭爛額,她又正設法重回兒子的生活中,喬必須把家族史中遺失的片段組合起來,而這趟探究真相之行將把喬帶入瀕死的險境……
內容節錄
《無聲的暗影》
1
我躺在引擎蓋上,背靠著擋風玻璃,曲著膝蓋,十指交錯,放在肚子上,放鬆呼吸,減緩疼痛。我想說被海K一頓是我今天的谷底,但這是撒謊。那個惡棍施加在我身上的拳腳還比不上我給自己的傷害。四周的夜色遼闊無邊,這種晚上會讓你老老實實的沉思,而我是用盡全力在思索。
我覺得自己被放逐了,像個遊牧民族,跟星星樹木和偶爾被夏季的微風吹來的薊草種子分享夜色。我努力思索把我帶到這裡的錯誤轉彎,可我好像找不到什麼可悲的藉口來說這件事不該是我的錯。我想跟亞當一樣,指著給我蘋果的那個人,或者更好,找個辦法怪罪給毒蛇,可是我的良心不肯讓我這麼做。我想要相信我是個更好的人,但是我知道我不是。這次都怪我,不怪別人。
我不知道是幾時發生的,但是在某個時候我狂妄自負了起來。我不再數落自己的不是,被我裝給外界看的形象迷住了—這一面的我讓別人能在我的苦痛中找到他們的博愛。知道嗎,我一直在照顧我有自閉症的弟弟傑若米,已經整整六年了,我有女朋友,我幫著她讀完了法學院。別人看在眼裡,就覺得喬.塔伯特可真是個大好人。他們被我的盔甲的光芒弄瞎了眼,沒發覺那只是錫箔糊的。我老是在等世人某天發現我不屬於這裡,我是從勞動社會的底層爬出來的,所以一切開始瓦解時我是不該驚訝才對。
許多年前,我逃家去上大學,傻不隆咚的,口袋裡沒有半毛錢,我並沒有真的想到我會靠頭腦賺錢而不是靠雙手。我當保鑣念到畢業,經常發現自己對那些較高階層的人懷著等量的輕視和羨慕,那些人的長褲因為坐了一整天而發皺,柔軟的手握著盛著高檔伏特加的酒杯—他們工作的地方不需要鋼頭鞋。要是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心裡想,我會很開心。
我仍記得從美聯社拿到第一筆薪資支票,我拿在手上瞪著看了幾個小時才拿去銀行。真的有人付我錢來讓我思考—使用我的大腦。沒有擦傷的指關節,沒有腰痠背痛。跟我十六歲那年首次加入勞動行列差得遠了—那年夏天我幫我媽的房東裝修公寓。他叫泰利.布瑞摩,我從他那兒學了很多,可是,唉,那份工作有夠鳥。
有一次,在一個能把人烤焦的八月天,眼睛裡刺人的汗水弄得我半盲,我爬上了一處滿是灰塵的閣樓,把厚厚的玻璃纖維隔熱材拖到閣樓最遠的角落,害得我癢了一個星期。另一次,我為了挖一條真正臭氣沖天的水溝,更換壞掉的下水管線,磨破了一雙皮手套。誰會想到我能搞砸一份辦公桌的工作,而且還砸得那麼徹底,讓我竟然懷念起鏟下水道的時光?可我就有那麼倒楣。
說到倒楣的一天,還有比從一個禿頭矮小男手裡接過傳票和訴狀書當開始的一天更倒楣的嗎?我正聚精會神寫著我那天的文章,根本連他的敲門聲都沒聽見—走進美聯社的辦公室是需要密碼的。在聽見他叫我的名字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房間裡,另一個記者指出了我,那人就面帶微笑走向我的辦公桌。
「喬.塔伯特嗎?」他問道。
「對。」
他遞出一個信封,我伸手就接。然後他說:「你被傳喚了。」
起先我沒聽懂,因為他的態度愉快得像是以為會收到小費。「傳喚?」我問道。
他的笑容變大。「你被控侵害名譽。祝你有愉快的一天。」說完他轉身就走出辦公室了。
我拿著信封傻傻站在那裡,不確定該怎麼想,然後我東張西望,看著記者同事的臉孔,希望能看到某個惡作劇的傢伙露出笑容,某個人在憋笑或是咬著嘴唇,但是我只看到同事的眼中混合著恐懼和同情,他們比我先一步想通了是怎麼回事。我拆開信封,抽出文件,認出了原告的名字。州參議員陶德.達賓思。我這才明白不是惡作劇。
我不應該會發生這種事的。我沒做錯一件事,我是一個多月前寫的報導,每樣元素都不缺:性、醜聞、政治權力—樣樣齊全,就只少了一樣,第二手資料,當時還讓我的編輯愛麗森.奎斯不只一點點緊張。可是我給了愛麗森我自己消息來源的真實性,也用確認過的證據來支持我的報導。我說服了愛麗森資料是沒有問題的,最後,愛麗森刊登新聞主要是聽信了我的說詞。
我走向愛麗森的辦公室,給她看指名我以及美聯社為共同被告的文件,希望能聽幾句安慰話,諸如:這種事很常見,或是放心吧,只是腐敗政客的花招。可是她說的話卻害我全身發冷,險些就吐了出來。她讀著文件,臉色變白,接著就叫我關上門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