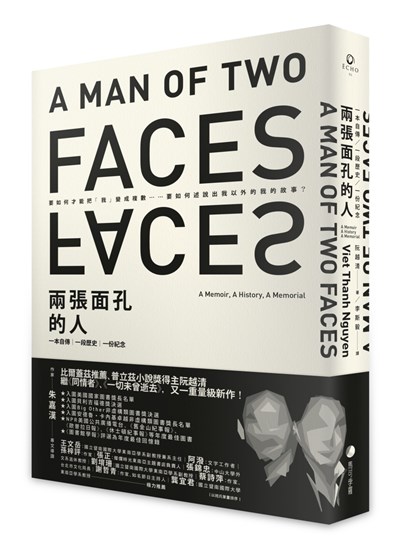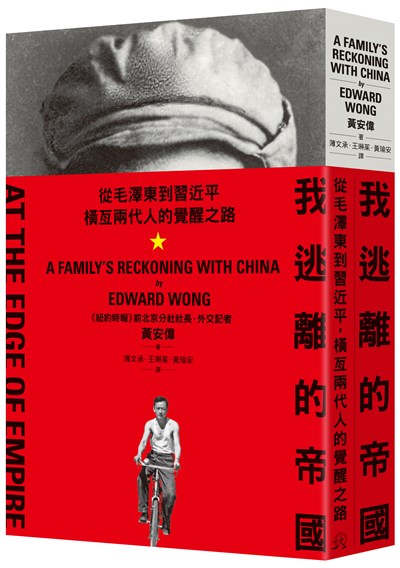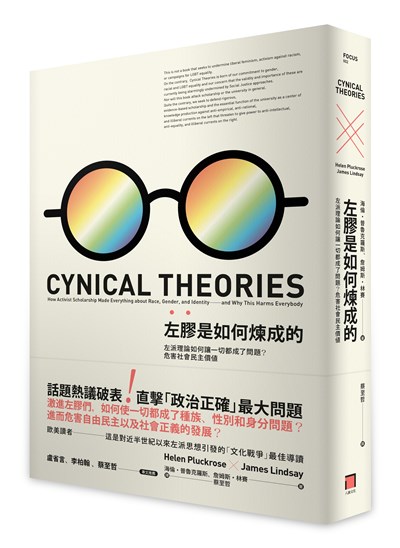本書為凱瑟琳.吉爾迪娜身為心理師的25年間,影響她思考心理諮商的可能與極限的個案。一次又一次,作者逐漸從「醫師」轉變為一名「見證者」,並在這五名橫跨不同種族與階級光譜兩極的個案中,學習如何隨機應變,成為一名更好的治療師。
面對童年曾經歷遺棄、虐待或忽視,個案卻對創傷經驗麻木的情形,作者學會不動聲色,等待時機成熟才詮釋並重新框架個案的情感模式。也誠實面對在治療過程中,個案有時也能操縱心理師導致治療受阻或失敗。一名受創極深的原住民個案也讓作者反省心理學專業從來都是白人所建構,並進一步學習原住民的世界觀及傳統儀式。
與個案一同迷航,並陪伴他們一步步走向療癒的旅程。
文章節錄
《早安,我心中的怪物:一個心理師與五顆破碎心靈的相互啟蒙,看他們從情感失能到學會感受、走出童年創傷的重生之路》
1 被蠢蛋包圍
我以心理師身分私人開業那天,我沾沾自喜地坐在自己的辦公室裡。我在我以知識搭建的 堡壘中,安於我習得的規則,很期待能擁有我可以「治癒」的病患。
我上當了。
幸好我當時不知道臨床心理學這一行有多麻煩,否則我可能就會選擇能夠控制受試者與變數的領域,純粹做研究。相反的,我必須在每週都有新訊息涓滴流入的時候,學習如何臨機應變。 在開業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心理治療根本不是心理師在解決問題,反而是兩個人面對面,一週又一週,致力於達成某種彼此可以一致同意的心理真相。
沒有人比我的第一位病患蘿拉.威爾克斯讓我更清楚地理解這一點。她是由一位全科醫師轉介給我的,那位醫師在他的語音留言裡說:「她會告訴妳細節。」聽到這個,我不知道是蘿拉還是我比較害怕。我剛從穿著牛仔褲與T恤的學生轉型成一位專業人士,身上是八○年代早期時尚必備的絲質上衣與厚墊肩的設計師西裝。我坐在我巨大的桃花心木書桌後面,看起來就像安 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跟瓊.克勞馥(Joan Crawford)的混合。幸運的是我二十來歲就早生華髮,這讓我的外表增添了某種非常必要的穩重莊嚴。 蘿拉幾乎不到五呎高,有著漏斗型的身材,臉上是大大的杏眼,還有一抹豐唇。要是晚個三十年看到她,我會懷疑她有打肉毒桿菌。她有著濃密的及肩明亮金髮,而她瓷器般的肌膚與她深 色的眼睛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完美的妝容、亮紅色的唇膏襯托出她的五官,身上是量身訂做的絲 質上衣、一件黑色的鉛筆裙搭配一雙細高跟鞋。
她說她二十六歲,單身,在一家大證券公司上班。她剛開始擔任的是祕書,但後來升遷到人資部門。在我問她我能幫什麼忙的時候,蘿拉坐著望向窗外許久。我等著她告訴我問題在哪。在 所謂的治療性沉默(therapeutic silence)之中——一種讓人不自在的安靜,理論上是要能從病人 身上導出真相——我繼續等待。終於她說了句:「我有皰疹。」
我問道:「帶狀皰疹或者單純皰疹?」
「如果妳整個人髒透了會得的那種。」
「性交傳染的。」我翻譯成大白話。
然後我問她的性伴侶是否知道他有皰疹,蘿拉回答說與她交往兩年的男友艾德,說過他沒有。然而她在他的藥櫃裡發現一個藥瓶,那跟醫師開給她的是同一種藥物。在我問她這件事的時 候,她表現得好像這樣很正常,而她對此無能為力。她說:「艾德就是那樣。我已經把他罵得狗 血淋頭了。我還能怎麼辦?」
這種司空見慣的反應,暗示了蘿拉很習慣這種自私欺瞞的行為。她說,她被轉介給我,是因為最強效的藥都無法遏制疾病反覆發作,醫生認為她需要精神醫學上的幫助。可是蘿拉很明顯沒 有進行心理治療的欲望。她要的只是解決皰疹。
我向她解釋在某些人身上,壓力是觸發潛伏的病毒發作的主因。她說:「我知道壓力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但我不怎麼清楚那是什麼感覺。我不認為我有壓力。我只是繼續過日子,被蠢蛋包 圍。」蘿拉告訴我,她生活裡沒有多少困擾她的事情,但也確實承認沒有別的事情比皰疹更讓她 傷透腦筋。
首先,我設法讓她安心,讓她知道從十四歲到四十九歲這個區間的人之中,六個人中就有一個長了皰疹。她的反應是:「那又怎樣?我們全都泡在同一池髒水裡。」我嘗試了另一個說法, 告訴她我理解為什麼她很心煩:一個宣稱愛她的男人背叛了她,再加上她身懷實際上讓她幾乎坐 不住的病痛,最糟糕的部分是羞恥。此後她必須永遠告訴她上床的每一個對象她長過皰疹,是帶原者。
蘿拉同意這個看法,但對她來說最糟的面向是,雖然她盡全力擺脫她的家庭環境對她的影響,她現在還是在污穢中打滾,就像她家人一直以來那樣。「這就像流沙,」她說:「無論我多努力設法爬出軟爛的泥漿,我就是一直被吸回去。我知道的,我努力嘗試到要沒命了。」
我要求她告訴我她的家庭狀況,她說她不打算去講「一堆廢話」。蘿拉解釋說,她是個實際的人,而且她想要減輕她的壓力,不管那指的是什麼,好讓她可以控制住痛苦的皰疹。她本來計 畫就只來這麼一次,而我會在這裡給她一顆藥丸或「治好」她的「壓力」。我向她說明,偶有壓力或焦慮很容易解除的情況,但時常都會持續下去。我解釋了我們需要約診幾次,好讓她可以學 習壓力是什麼,還有她如何經驗壓力,以發現壓力來源,然後找到方法加以減輕。她的免疫系統 有可能盡全力在對抗壓力,以至於沒剩下任何力氣去對抗皰疹病毒了。
「不敢相信我真的必須這麼做。好像只是要來拔個牙,卻錯把整個大腦都拔下來了。」蘿拉看起來很厭惡這個結論,但她最後屈服了。「好吧,就讓我再預約一次。」
要治療一位沒打算取徑心理學的病人是很困難的。蘿拉只想治癒她的皰疹,而且在她心裡,心理治療只是達成那個目的的手段。她不想說明家族史,因為她想不通這跟治療皰疹怎麼會有關聯。
在我開始做治療的第一天,有兩件事情是我沒預料到的。首先,這個女人怎麼可能不知道壓力是什麼?其次,我讀過數百篇案例研究,看過一大堆治療錄影帶,出席了幾十次教學訓練會 議,裡面沒有一次碰到病人拒絕提供家族史。就算我在精神病院裡值晚班的時候——在那個地方,心理學上的失落靈魂有如貨物,被他們儲存在後面的病房裡——我也從沒聽過任何人反對提供。有個自稱來自拿撒勒(Zazareth),父母是聖母瑪麗亞與約瑟夫的病患,就算是這種人也提出了家族史。而現在,我遇到的頭一個病人就拒絕提供!我領悟到我必須照著蘿拉怪異的方式與她自己的步調進行治療,否則她就會跑掉。我記得我在自己的筆記夾板上寫道,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讓蘿拉投入治療。 (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