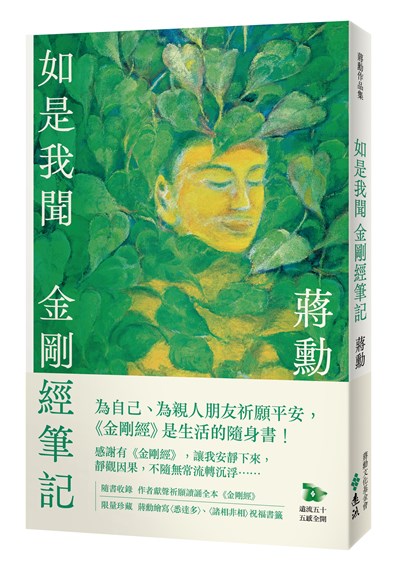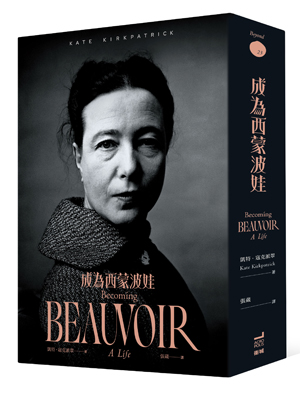
西蒙・德・波娃寫下的《第二性》已是女性主義經典,然而,她本人卻成長於性別極度不平等的年代。當時女性很難選擇自己所期望的人生,縱使才華過人的波娃,也經常因為性別而遭到輕蔑與貶低。但她並不屈服於此,反而堅持發聲,並時時刻刻思索哲學與倫理,思索著人該如何「成為自己」。凱特・寇克派翠使用近年新出土的材料,並檢視過往的回憶錄,寫成這本《成為西蒙波娃》,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波娃傳記,讓我們能更深入理解波娃的人生與思想。
文章節錄
在她過世時,波娃作為公眾人物的生涯已長達四十年——有人愛她,有人恨她;有人奉她為偶像,有人出言詆毀她。由那時起,人們持續以她與沙特的著名戀情與早年生活作為材料,採取訴諸性別的態度,抨擊她道德有問題,貶低她在著作中所提出的哲學、政治與私人領域中的問題——尤其針對《第二性》。波娃曾主張,如果男人想成為有道德的人,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行為協助打造出一個令他人蒙受壓迫的處境,並改善此事。她也曾向女性提出挑戰——別再順從地活在「女人只能為男人而活」的迷思之中。如果一個人曾遭到外界無 _情的拒斥,她的生命便難以強健興旺。
波娃的內在面向從未將自己視為「偶像」。她在與史瓦茲的訪談中說:「我在其他人眼裡是西蒙.德.波娃,但在我自己眼裡不是。」她知道女性渴望找到可供仿效的正面典範,也經常有女性問她,為什麼她的小說裡沒有更多正面的角色,而是充斥著與她所提出的女性主義願景不符的女性角色。有些讀者說她們在書中角色身上看到波娃本人的影子,並納悶著這些角色之所以沒能活出女性主義的理想生活,是不是因為波娃本人在這方面也失敗了?
波娃回答道,她覺得正面的角色「很可怕」,而以正面角色作為主角的書則相當無趣。她說,每本小說「都是一個問題意識」,她的人生也是。
波娃在世時,讀者因為她的生活方式而拒絕接受她的論點——他們說她愛過太多男人,說她愛錯了人,或以錯誤的方式愛人(當時大眾甚至還不知道她的同性戀情)。人們指責她付出太少、付出太多、太女性主義、不夠女性主義。波娃曾承認,自己對待他人的方式並非總是無可指摘。她的言行清楚顯示出,她很懊悔自己與沙特的關係曾令許多偶然的第三者(Les tiers)受苦。
波娃曾聲稱,她與沙特的關係是她人生中的一項成功。史瓦茲也就此事問過波娃,他們兩人是否也成功建立了一段平等的關係?波娃說,他們之間從沒有平不平等的問題,因為沙特身上「沒有任何壓迫者的影子」。有趣的是她在此也表示,如果她愛上的不是沙特,那麼她也不會讓自己受到壓迫。有些人認為波娃這句話是在說,她在職涯上的自主性讓她得以逃脫被宰治的命運。許多女性主義者都懷疑波娃落入了壞信念中,懷疑她是否把沙特「變成了連自身的批判目光都必須止步的聖域」。
如今我們已很清楚,波娃對沙特有諸多批判——但她批判的力道對許多人來說似乎不夠。
八○年代中期,有個美國哲學家跟研究波娃的學者瑪格麗特.西蒙斯說,她很不滿波娃在自傳裡老愛說我們、我們、我們。她為什麼不說她?「她彷彿整個人都消失了。」但她其實沒有消失,她一直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她用自己的聲音說出「我們」和「我」,因為她認為「就算身為女性主義者,還是可以與男人擁有親密關係」。事實上,人能與許多不同的男人與女人擁有親密關係。她認為,她的思想是她這個人最重要的部分,而沙特是她在思想上無人可比的親密摯友。許多來自外在面向的書評批判波娃只是沙特的影子、說她毫無想像力;連她的戀人都說她的書很無聊,或是跟哲學有關的內容太多。但在波娃這輩子的多數時間裡,沙特都是那個大力鼓勵著她的人,在這場舉世無雙的對話中持續與她的心智進行交流。
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波娃內在面向的完整全貌,經過重述的人生故事不等同於實際的人生經歷。但就外在面向而言,我們必須記得她奮力成為自己時所展現的能動性。在某些情況下,她也選擇寫出那個被忽略的「我」字。在《環境的力量》中,她說她早在認識沙特——這個後來會以《存在與虛無》一書聞名的哲學家——之前,就發展出了一套關於存在與虛無的哲學看法。「二十歲時,我在私人日記中初步探討了存在與虛無的問題——我所有的作品都叩問著這個問題卻從未得到解答。」她也在寫出《女賓》之後表示,事情已有所改變:「我一直都『有話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