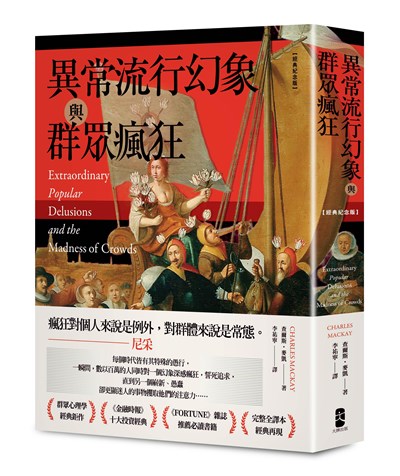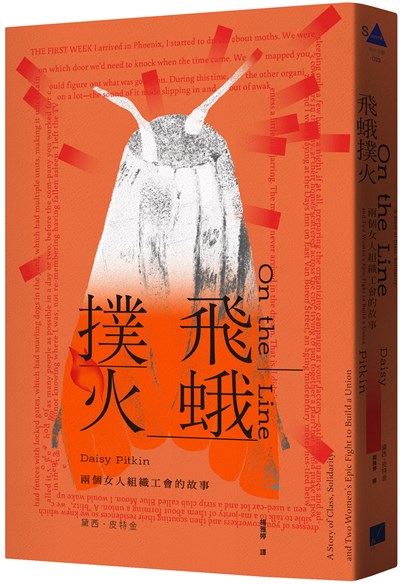
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勞動條件愈來愈糟,是全球的趨勢,還有什麼條件組織工會?
這本書描寫組織洗衣廠工會的艱苦過程,有珍貴的歡笑、互助、友誼,同時也反省工會內部的民主、組織者由上而下的領導性、對於掌握權力的錯誤妄想、上級工會的政治鬥爭……在勞工運動中,要面對的不只是資方,也包含你所屬的工會及你自己。另一方面,書中也爬疏美國勞工運動百年來未正視的性別議題,「工會的男人總認為女人是靠不住的士兵」,然而一九○九年受不了男性工會幹部空話而上臺登高一呼總罷工的,是一位縫衣女工。
作者黛西和墨西哥女工阿爾瑪在這場勞工運動中是並肩的戰友、親密的朋友,但仍要面對的是,專業組織者和其協助組織的工人,核心的差距是什麼?
內容節錄
《飛蛾撲火:兩個女人組織工會的故事》
一. 蛾 Las Polillas
抵達鳳凰城(Phoenix)的第一週我便開始夢到蛾。我們每晚只睡幾小時,甚至通宵熬夜,為你們工廠的工會組織運動做準備:蒐集你同事的姓名地址,然後勘查其住所,以得知哪幾家有圍籬,柵門會上鎖,哪幾家院裡的狗會吠,哪幾家是多戶合棟,不確定到時候該敲哪扇門。我們以這種方式繪製你同事的分布圖,標示他們分散在市內各處的住家,試圖擬出計畫,以期與他們大多數人商談組工會的事。我們稱此行動為「閃電戰」(blitz):趁著你上班的公司還搞不清楚狀況,在一兩天內掌握到盡可能多的人。
這期間我和其他組織者住在東范布倫街(East Van Buren Street)的戴斯旅館(Days Inn),這家老舊的汽車旅館從二十世紀中開業至今,坐落於中古車行和名叫「藍月」(Blue Moon)的脫衣舞吧之間。我會在陌生的房間醒來,不知身在何處,也不記得怎麼睡著的。我多半讓電視開著——它的聲響使睡睡醒醒的轉換感覺不那麼突兀。夢裡的蛾從不曾降臨過。意思是,我沒看見牠們從別處飛來。沒看見牠們降落在我身上。牠們突然就覆蓋了我,彷彿一直都在那裡。我趴在汽車旅館床腳的髒地板上。睜眼。抬頭。往下看自己的身體。每個皮膚細胞都鋪滿了蛾。每一寸都是灰白褐相間。無數粉狀細鱗。撲拍著。
多年後,我在土桑市(Tucson)的酒吧上班,那時我早已離開工會,因為目睹(並造成,我知道)我們奮力打造的一切分崩離析令我疲憊、厭倦又悲傷,而且不知怎麼就決定這些感受可以讓我心安理得地不再做組織。我任職的酒吧原本將毛巾與餐巾外包給一家小型工會洗衣廠清洗,後來改交由另一家規模更大的區域性非工會洗衣廠。當初接這份工作,部分是因為它的世界與我在全國各地領導的工會運動相距甚遠,至少我這麼以為,但酒吧的髒毛巾當然也需要清洗。為了換廠的事,我先後向經理、老闆和房東抗議,甚至在酒吧的某位股東進來喝一杯時對她陳情,但那家非工會洗衣廠比較便宜,而我也不再跟工會的任何人聯繫,沒立場與酒吧同事組織任何形式的抗爭。有一天,非工會洗衣廠派了新司機來收件,他清空屋後儲物櫃裡的髒布巾時,我認出了他:在你們洗衣廠進行抗爭的那段時間,他是跟工會對幹的司機之一。他算是比較惡劣的那型,我仍清楚記得他開著卡車經過我們正在發傳單的停車場,汗流浹背、滿臉通紅地從車窗咆哮「婊子!」「蟑螂!」和連珠炮似的辱罵。他沒認出我,就算有也沒說什麼。
那星期稍晚,我因為高燒和背灼痛掛急診。兩個月來我已經跑三次醫院,每次都需要一劑嗎啡才頂得住感染的疼痛,有次是為了排出腎結石。護理師將藥劑注入點滴瓶,我的臉愈來愈重,腦袋嗡嗡作響,身體僵硬顫抖,體溫隨著冷藏過的輸液滴進血流而驟降。我們在你們洗衣廠發動工運已是八年前的事,我們最後一次說話是三年半前。而我索取被毯,再要一條、還要一條時仍想起你,阿爾瑪。當護理師走到簾幕隔間的角落,從金屬櫃抽出毯子,在床上方抖開薄薄的布料,當它們飄落下來,每張毯子都讓包裹我身體的繭再加厚一層,我想到你。我想到你和桑迪亞哥、安娜莉亞、安東妮雅、芮娜和西西莉亞。那間醫院是大學醫學中心,將被服布巾外包給你上班的工業洗衣廠。你觸摸過那些被毯。你觸摸過床單、枕套和我穿的病人袍。我出院後,組成這顆繭的布巾會被放進塑膠垃圾袋,跟其他塞滿布巾的垃圾袋一起裝進底部有滾輪的藍色垃圾箱,再被推上你們工廠的洗衣車——那種十八輪巨型卡車——連同其他數十個藍色垃圾箱,卡車會沿十號州際公路從土桑開到鳳凰城,垃圾箱會被卸載到汙物分揀部,你可能正在那裡工作,塑膠袋會被某個在作業線前端工作的人撕開,那大概不會是你,但可能是桑迪亞哥,被服和布巾會經由輸送帶傳到你工作的位置,而你會再度觸摸到它們。
那晚我獨自待在醫院。雖然我跟你一起花了許多年封守自己,絕口不提恐懼,但我承認我很害怕。害怕似乎沒人知道造成感染的原因,害怕它會蔓延至身體其他部位。這些既不屬於我、也不屬於你的床單被毯,我彷彿透過其粗糙的布料接觸到你,因而獲得撫慰。我記得你害怕時笑聲多麼尖銳響亮。從被毯裹成的繭裡,我聽到了。
隔天,在家裡沙發上發著燒的我,開始寫這些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