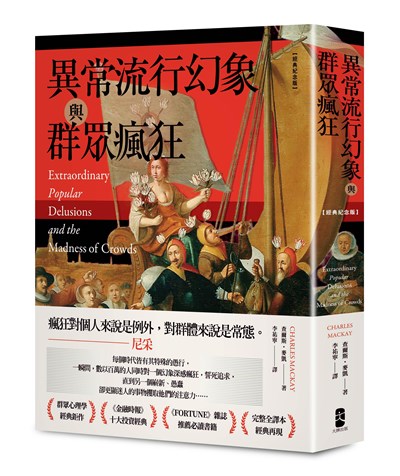這是一本用100年的視野觀看中國發展的社會科學論述,在近年改革開放、經濟躍升發展的局面中,作者許知遠卻警覺的指出,中國努力改革了100年,卻還是個未成熟的國家,經濟傳奇的背後,潛藏著不可輕忽的危機和風險。
許知遠在大陸是有高知名度的知識份子,1976年出生,北京大學畢業,作為大陸年輕一代的評論家,又不是絕對的異議份子,現為英國訪問學人,瞭解世界趨勢與世界對中國的期待與批評,而能在這本書中縱覽中國現代變遷的軌跡,又能提供體制內對中國體制的批評。
書中從清朝的衰微觀察到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到鄧小平,沒有逃避1989年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仍然探討中國在現代化的努力中,專制對中國長期的影響,並指中國遲早要面對民主,尤其經濟改革造成資源分配不均不公的弊病,有必要以更民主的方式分配資源。
在一般從經濟發展優勢的經濟管理角度觀察中國的論述之外,這本書提供純批判角度的縱觀評論,從相當程度代表中國改革開放新一代觀點所作的論述,對於外界想要瞭解的中國,有很多的代表性,尤其年輕一代的自省,告訴世人也告訴中國人自己,中國在強勢崛起的光鮮外表下,仍是個未成熟的國家,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文章節錄
誰更了解中國?
在風景如畫的三峽建立世界上最壯觀的大壩,照亮長江中下遊;將經濟增長帶入廣闊的西部的內地,用管道將石油天然氣運輸出來;翠綠的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中那些數不清的醜陋的工廠的工人們每天十二小時、每周七天、每月心甘情願地只掙一百美元的生產著打火機、鞋帽、空調、微波爐、玩具,將它們充斥到阿富汗的小商品市場與美國的沃爾瑪超市中;中國的領導人前往俄羅斯、加納、智利、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持續高溫的中國經濟需要更多的鋼鐵、石油;施若德、盧拉、席哈克、瓦傑帕伊拜訪北京,他們需要這個市場;中國的勞工飄洋過海、翻越戈壁,前往美國、歐洲、東南亞、中東、南美洲、北非,開餐館、開超市、修公路……他們既建設自己的家園,也改變世界的面貌,他們製造了矽谷式的奇蹟,到納斯達克上市,收購了IBM的電腦業務,他們也忍受低工資,付出汗水、鮮血乃至生命。
但是,如果你願意把你的眼界放得再開闊一點,再深入一點,扔掉報導中國奇蹟的商業媒體,離開北京、上海的金融中心,不去參觀世界工廠中的生產線,當你的視線稍稍偏離時,你就看到了另樣的中國。生活顯得停滯,不那麼充滿希望,建築是粗俗醜陋的,年輕人眼神迷離,山川河流是被汙染的,像一個世紀以前一樣,土地仍不夠耕種,通往城市的打工之路日漸狹窄,要想進入世界經濟循環的鏈條,他們需要更多的技能。
我常常疑惑,二零零五年的中國人和一九零五年的中國人還相似嗎,和一零零五年的中國人呢?直到今年,我才認真地閱讀林語堂出版於一九三五年的《中國人》,那一年也是魯迅去世的年份,這位二十世紀最傑出的作家告訴我們,中國傳統一片漆黑,只有奴隸、太監和吃人的禮教,那一年也是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的高潮,打麻將、隨地吐痰、衣衫不整,這些中國人的惡習必須被克服,代之以清教徒的清潔與克制。但是林語堂卻在批評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之後,談起了中國人的內心平和、特別的幽默感,那些動人的詩歌、戲劇、繪畫、書法,中國人在面對災難時的韌性和勇敢……
中國太過龐大,太過複雜,人太多了。一九零四年時,世界有十六億人口,中國是四億,二零零四年時,對應的數字是六十五億與十三億。它擁有世界第三大的領土面積,漫長曲折的邊界至少與十四個國家相鄰,並和其中的一些國家不可避免地發生過衝突。當她的北方大雪紛飛時,她的最南方仍被裹在炎熱之中,儘管都是中國人,他們在體魄、性格與習俗上卻相差甚遠。東北人的高大和福建人的短小差異顯著,如果一個廣東人試圖用方言與山西人交流,障礙是可以想像的,而杭州人似乎也永遠適應不了四川菜的辛辣……一些早期的外來觀察者很容易就發現,中國各個省份間的差異就像歐洲不同國家間的差異,他們彼此間還如此冷漠,當整個東北被日本占領時,上海仍舊歌舞升平,以至於他們總是疑惑,這麼一個國家究竟是按照什麼樣的方式組合在一起並運轉的。一份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在一八六八年寫道:「什麼是保持中華帝國完整的力量?……每年都預期它會滅亡……然而,在麥基洗德(《舊約》中的人物)的時代就充滿活力的帝國還可以比所有成長中的年輕國家存活得要久,並且當所有的歐洲之國和君權被打倒摧毀時,她仍然保持了一種持續不斷的活力。目前,什麼是在那個地方把廣大不調和的領地結合於一體的紐帶呢?」
伴隨著中國的每一次劇烈的變化,這個疑問就會被再次提起。如果說地域上的差異已維持了幾千年,那麼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三條主線的失調則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種種災難的根源。曾國藩、李鴻章一代人試圖僅僅通過軍事技術上的更新而最終失敗了;孫中山則依靠複製美國的政治制度也遭遇重大挫折;鄧小平的改革給中國帶來了一百五十年歷史上最富希望的時期,但改革僅僅侷限於經濟領域的單向街上,導致的文化與政治上滯後的後遺症愈發明顯。
關於中國的描述總是在兩極之間搖擺——它要麼前途光明得不可限量,要麼就處於崩潰邊緣。自從拿破崙天才地創造了那句關於中國的格言之後,人們就不斷地在「覺醒」與「沉睡」的判斷之間跳躍。政治家與知識分子們說,我們無法創造出解釋中國的理論,因為它過於複雜——擁有過分悠久的歷史、過多的人口。但事實上,沒人能創造出任何能夠解釋任何國家——不管它多麼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