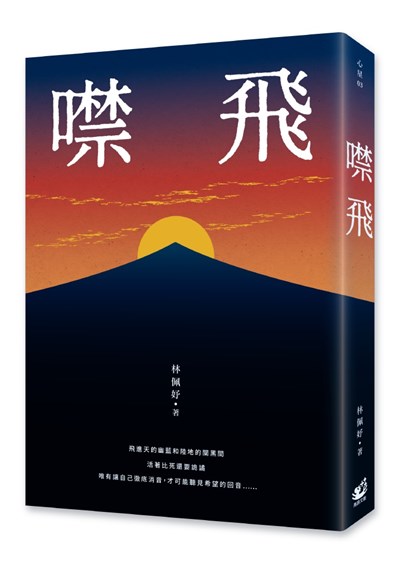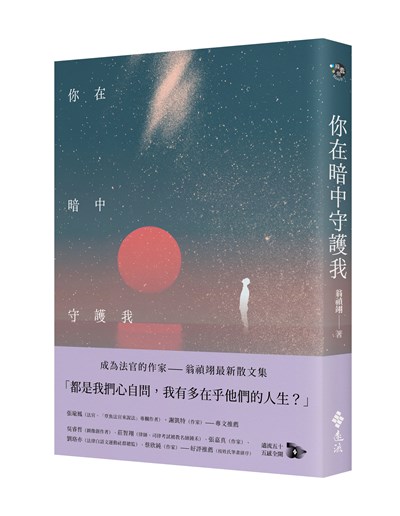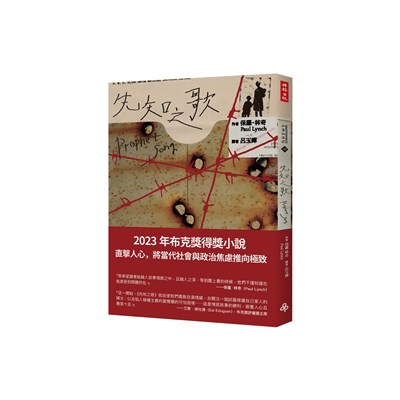真正的台灣文學史記載始自本土作家葉石濤1987年完成的《台灣文學史綱》,但不算完整,中間陸續出版各種版本,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陳芳明剛完成的《台灣新文學史》,從1920、1930年代寫到現在,幾近百年的回顧,可說最完整。不過,他奠基於殖民史觀的台灣文學史觀,難免被批評,他歡迎批評者一起討論並講出道理來。
作者從1999年開始發表台灣文學史論,並在《聯合文學》連載,歷經十二年,終於完成近五十萬字的重量級著作。他寫台灣「新」文學史,指白話文的新文學歷史,另外,如何詮釋歷史的思想脈絡也會影響作者如何選擇歷史材料,在這方面,他以殖民史觀貫穿台灣文學史。
台灣於1895年到1945年日據時的文學從殖民史來寫沒問題;但把1945年台灣光復到1987年台灣解嚴期間稱為再殖民時期,1987年解嚴後,稱為後殖民時期;這種以國民黨政府也是某種程度殖民的史觀建構的台灣文學史,難免會遭到批評。他則認為不同史觀也可講、寫出不同的台灣文學史,才不會失去對話空間與發言權。
作者認為中國文學史只是中國漢民族男性文學史,不僅在五族文化的文學上有欠缺,更以男性沙文文化為主,他則很重視女性文學作品,特別以專章討論。他也試圖觀照到每一種相對地邊緣議題,包括原住民文學、同志文學等等。即使政治背景比較台灣本土主義,他仍努力不以太強的政治觀詮釋文學史,並以藝術性、文學性的角度考量,為讀者提供觀覽百年台灣文學的嶄新視野。
文章節錄
張愛玲小說中的現代主義
在現代主義風起雲湧之際,張愛玲文學在台灣也普遍傳播,蔚為台灣文學的奇異現象。張愛玲文學是由夏志清的評論而介紹到台灣的。這個陌生的名字與台灣社會初識時,從來並未預告她將成為「張派作家」的奠基者 。一位從未在台灣成長,也從未有任何台灣經驗的作家,竟然能造成風氣,絕對有其複雜的理由。張愛玲不是台灣作家,但是她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恐怕比起魯迅還要深刻。
張愛玲的小說被介紹到台灣,便是在香港出版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由於這兩部小說寫的是中共統治下人性被扭曲的故事,這種題材較諸台灣盛行的反共小說還來得真實生動,張愛玲遂被誤為反共作家。然而也是因為透過如此的誤解,她的文學作品終於能卸下「漢奸」罪名而開始進口到台灣。張愛玲能夠受到廣泛的接受,並不是因為她的反共立場。較重要的是,她小說中透露的技巧,與當時現代主義的風尚有相互重疊之處,因此,文學品味正好可以與當時讀者的審美銜接起來。然而,張愛玲小說精采的地方尚不止於此。她的故事有上海鴛鴦蝴蝶派的韻味,卻能夠把才子佳人的故事寫得更為殘酷而蒼涼。她的文字語言則有《紅樓夢》式的華麗與絕美,卻又鍛造得更為流暢透明,常常帶給讀者奇異的美感。因此,她的作品不斷被傳誦之餘,無形中也使讀者更加能接受現代主義的奧妙。
她的小說真正在台灣連載,便是從短篇小說〈金鎖記〉改編為長篇小說〈怨女〉,於一九六六年四月起在《皇冠》做系列的發表。這篇作品給讀者有了驚豔之感,使她的早期創作生涯開始受到好奇的關注。《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在台北正式出版後,便開啟了此後的張愛玲熱。不能否認的,在台灣的政治封鎖下,她的小說引發出來的想像與欲望,超越了當時許多作家的格局。在現代主義美學的建構上,張愛玲沒有現代作家那種沉重的使命,她是把具體的生命經驗提煉成為文學藝術。那種內心情緒的刻畫,既是現代主義的,也是寫實主義的。文字的魅力,使她的小說讀來更為繁複而豐碩,幾乎每一次閱讀都可挖掘到全新的意義。她的文學會造成風潮,她的技巧會獲得模仿,誠非偶然。
張愛玲的文學特色,既是接受傳統,也是抗拒傳統。對於中國固有父權文化之批判,她確實具備了非凡的勇氣。然而她並不使用激烈的字眼,而是反其道而行,以細膩、幽微的詞句,並以近乎鄙夷的語氣對宗法社會投以最大的輕蔑。在相當引人矚目的小說〈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她刻畫一位極平凡的女性嬌蕊。這位女性小人物被主角振保遺棄之後,仍然生活得非常理直氣壯。反而是振保竟然不能接受這樣的事實,徹底被擊敗了,毫無緣由地淌下眼淚。張愛玲在這篇小說裡強烈暗示,男性彷彿是強者,是權力支配者。然而,一旦女性不再被支配時,男性頓時就變成了弱者。她的小說清楚揭示,女人好像是四季循環,是生老病死,是飲食繁殖,則無論何種折磨痛苦都能承擔下來。這種穿透紙背的人性刻畫,近乎無情冷酷。與當時政治口號虛構出來熱烈的反共文學比較起來,她的小說特別顯得真實無比。
張愛玲以她的小說,具體示範給台灣讀者認識何謂現代主義美學。她擅長描寫封鎖、出走、斷裂、背叛、孤絕等等的隔離美學,最佳的作品當可見諸〈傾城之戀〉。這篇小說所以引起眾多的討論,就在於它與同時代的無數小說完全不同。抗日戰爭裡的中國作家,幾乎都被驅使去撰寫國防文學或民族文學。這種在砲火下提煉出來的作品,自有其高貴情操的一面;然而,人云亦云的作品,甚至相互模仿腔調的文學也大有人在。千篇一律的口號、吶喊、教條,似乎淪為制式的複製。張愛玲在步伐一致的浪潮中,選擇相反的方向,揮筆解剖中國封建社會的黑暗。她之令人側目,就在其他作家渲染光明色調之際,她跨入黯淡的世界。
張愛玲撰寫《秧歌》與《赤地之戀》這兩部長篇小說時,已經與中國社會是隔離狀態。更為重要的,她對中共政府也保持高度的疏離態度。所謂疏離,乃是指她所賴以生存的社會應該是耳熟能詳的,她所認識的中國百姓應該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一個父權體制建立起來之後,她的生活環境反而淪為畸形的存在,不僅讓她陌生,甚至還使她恐懼。即使是張愛玲本人的生活,也必須揮別小布爾喬亞式的世界,全心接受勞動入民的改造。
張愛玲寫完《秧歌》與《赤地之戀》後,似乎沒有繼續更出色的創作。不過,對一位傑出的作家而言,倘然作品是重要的,並不需要多產而豐收。世故老成的她,在二十歲到三十歲之餘,就已經塑造成熟的心境。在年少時期,她便能透視人世的蒼涼悲歡。世間沒有一件愛情不是千瘡百孔,她在年輕時代就已經如此喟嘆。然而,要描寫的不是愛情,而是愛情背後的黑暗人性。從〈傾城之戀〉到《赤地之戀》,張愛玲再三穿越於人性明暗的縫隙之間。她的筆觸冷酷悽慘,只為反射人的陰暗醜惡。只是,蒼涼盡處,並不全然絕望。就像〈傾城之戀〉那樣,人還是可以尋找到光明的出路,只是要開啟一個時代的閘門,就必須勇於棄擲黑暗的父權。
張愛玲小說在一九六○年代風行時,現代主義的擴張已經臻於高峰。回顧這段歷史,當可理解現代化運動徹底使台灣作家重新思索創作技巧的問題。這種技巧的鑄造,建立了現代文學世代的重要風格。在六○年代崛起的作家,他們的許多作品都升格成為文學經典。這場壯闊的運動,無論遭受何等負面的評價,畢竟已經改變了台灣文學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