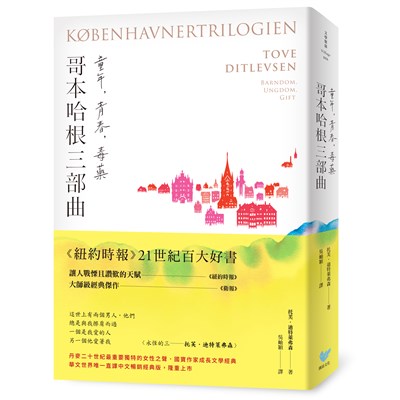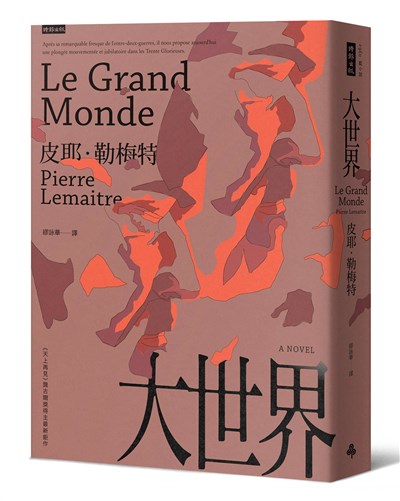這裡最多的不是芭樂、襪子或董事長,而是失序與瘋癲。
瘋掉的董事長「但丁」找不到他的羊駝;完美主義的高材生鄉長準備宣布大事;三姊妹的一號要上臺唱歌;三號被候鳥催促著快回來;而二號,二號只想朝世界尖叫。
當遊客稀少的小地方湧進了整團迷霧,短短一個禮拜,有人的世界崩壞,有些人從廢墟中長出來……或許太多人姓蕭的社頭就是個就是蕭了了,痟佮有賰的所在。從星期二到星期六,看社頭人的寂寞群像,該笑的該哭的該崩潰的齊聲喧嘩,共同迎接史上最瘋狂的織足常樂超級芭樂星期六!
內容節錄
《社頭三姊妹》
一號醒來,想吃稀飯,有死亡的預感。
一切,都不一樣了。
空氣有葵花油質地,黃橙黏滑。床頭燈色調變了,明明是熾熱白光燈泡,怎麼隔一晚就蒼老了,閃爍黃暈色調。哪裡來一大隻冰涼的死魟魚黏貼在她身上?喔,原來是吸飽整夜溼氣的棉被。她躺在床上瞇眼觀星,在自己的雙臂上數老人斑,兩根長斑的繁星香蕉,數啊數,一夜多出了十幾顆星星。
有涼風。對,竟然是涼的。怎麼可能是涼的。今年夏天好漫長啊,以為會一整年都是夏天,終於,在熱死之前,等到風涼。稀薄淡霧從清水岩林間啟程,一路翻攪,方向隨意,經過芭樂市場,籠罩芭樂園,刷過社頭運動公園,越攪越濃稠,變成卡布奇諾的奶泡,慢慢覆蓋整個臺灣中部小鄉,抵達火車站,悄悄溜進火車站正前方的社斗路小巷,來到一號居住的三合院,霧稍微遲疑了一下,這戶人家一直都有點可疑,不,不是有點,是非常可疑,入口地上放了個小燈,上面寫了幾個醜字,老屋,敗瓦,頹磚,亟需補葺,卻一切整潔有序,太乾淨了,太奇怪了,屋內住了個老男人,喔不不不,霧困惑搖頭,其實是個老女人,剛剛醒的短髮老女人,整個社頭鄉都還沒起床,沒人說話,霧卻聽到好多聲響,這三合院有話有語有吟有嘆有叫有喊,稻埕不晒稻不晒乾菜不晒棉被不晒芭樂不晒衣服不晒襪子不晒狗,種了許多奇異花草,花香葉脈都非本地種,霧繞著三合院外牆滑行,覺得屋內時區與空間不屬於這鄉鎮,疑似凶宅,有濃重的死亡氣息,決定不想入屋,無奈涼風胡亂推進,霧入埕,進正房神明廳,闖廂房,那房窗戶洞開,老女人就睡在裡面,霧真的不想進去,實在是不得已,清晨涼風剛剛從山區那邊出生,還是調皮哭鬧的嬰兒,不懂節制,亂踢亂推,霧就滑進去了。
她竟然忘了關燈,想到電費,罵自己白癡,伸手用力拔掉插頭。昨晚上床,高溫在臥室裡忘情森巴,不可以,她握緊手心,不可以開冷氣,電扇也搬出去,就是不准自己開電器,熱又怎樣?睡著就不熱了,躺下快睡,幹你娘少囉唆。一直喊熱死了熱死了,但怎麼死不了,該死的賴活,不該死的卻都死光光。身體反側,皮膚噴出的都不是汗,是撢不掉的過去還有悔恨,背部往事溼透,卻什麼都沒揮發蒸散,一切都沒忘。她一直跟自己說,睡了就好,死了就好。卻實在是睡不著,也不知道該怎麼死。起身開窗邀風,不夠不夠,風不來,乾脆直接把窗框整個拔掉,風才進得來。老窗鏽朽,在她手中癱成一張死亡證書。拆窗根本是盜墓,驚醒陳年沉睡汙垢,漆塊木乃伊,黑黴乾屍,飛塵鬼魅,她眼睛無法容納清晰可見的紊亂髒汙,掃把畚箕拖把漂白水,不夠不夠,一桶水抹布刷子,臥室這側洗不夠,還必須洗外牆,熱死了,但不弄乾淨,頭皮萬蟻,腳踏針床,更不可能睡得著。鄉間寂靜,假如鄰居此刻聽到拖把擊打水桶,竹掃把刮傷地面,好奇朝這三合院探頭,看到她在那邊東刷西洗,一定不會感到意外,也不會覺得是夜半女鬼,反正是那個一號痟查某啦,發神經,或鬼神附體,都這麼晚了,還忙著大掃除。受詛咒的瘋女人,做任何怪事,無人稱奇。
她想不起來昨晚到底幾點睡著。今天是星期一還是星期二?窗框跟窗玻璃都不見了,牆上一個長方形開口,邀霧入臥。
這白茫茫的氣體是什麼?霧?她還在夢中嗎?社頭多久沒起霧了?
她推開魟魚,起身看霧,霧氣拉扯身體,韌帶摩擦,關節推擠,骨頭發出吵鬧的喀喀喀聲響,太吵了,彷彿身體裡住著一群火雞。她都已經用力推開霧,在床上坐穩了,那群火雞還在叫。
揉眼,眼屎堅硬巨碩如蛋,卡在魚尾紋裡,鳥鳴入耳,她懷疑夜裡有鳥入窗,在她眼周下蛋。手指捏碎那些鳥蛋,她用力張開眼。
看到了。
有人快死了。
不知道是誰,但,確定,有人快死了。
她無法控制她的預感。她無法解釋她的預感。不定期,挑季節,夏天真的太熱,少見,所以三合院門口地上那盞小燈,夏天時常不通電,恁祖媽不爽做生意,太熱流太多汗,股溝濁水溪,肥肚大肚溪,兩條腿臭水溝,不想賺錢啦,等天氣轉涼,預感比較容易發生。預感不受情感理智控制,那是一種視覺的傳喚,通常是眼睛看到了什麼,觸及了腦子深處的弦,聽到某種短促而鋒利的高音,類似拿菜刀在砧板上用力剁活雞頭,夢境受到壓迫,噴出顏彩汁液,擠出視覺預感,世界一皺,身體地震。她就知道了。這種「知道」,不是取得知識,並非語言傳導,真的硬要解釋,像是收到影像訊號,她必須以在家庭在學校習得的語言系統翻譯這些訊號,以最粗淺的說詞,傳達給人類。有人說這是通靈。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她不知道什麼是「靈」,問她是鬼是神是大自然還是胡謅騙人,她會聳肩,她哪知道啦,桌上神像不言不語啊,該燒香該燒紙錢該擺上貢品,她祭拜禮數周全,但那些神從來不跟她對話感應,她總是說最好不要信我,我幫不了你,你幫不了我,但拜託,要包紅包,你買中午排骨便當要花錢,啊我沒辦法從空氣中抓出炸排骨,我也是要生活。除非,真是命苦人。
此分此秒,她的眼睛凝視晨霧,沒戴老花眼鏡,沒開燈,眼前氣流凝滯,要是被帶去看眼科,醫生一定有科學解釋,說有輕微白內障,嚴重一點就要開刀。但這不是醫學。面前的現象,科學無法解釋,整個社頭,可能只有這老三合院裡面才會發生。霧抖動了一下。對,霧有形有體有命,沒有眼睛,但,她知道,霧跟她對看。霧在人類抵達此地開墾前,已經居住在清水岩山區,若是隨手擒一把汽霧,利刃橫切剖開,會看到幾世紀的年輪。霧有自己的語言系統,無聲息,人耳聽不見,文法是濃淡。此刻,霧濃,從她身體彈開,跟她保持一公尺左右的距離,看著她,姿態是警戒的貓。她眼周肌肉抽動,眼屎終於全部掙脫皺紋夾縫,一地碎鳥蛋。昨晚的夢境流淌,指尖長出玫瑰刺,睫毛鋸齒扭曲,脣紋螺旋,死皮掙脫腳踝,腋毛彈簧壓縮拉伸,她想起來了,夢裡的顏色光影物件溫度聲音時間。物件是磚塊。顏色是秋日黃葉。有涼風。好多好多人尖叫。有人哭有人笑。一道鮮黃的光。誰在吃火?又冷又暖。時間就是這幾天。本週。眼前的世界變成一張紙,有股力量,她看不見的力量,把面前的紙抓皺,迅速又攤平。
她清楚自己是個被時代拋棄的老女人,但她知道怎麼用現代的語言解釋這種預感。以當代語言形容,這就像是,她腦中播放電影預告片。災難片,鬼片,推理犯罪片,反正不管什麼類型的片,都會有人死,電影本週上映。
完了。是誰。怎麼辦。管他。隨便。她只會預言。卻無力阻止。她試過很多次,都阻止不了,完全無法改變。反正她最在乎的人已經死了。不要問她,這次輪到誰死?她不知道。她確定不是自己。幹。怎麼還沒輪到自己。等一下。自己突然的預感,都是關於自己人。誰要死了?確定不是她自己,應該不是。那是二號嗎?還是三號?
每天都有人死。上個禮拜,村長千拜託萬拜託,請她打開門口地上的小燈,他想帶母親來給她看。那晚奉神正廳夭壽熱,神桌上十幾尊木刻神像都在爆汗,對她喊:「拜託開冷氣!」但她根本聽不到。她身體根本沒有任何震動,只好跟村長說:「今日紅包要大一點喔,是你要我開門的,我今天本來沒營業,熱死了,那我要開冷氣了喔,幹,熱死,我沒辦法。喂,聽到了沒?電費很貴的,我平常怎麼可能開冷氣?」村長用力點頭,她把冷氣開到最強,關門關窗關大燈,只開神桌上一小盞低瓦數檯燈。冷氣呼出寒氣,神桌上的神像一臉舒暢,覆蓋神桌的桌布上繡有三隻鳳凰,差點熱到脫落一身羽毛,幸好開了冷氣,鳳身抖擻。村長母親坐在輪椅上打了好幾聲噴嚏。她坐在神桌前,任冷氣吸乾腹部上的大肚溪。村長母親打到第十六聲噴嚏,終於,她說可以了,來了。村長知道程序,開門,好多花,好多葉子,滿月銀光,手刷過各式各樣的植物,不能隨便,認真聞,用心挑,繞了好幾圈,最後摘了小巧綠葉,不要問村長這是什麼植物,他怎麼可能知道,全部都是沒看過的外來種,他只是感覺到那片葉子對他招手。回到神明廳,掌心攤開,給一號看葉。一號收過葉子,置放手心揉搓,直至葉子出汁,舌尖嘗葉,低頭觀翠綠掌紋,短而急促的呼吸,鼻毛伸長如章魚觸鬚,嗯,味如胡椒輕辣,初嘗微苦,隨即口舌蜜汁,疾速閉眼張眼,村長母親狂打噴嚏,葉子噴飛,面前的世界一皺,她收到死亡的訊息。她直接對村長大聲說:「沒剩幾天。」村長母親聽力不好,只是面前這個一號女人音量真是太大了,聽聞這句,皺臉嚴冬,眉毛瞬間掉光,雙瞳凹陷。她兒子忍不住發出欣喜笑聲,隨即壓抑臉部肌肉,掏出紅包,多塞幾張大鈔,哼歌推輪椅離去。三天後,村長家開始治喪,村長哭聲已經排練三天了,響亮且悲愴,孝子交響曲逼鄰里同悲。一號真是神準。
來到三合院問事的人必須摘葉或花瓣。她自己突來的預感,則不需植物,喜或悲,好或壞,生或死,說來就來,都是跟這三合院有關的人。
其實真的是所謂的預感嗎?若是有人問她,她會坦承,不見得吧。如果村長帶著母親去醫院,醫生檢查一下,也會說沒剩幾天。但真的很多人信她。三合院門口地上那盞小燈打開,表示開門營業,一定會有人上門。嬰孩收驚,開業命名,麵店求客,高中生學校成績不佳,芭樂求豐收,政客問票,夫妻求子,單身求愛,褲襠萎靡求堅硬。來者皆知她的個性,她不說安慰假話,心裡有什麼說什麼,好的壞的都說出口,不怕得罪人。要是她毫無感應,就不收紅包,送客,日後有緣再說。父母抱著學步小孩上門,喊發高燒,她直接逐客:「拜託,什麼時代了,臺灣健保很便宜,發燒就去看醫生,不要來我這種怪力亂神。去,不要一直站在那邊,快去。怎樣?要我打電話去診所幫忙掛號嗎?還是要我報警?說你們虐待嬰兒?」對方不走,堅持入神明廳,還亂摘葉子花瓣,踢倒花盆,她無法忍受花園被外人弄亂,直接吼:「幹你娘,我看起來像是會讀書的人嗎?醫學院我八輩子都考不上啦!我高中都沒有畢業,幹你娘啦!幹!幹!幹!社頭有幾百間廟,自己隨便去找,不要來找我!幹!」她的音量喚醒發燒孩,他掙脫母親懷抱,在三合院跑了一圈,對著父母說出了生命中第一個字:「幹。」那對父母聽聞這清脆嘹亮的「幹」,覺得是神蹟,跪下對她膜拜。
幹。這次換誰死。
反正她救不了。她誰都救不了。很多人都說她這個痟查某有神力。神力個屁。她什麼都阻止不了。有神力的話,怎麼會如今一個痟查某獨自住這個爛三合院,沒有家人,沒有朋友。
她從衣櫃翻出外套,昨晚想脫光光睡覺,今早就要穿外套了。她徐步到屋外澆花草,摘枯葉,霧氣裊裊,幾株熱帶植物微顫。啊,怎麼忽然就秋天了。屁啦,島嶼中部,秋什麼天,秋個屁,就是熱大半年,接著稍微不熱幾個月,根本沒有明顯的秋天,樹葉不集體轉黃,山區沒有滿山楓紅。但,就是有這樣的時刻,夏天不告而別,風的成分變了,忽然轉涼,冷氣終於可以放假,長袖長褲薄外套,可洗熱水澡,開始留長髮,想到遠方的人。體感溫度還能以文字數字確切度量,難以言喻的,是心裡細微的變化。炎夏溼熱,日夜汗水淋漓,情緒焦躁。「躁」是很強烈的情緒,占據許多空間,排除其他感知,脾氣森林大火,口噴熱帶氣旋。夏天離開,天地忽然降溫,身體除躁,立即騰出許多空間,許多細微的情緒就冒出來。忽然特別思念,想鑽到神桌下,但自己鑽根本沒用。昨天還上街吃一大碗剉冰,今天想喝一碗熱茶,想吃一碗蒜頭麵,想織一件毛衣卻不知道要織給誰,想燉水梨,想去休耕田裡挖泥塊堆土窯烤蕃薯。最想最想最想喝一碗杏仁湯。不是任何人煮的杏仁湯,特別不是街上賣的那種,難喝死了,人工香料味道好噁心。她想喝母親的杏仁湯。但她煮不出那個味道。母親沒機會跟她說配方,就死了。她預知母親的死。但她當年不敢說出口。說出口又怎樣。她很小就知道了,她根本沒有辦法阻撓死亡。小時候對死這個概念還很模糊,只會哭,跟著兩個妹妹哭,大家都在哭,只好跟著哭。一直到有天風涼,她好想喝一碗母親的杏仁湯,發現這輩子根本沒機會喝到了,那刻反而無淚,似乎終於知曉了死亡的強大。她試圖以其他湯水填滿身體,可樂沙士芭樂汁,身體裡裝越多飲料,對杏仁湯的渴望就越強烈。她不知道母親的杏仁湯配料,但清晰記得母親蹲在地上剝杏仁皮的模樣。天氣一轉涼,母親就會去市場買一大包杏仁,回來以清水洗杏仁,加水置入冰箱,隔夜才取出,加入滾燙熱水,指腹與指甲揉搓,杏仁皮就快速脫落,褐色的杏仁蛻變成白亮的果仁,像發亮寶石。接下來的步驟,她完全無記憶。
喝不到最想喝的那一碗杏仁湯,那種永恆的失落。對她來說,這就是入秋。
涼風在她頸背溜滑梯,在她耳邊喧鬧:「怎麼頭髮剪這麼短?像個男人。」夏天終於去死了,她想到接下來不用每個禮拜都去剪頭髮,可以省很多錢,心情還算不錯,任涼風鬧。她從來不懂二號,那一頭蓬鬆大捲的及腰長髮,在她眼中是個恐怖的捕鼠籠,高溫就是一大群肥大的老鼠,衝進那團長髮,永遠困在裡面。她一直很想拿一把大剪刀,衝過街,反正就幾步路,抓住那團長髮,一刀喀嚓,一定可以抖落千百隻噁心的鼠屍。算了,想想而已,都多久不說話了。看到就煩。
真的入秋了,那些貓狗,會不會著涼?
一一確認花草皆喝飽水,枯葉掃盡,快速鬆土除雜草,沒手錶,不知道幾點了。其實根本不需要手錶,聽到遠方狗吠,就是早上05:25,二水開往基隆的區間車在社頭停靠。火車惹狗吠,好啦好啦,我澆花打掃一下,就去準備飼料,不要叫了啦,已經很多人討厭你們了,再叫就會被撲殺了。
她什麼時候開始餵流浪貓狗的?想不起來了。她小時,社頭流浪貓狗比現在多很多,上學途中常會遇到一大群野狗,皮膚潰爛,看到騎單車的小孩就狂吠狂追。野狗感知強烈,捕狗大隊的卡車還沒開進社頭,牠們就已經失控,往山區狂奔。野狗似乎也聽到了鄉里謠言,在田野遇見她們三姊妹,安靜穩坐,眼神不敢直視,傻一點的狗會搖尾巴,壯碩凶猛的狗則定格假裝是廟裡的石獅,絕對不追她們,太可怕了,大家都說,惹到她們不得好死。有一次三姊妹在田間遇到野狗打群架,都已經咬到見骨濺血了,見到三姊妹,野狗尖牙塞到狗嘴最深處,夾尾巴,喉嚨收束,讓出一條路。
是那一次,她發現自己的眼睛,除了能取得預感,還有抹除的能力。她不會解釋預感,當然也不會解釋抹除。其中有一隻毛髮糾結的大狗在她腳邊搖尾巴,她蹲下摸牠,從書包拿出餅乾餵食,狗在她身上開心扭動身體。二號跟三號尖叫,說好噁心,好臭。
「不要亂講,噁心什麼?很可愛啊。」
「妳近視喔?狗在流血,妳衣服還有褲子都沾到了啦。牠身上有乾掉的大便,很臭!我幾百公里外就聞到了。」
「妳神經病喔!不要再摸了啦,很多人在看,誰知道他們會跑去跟阿公說什麼。」
她低頭看狗,沒有啊,沒有看到大便,根本沒有血,她們亂說話。她只知道,她的視線裡有幾大塊白糊的區域。她猜大概是近視吧。
後來她看到阿公在房間看日本色情片,畫面上的男體女體,讓她看傻了眼。那些男女器官,都被遮蔽了,像是有誰拿了噴漆,在他們身上噴上了霧。她看傻了,沒注意到阿公憤怒的表情。阿公沒拉上褲子,直接一腳踹過來,她來不及躲,身體飛出去。阿公啊阿公,我不是想跟你一起看色情片,而是,我的眼睛,跟你看的片子一樣,也會自己噴霧喔,這裡噴那裡噴。
必須要經過很多年,她才慢慢理解自己視覺抹除的能力。不想看到的,不該看到的,她視覺會自己在眼前畫面上噴霧。她不太能夠以意志控制,視覺會自己抹除,不想看的,不該看的,這裡噴一下,那裡噴一下。但是,真奇怪,灰塵髒汙,視覺就是不會抹除,反而會放大。潔癖個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