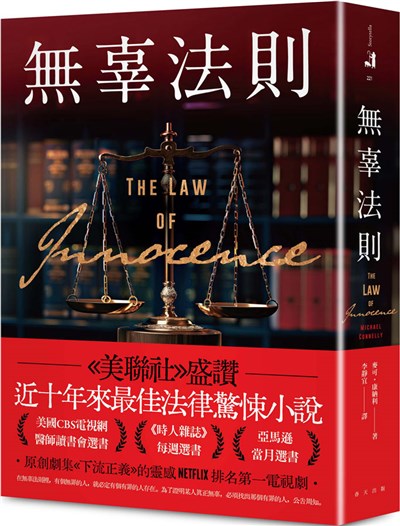
在無辜法則裡,有個無罪的人,就必定有個有罪的人存在。為了證明某人真正無辜,必須找出那個有罪的人,公告周知。
在慶祝贏得重大勝利的這晚,辯護律師米奇‧哈勒被警方攔車盤詰,結果在他的林肯轎車後車廂找到一具屍體,被害人是他以前的當事人。哈勒馬上被控謀殺罪起訴,而報復心切的法官裁定保釋金為五百萬美金,他無力負擔。
哈勒選擇為自己辯護,被迫在洛杉磯市中心的雙塔矯治機構牢房裡準備自己的辯護論據,同時還要不時留意周遭,因為身為法院體系一員的他是個明顯的目標,而在他揭發監獄內的腐化惡行之後,更難有朋友。
但更為重大的陰謀是針對他而來的這個命案。哈勒知道自己是被陷害的,不管幕後黑手是他的新敵人或舊仇人。他與信任的團隊成員展開調查,而哈勒也必須在法庭上使出渾身解數,對抗不利於他的證據……
內容節錄
《無辜法則》
第一部 雙塔
1
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對辯方來說,今天原本是個好日子。我讓一名男子無罪釋放。他被控蓄意傷害,但我讓陪審團判定他是正當防衛。那名所謂的「被害人」本身就有暴力前科,這一點是檢方與辯方證人(包括他的前妻)在交互詰問中都拚命想釐清的。但我的致命一擊是再次傳喚他坐上證人席,透過連串的詢問,一步步逼他瀕臨失控。他失去冷靜,出言威脅,說他很樂意和我在街頭相遇,就只有我和他,一對一。
「到時候你是不是也會說是我攻擊你,就像你堅持是本案被告攻擊你一樣?」我問。
檢方提出異議,法官同意,但效果已經達成了。法官知道,檢方知道,法庭裡的每個人都知道。不到半個鐘頭之後,陪審團審議結果:「無罪」。這並未創下我最快的判決紀錄,但也很接近了。
在市區非正式的辯方律師酒吧裡,有個慶祝無罪判決的儀式,類似高爾夫球手在高爾夫球俱樂部慶祝一桿進洞那樣。也就是,請在場的每一個人喝酒。我的慶功會是在第二街的紅木酒館舉行。這裡距市政中心只有幾條街,足以吸引至少三個法院過來的賀客。紅木酒館不是鄉村俱樂部,但很方便。慶功會—意即免費酒吧—開始得很早,結束得很晚。渾身刺青的酒保莫伊拉仔細記帳,然後把所有的損害全交給我。這樣說吧,剛剛因為我而恢復自由身的那位當事人,付給我的錢肯定比不上我刷卡的金額。
我的車停在百老匯街的停車場。我坐進駕駛座,左轉駛出停車場,再一個左轉,回到第二街上。一路綠燈,所以我沿著第二街暢行無阻開進邦克山下的隧道。通過隧道差不多快一半時,我才在隧道壁面被汽車廢氣燻得發黑的綠色磁磚上看見藍色燈光倒影。從後照鏡裡,我看見一輛洛杉磯警局的巡邏車跟在我後面。我打燈號,靠向慢車道,想讓警車先過。但警車跟著我變換車道,緊隨我車後,相隔約六呎。這時我才明白,警車是要我停車。
我等到出了隧道,右轉到菲格羅亞街時才停車,熄火,降下車窗。從林肯轎車車窗外的後照鏡裡,我看見一名制服警員朝我的車門走來。他的巡邏車上沒有別人。走近我的這名警員是獨自出勤。
「請出示駕照、行照和保險證明。」他說。
我看著他。他名牌上寫著「彌爾頓」。
「當然沒問題,彌爾頓警員。」我說,「但可以請教一下,你為什麼要攔下我?我知道我沒超速,而且這一路上都是綠燈。」
「駕照,」他說,「行照,保險。」
「好吧,我想你遲早會告訴我的。我的駕照在外套口袋,其他東西在置物箱,你希望我先拿哪一樣?」
「先拿駕照。」
「沒問題。」
我掏出皮夾,從其中一個隔層抽出駕照。衡量眼前的情況,我心想,彌爾頓會不會一直在紅木酒館監視參加慶功會的律師,以為我們會喝得醉醺醺,無法開車。據說有些警察會在無罪判決慶功會舉行的晚上這麼做,如此一來,就可以用各種交通違規來找辯護律師麻煩。
我把駕照交給彌爾頓,接著打開置物箱,很快就把這位警員要求的資料全交到他手上了。
「現在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我問,「我知道我沒—」
「請下車,先生。」彌爾頓說。
「欸,老兄,你當真?」
「請下車。」
「隨便啦。」
我用力推開車門,迫使彌爾頓後退一步讓開,才下車。
「順便告訴你一聲,」我說,「我在紅木酒館待了四個鐘頭,但一滴酒都沒喝。我已經五年沒喝酒了。」
「很好。請走到你的車子後面。」
「請記得打開你的攝影機,因為這可能會有點尷尬。」
我穿過他身邊,走到林肯轎車後面。停在我車後的巡邏警車車頭燈照亮我。
「你是要我走直線嗎?」我說,「倒數數字,用手指摸鼻子,還是什麼?我是律師,我知道你們的把戲,這簡直是活見鬼。」
彌爾頓跟著我走到車後。他是白人,高高瘦瘦,頭髮理得很短。我看見他肩上有大都會司的肩章,長袖制服衣袖上還有四個V形標章,我知道任職每滿五年可以得一個,所以算來他已經快要從警局退休了。
「你知道我為什麼攔下你,先生?」他說,「你的車子沒有車牌。」
我低頭看我這輛林肯的後保險桿。沒有車牌。
「該死,」我說,「呃……這只是個惡作劇。我們在慶祝—我今天剛打贏一場官司,我的當事人無罪釋放。我的車牌是『我打贏』,一定是有人覺得偷走我的車牌很好玩。」
我拚命回想,有誰比我早離開紅木酒館,又有誰會覺得這樣做很有趣。達利,米爾斯,伯納多……誰都有可能。
「檢查你的後車廂,」彌爾頓說,「也許車牌在裡面。」
「不,得要有車鑰匙才能把車牌放進後車廂裡。」我說,「我要打個電話,看是誰—」
「先生,我們得先搞定眼前的事,你才能打電話。」
「鬼扯,我懂法律。我又沒被羈押—我可以打電話。」
我杵在那裡,等著看彌爾頓會不會進一步挑釁。我注意到他胸前的攝影機。
「我的電話在車裡。」我說。
我開始往敞開的車門走。
「先生,請停住別動。」彌爾頓在我背後說。
我轉身。
「什麼?」
他抓著手電筒,光線射向車後的地上。
「那是血嗎?」他問。
我往後退,也低頭看龜裂的柏油路面。警員的手電筒光線對準我車子保險桿下方的一小團液體,中央是暗紅色,邊緣近乎透明。
「我不知道。」我說,「但不管是不是,應該都早就在這裡了。我—」
就在我這麼說的時候,我們兩個都看見又一滴液體淌下保險桿,滴在柏油路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