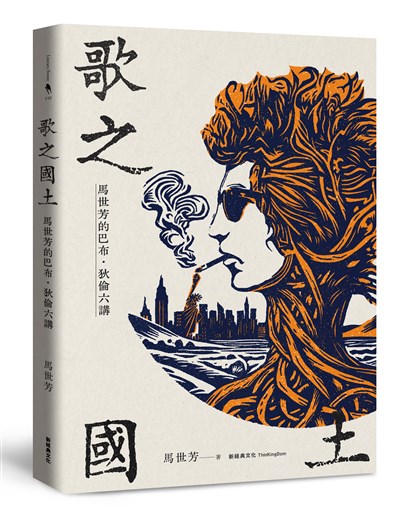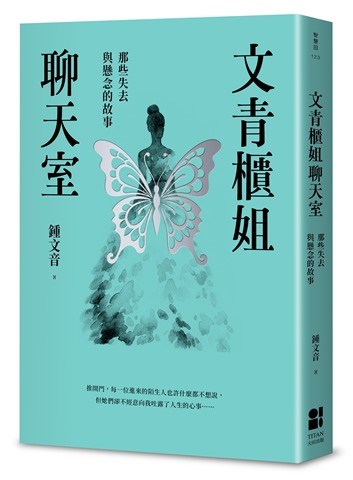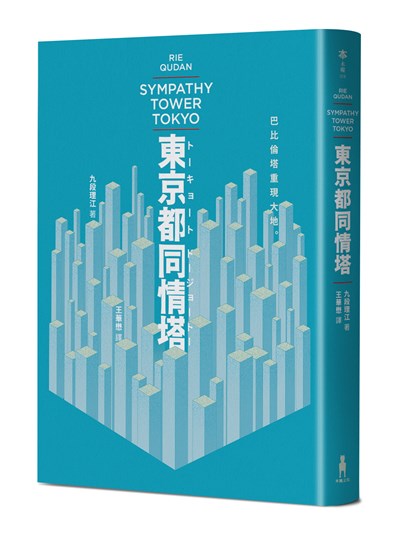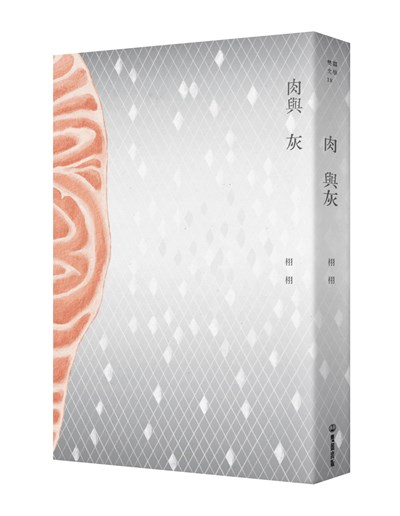
肉與灰是詩人栩栩的第一本散文集,在疫情大流行的三年間,在人與人的交流受阻絕的時刻,栩栩重新觀察自身,與自我對話。我們的身體往往在健康與疾病之間遊移,並且無能轉圜的以死亡為生理的終點。位居醫療第一線的作者,不僅成為社會抵禦病毒的前鋒,更細細觀察面對威脅時的情感反應。除此之外,栩栩以優雅的文字凝塑了細膩的身體感,從食衣住行各端體察。在生動的文字背後,藏著她處世的智慧以及宛若頓針,刺激卻不傷人的幽默。
內容節錄
《肉與灰》
陽春白雪
嘴饞,又或自我感覺餓,內心就忍不住開始琢磨著吃些什麼好,正經吃一碗米麵太多,炸物太膩,餅食無茶湯相佐未免少了一趣,思來想去,還是吃豆花吧。
豆花可開場,可為插曲,亦可作為一餐之收尾,可簡可繁,即知即行,隨便哪個街坊都有,不用特意去尋,最適合臨時起意。說起來不是沒有一點弔詭,豆花之狀,瑩白如酪,味淡近於寡,這樣清冷潔淨的小食,俗世裡竟然唾手可得。
也許使豆花真正變為可即的,不是一地豆花攤的密度高低,而是配料。本來,倘若豆花細嫩帶豆香,糖水蔗香味足,有沒有配料,無關宏旨,然而能以簡樸本真取勝的豆花,為數畢竟不多;常見的其實是另一種:玻璃方櫃裡各色配料琳琅排開,該繽紛的繽紛,該剔透的剔透,豆花靜靜躺在碗底,觀其形,嘗其味,平淡無奇。
即便如此,上豆花攤光顧,仍然是樂事一樁。這裡清涼,空氣裡沒有油煙,不沾葷腥,一應熱惱盡皆退出數丈之外;但這裡又實在熱鬧,店主從深桶中平平鏟出幾鏟豆花,刀刃旋轉著飛濺出冰屑,接著,就開始挑選配料了。
盛裝豆花的碗不必深,碗面卻要寬綽些,諸般果豆排列堆疊,輝映滲潤,宛若團花綻開。
首先需要一點彈牙的東西。湯圓是我的心頭好,紅白雙色,有一種老派節慶感。粉角粉稞。芋圓地瓜圓,基本上我個人的接受度只到這裡,抹茶圓咖啡圓紅麴圓什麼的,美則美矣,真放入豆花碗內,太鬧。至於珍珠粉圓,還是留給奶茶比較般配。這一類配料多由木薯粉製成,煙韌軟糯,能增加飽足感。
需要一點顆粒感。豆類大概就是為了這件事而存在的,玉粒金波,紅豆綠豆薏仁雪蓮。我鍾愛花生或麥角,要一抿即化,唇齒閉攏前顆粒完足,一碰,立即化開敷在舌尖,分明又綢繆。顆粒存在感強弱全憑個人喜好,沒有絕對。假若豆花攤稍具規模,可能也提供紫米,有的話,那就挑紫米。
需要一點滑溜的東西。豆花本已是滑溜之物,再添一點滑溜的東西,乍聞之,似乎不通;然則物與物摩擦力各不相同,這一類滑溜的東西最好略具彈性或韌性,與唇齒交纏,產生阻力,卻不致兵敗如山倒。摻入豆花裡,一腔柔滑中立即顯出變化,此乃正襯之法。我一般挑杏仁豆腐或桂花蒟篛,炎夏改仙草。愛玉太清雅,怕折墮了。
最後,假若店家能熬芋頭至酥爛,我會加點一份芋頭。
當然這只是個通則,天熱懶怠咀嚼,那就是仙草配杏仁豆腐,美其名曰黑白雙仙;又或者仙草珍珠蜜紅豆,烏壓壓湊成一碗,便是烏雲蓋雪。豆花的好好在它非常自由,不必依循典範,隨便這邊一指那邊一指立刻就能組合出一碗風景來,各吃各的,誰也不遷就誰。
但對我來說,必需再加一瓢碎冰屑。冰屑本身無味,可是卻能夠恰如其分地成為奶與蜜的襯底,咬在嘴裡喀啦作響,捧在手中,半融半凍,像陽春裡的一捧白雪。
所謂餘裕,時常不過是這樣一捧白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