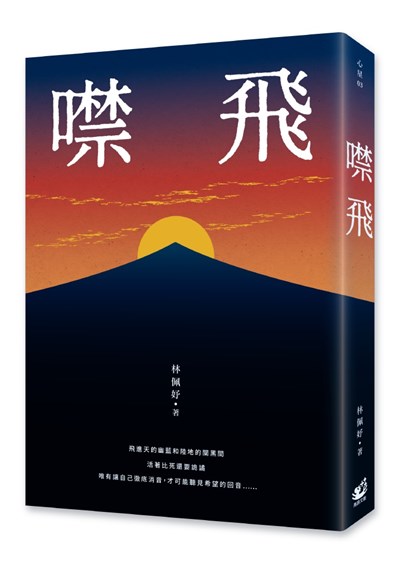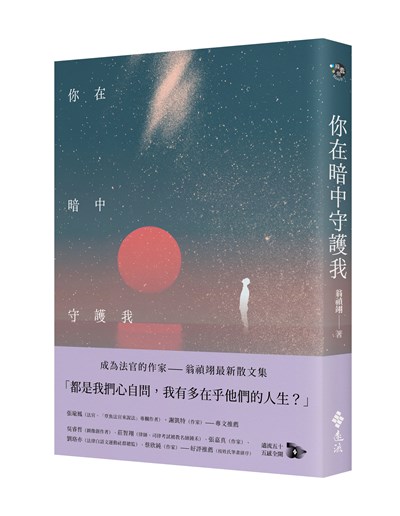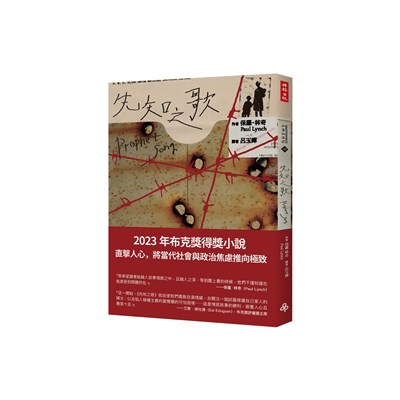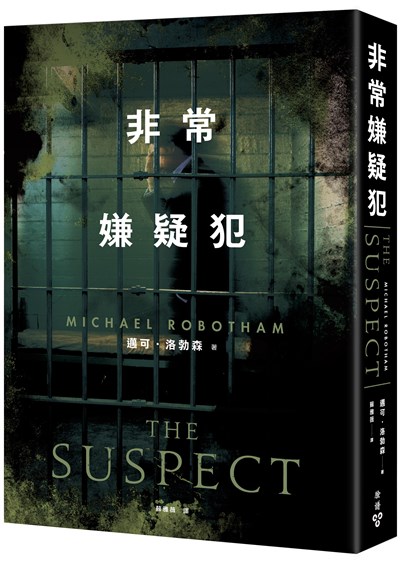
臨床心理學家歐盧林醫師擁有成功的事業、美滿的家庭,然而,當他認識的一名醫院護士慘遭殺害、他主動協助辦案,他擁有的一切全都面臨危機,因為他陰錯陽差成了頭號嫌疑犯──與死者共事期間的糾紛讓他被警方盯上,他指出自己的病患描述的施暴情境與案情相似時,警探卻更加認定他企圖轉移焦點。他只好自力追查凶殺案的真相,竟查出一樁塵封的家暴案件,所牽涉的人員紛紛痛失至親或意外身亡,故事開頭慘死的護士僅僅是其中之一……。
內容節錄
《非常嫌疑犯》
氯仿為無色液體,密度是水的一點五倍,氣味類似乙醚,嘗起來比蔗糖甜四十倍。氯仿是重要的有機溶劑,主要用於工業。
蘇格蘭愛丁堡的醫生詹姆.辛普森爵士首先在一八四七年把氯仿當作麻醉劑使用。六年後,英國醫生約翰.史諾也在維多利亞女王產下第八個孩子利奧波德王子時使用氯仿。
在口罩或布料滴上幾滴,通常幾分鐘內就能產生手術用麻醉劑的效果。病人會在十到十五分鐘後醒來,頭腦昏沉,但鮮少有反胃或嘔吐的症狀。約三千分之一的案例使用氯仿極為危險,會造成心臟麻痺致死……
我闔上百科全書,放回書架,草草記下筆記。為什麼巴比.莫蘭的衣服上有氯仿?他拿工業用溶劑或麻醉劑要做什麼?我隱約記得咳嗽藥和止癢乳膏偶爾也會用到氯仿,但量不足以產生獨特的氣味。
巴比說過他是送貨員,或許他配送工業用溶劑。下一次看診我會問他,屆時希望漂泊外太空的太空人已經連絡地表控制台了。
我走進廚房,倒了咖啡,跟查莉一起坐在早餐吧檯。她用麥片盒撐起圖書館的書,我的早報放在柳橙汁旁邊。
查莉在玩遊戲──模仿我做的每件事。我咬一口吐司,她也照做。我喝咖啡,她就喝她的茶。甚至當我歪頭想讀消失在報紙摺起處的新聞,她也跟著歪頭。
「你用完橘子醬了嗎?」她在我眼前揮揮手。
「對,抱歉。」
「你跟小精靈去神遊啦?」
「他們跟妳問好。」
茱麗安從洗衣間出來,撥掉額頭上一縷散落的髮絲。烘衣機在後頭隆隆運轉。我們以前會一起吃早餐―喝濾壓壺煮的咖啡,互換早報的不同版面。現在她停下來的時間不夠長了。
她把碗盤放進洗碗機,將我的藥放在我面前。
「醫院出了什麼事?」
「我有一個病人跌倒了,他沒事。」
她皺起眉頭。「你說過會少接緊急案件的。」
「我知道,就這一次而已。」
她咬了四分之一片的吐司,開始裝查莉的午餐。我聞到她的香水,注意到她穿了新牛仔褲和最好的外套。
「妳要去哪裡?」
「我有那堂『了解伊斯蘭』的研討會。你答應四點會到家照顧查莉。」
「不行,我要看診。」
她不太高興。「有人得在家。」
「我五點可以到家。」
「好吧,我看能不能找到保母。」
我從辦公室打電話給盧伊茲警探。背景可以聽到工業設備和流水聲,他在河川或小溪旁邊。
我報上姓名,就聽到明顯的電子喀喀聲。我猜想他是否錄下我們的對話。
「我想問你凱薩琳.麥布萊的事。」
「嗯?」
「她身上有幾個傷口?」
「二十一個。」
「病理學家有找到氯仿的痕跡嗎?」
「你讀過報告了。」
「裡面沒提到。」
「你為什麼問?」
「可能不重要啦。」
他嘆了一口氣。「我們談個條件吧。你別再打給我問這種鳥問題,我就撤銷你那張沒繳的停車罰單。」
我還來不及說對不起打擾他,就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悶哼一聲「真謝謝你啊」就掛了電話。這傢伙的溝通技巧跟葬儀社員工差不多。
芬威醫師在我的候診室鬼祟遊蕩,瞥看他的勞力士金錶。我們要去梅費爾區他最喜歡的餐廳吃午餐,週日的報紙增刊往往會介紹這類餐廳,因為主廚喜怒無常,長相英俊,還跟超模約會。據芬威所說,名人經常在這家餐廳聚會,但我去的時候他們都沒出現。
今天芬威特別努力裝得和藹可親。走去餐廳路上,他問起茱麗安和查莉。接著他唸出整本菜單,評論每一道菜,彷彿我不識字。當我點了礦泉水沒有點酒,他看來有些失望。我解釋,「我發誓中午不喝酒了。」
「這麼不合群。」
「我們有些人下午要工作。」
侍者過來,芬威明確指示他的餐點該如何料理,甚至建議烤箱溫度,還有肉是否該先敲嫩。如果侍者有點頭腦,就會確保這些指示絕不會送進廚房。
我問,「沒有人告訴你不要惹火替你準備食物的人嗎?」
芬威一臉困惑看著我。
「當我沒說。」我說,「你顯然大學沒打過工。」
「老兄,我有零用錢啊。」
我就知道!
芬威四處張望,尋找熟面孔。我總是不太確定跟他吃午餐是要做什麼,通常他會試圖說服我投資房地產或新創生技公司。他對錢毫無概念,更不知道大多數人賺的錢多少,房貸又多重。
平常我非不得已不會請芬威給我建議,但他人就在這兒,我們聊天又沒梗了。
「我問你一個假設問題。」我折起餐巾又攤開。「假如你懷疑病人可能犯下嚴重罪行,你會怎麼做?」
芬威看來嚇了一跳。他回頭張望,似乎擔心有人會偷聽。他悄聲說,「你有證據嗎?」
「不算有……應該說是直覺吧。」
「多嚴重的罪行?」
「我不知道,可能是最嚴重的那種。」
芬威往前傾,一手蓋住嘴巴。沒人比他更顯眼了。「老兄,你一定要報警。」
「可是醫病保密協議呢?我的工作仰賴保密,如果病人不信任我,我就幫不了他們。」
「不適用,別忘了塔拉索夫案的先例。」
塔拉索夫案是六零年代末期一名大學生在加州謀殺他的前女友。他事前曾在就診時告訴心理師他打算殺了她。受害女孩的父母控告心理師失職,最終勝訴。
芬威還在說,鼻子緊張地抽動。「如果客戶表示他可能有意嚴重傷害第三者,你有義務提供相關的保密資訊。」
「沒錯,可是假如他沒有威脅特定人士呢?」
「我覺得沒差。」
「當然有差。我們有義務保護目標受害者不受傷害,但前提是病患擺明威脅要行使暴力,並真的指出對象。」
「你在雞蛋裡挑骨頭。」
「我沒有。」
「所以我們就讓凶手逍遙法外?」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凶手。」
「你不是應該讓警方決定嗎?」
也許芬威說得對,但要是我妄下的結論錯了呢?保密是臨床心理學不可或缺的一環。如果我沒有巴比的許可就透露看診內容,我可就是違反了十幾條法規,可能遭到協會懲處,或吃上官司。
我有多肯定巴比很危險?他攻擊了計程車上的女子。除此之外,我只聽過他精神錯亂地提到夢中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