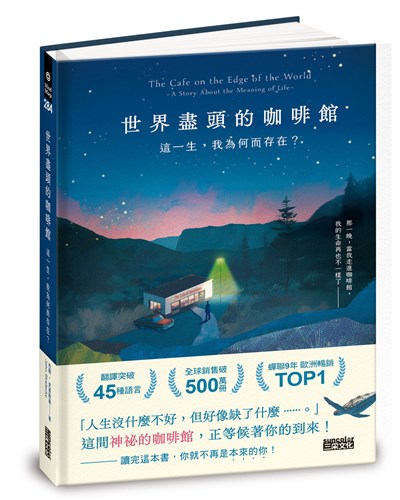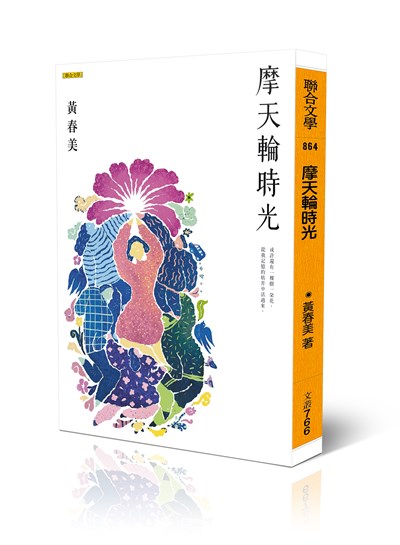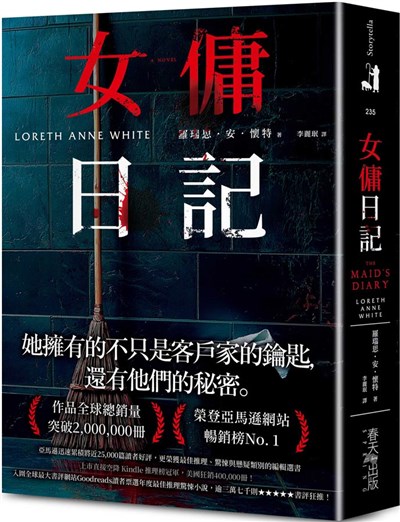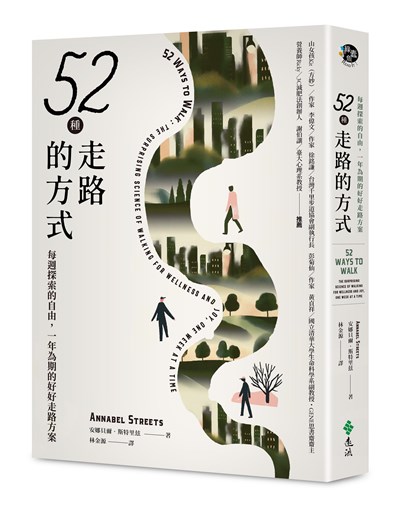龍仔尾,一個位於縱谷海岸山脈下的小小村落,地圖上不容易找到的地名,生活著世代勤懇勞動的人民。
一場大疫,讓蔣勳意外在龍仔尾的一座農舍待下,天地彷彿是牢房。在這裡,他的肉身被隔離,心靈卻彷彿在桃花源裡。龍在眼前,雲煙飛瀑,活靈活現,還有幾隻貓咪流連忘返。他在這裡無所事事,看雲來雲去,看世事原無是非,確有因果的人生……。
文章節錄
《龍仔尾‧貓》
大疫 ◎蔣勳(作家、畫家、詩人)
大疫流行,我住在縱谷,縱谷進入台東縣的北端,住在池上靠東的邊緣,沿著海岸山脈到了尾端,屬於萬安。
萬安大多是客家移民,世代務農,我住的龍仔尾在萬安的南端,小小的聚落,幾戶人家而已,稻田、菜圃,很安靜的狗吠,知道有人迷了路,誤闖進村子。
村口的福德祠旁有大樹,樹下涼亭,總坐著村裏閒聊無事的老人家。
他們閒聊,也看山,隔著大片的稻田,遠遠望著中央山脈聳峻的大山,是南橫入口的舞樂群峰,落日時分有非常驚人的霞彩變幻。老人家們看慣了,不覺得稀奇,多回家吃飯了。我便坐在祠堂樹下看我覺得每天都稀奇變化莫測的晚霞餘光。
那是三級警戒的時刻,規定隨時必須戴著口罩。要保持社交距離,到超市買東西排隊,都有人與人之間一公尺半的距離。
原來,不只山脈是隔離,海洋是隔離,河流是隔離,沙漠是隔離。
原來,傳染病也是一種隔離。
歐洲中世紀,黑死病蔓延,一個村落,發現有病例,被列為疫區,鄰村的人即刻封鎖,甚至放火焚燒,毀滅這個村落。
莎士比亞的名劇《羅密歐與茱麗葉》,傳信的神父,因為被診斷出黑死病,就一起被鄰人釘門釘窗,即刻封鎖在屋內,不得外出。
沒有想到,遇到了疫區隔離的歷史。
原來的疫區是武漢,在杭州的人覺得無關。疫區在全中國蔓延,台灣也覺得無關。我去了倫敦,倫敦的人覺得亞洲是疫區,與歐洲無關。
二○二○年二月,我還去了南非,南非的人更覺得疫區遙遠,不干他們的事。三月疫情在義大利爆發,倫敦城裡許多義大利遊客,但是,倫敦人還是覺得義大利很遙遠,不干他們的事。三月九日,我警覺到疫情不只是義大利、西班牙,落荒而逃,歐洲的朋友大多覺得我大驚小怪。
一個星期後,我在台北隔離,倫敦已經封城。
新冠疫情,是人類史上一次巨大的病疫,三年過去,沒有人知道下一步會如何發展。我們不知道如何隔離,如何防範。全世界都是疫區,隔離?要到哪裡隔離。
疫區是一個界限的概念,國家也是,縣市鄉鎮,都有界限。
從池上往北,車程二十分鐘到富里,富里是花蓮縣,所以,池上、富里之間有縣界。
界線給我們一個誤解,以為可以隔離,然而,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的時候,忽然發現,人類在地球表面上劃分的界線,似乎沒有了意義。
一次全球不能倖免的疫情,讓每個隔離的地區更努力防衛,希望能阻絕疫情,希望隔離在疫區之外。
那一條隔離的線,可以阻擋什麼?
地球上最偉大的阻擋的界線,大概是長城吧……在數千年間,為了防範戰爭修建起來的一條長長的城牆。
卡夫卡寫過《長城》,一條虛無而又荒謬的巨大的牆。
牆,究竟阻擋了什麼?
二○二一的五月到八月,島嶼宣布三級警戒時,我「隔離」在龍仔尾。
感謝這個十幾戶人家的聚落,讓我覺得「隔離」也可以這麼美好。每天夜間散步,可以戴口罩,也可以不戴口罩,因為不太有遇到人的機會。
七月初,一期稻作收割,會聽到遠遠稻田裡曳引機的聲音,許多白鷺鷥跟在曳引機前後,爭搶啄食被機械驚嚇逃出的昆蟲。
我走在龍仔尾,沒有感覺到疫情。我在想,世界有很多地方,高山之巔,樹林環抱的谿谷,小小的島嶼,是不是也有很多像龍仔尾這樣安靜的聚落,沒有特別感覺到隔離的痛苦?
我被大片稻田隔離,被長長的縱谷的風隔離,被晨昏的旭日與夕照隔離,被卑南溪入海的遠遠餘光隔離,被七夕晚上滿天繁星的銀河隔離,被午後洶湧的雲瀑隔離……在這樣浩大廣闊的天地間隔離,為認識和不認識的眾生的逝去誦經。
或許,前世與今生的隔離,讓我聽不到上一次繁華盛放時嘩嘩的蟬鳴……
或許,我靜下來,還聽得到來世沒有驚恐怖畏的微笑。
時間是不是一種隔離?
三生石上,還記得那告別傷痛,淚水落在親人手上漫漶成的一片胎記嗎?
所以,牆阻擋了什麼?
一道一道的橋,貫穿河流的阻隔;一艘一艘的船艦,通過海洋,連結區隔的領域;一架一架飛機,在世界各地飛翔,讓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區域彼此來往。
我們以為世界的隔離愈來愈小,認識、諒解、包容,因為來往愈來愈多,可以取代陌生、疏遠、懷疑、敵對。
然而,我們是不是太早下了結論?
在疫情來臨的時候,我也如此自保,從自己認為的「疫區」逃離。但如果全世界都是疫區了,我要逃到哪裡去?
我在龍仔尾的時候,心想:我可以把全世界驚慌的人都帶到龍仔尾嗎?
社交距離,讓我想到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他說的「息交絕遊」,其實是某一種意義上的「社交距離」吧。
我也想到他幻想出的「桃花源」世界,一個在現實如此不完美的戰亂中創造出的「烏托邦」。「烏托邦」本來是一個假託存在的「邦國」,柏拉圖在哲學裡創造了「Utopia」,陶淵明卻指證歷歷,說明「桃花源」真正存在,那條「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那條路通往一個被「隔離」的世界,不只是空間的「隔離」,也是時間的「隔離」。住在那裡的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所以是在秦代的大戰亂時代就選擇了與外面世界「隔離」嗎?
大疫期間,我在龍仔尾,覺得是自己的「桃花源」。
隔離,可以這麼美好。保持社交距離,這麼孤獨,完完全全跟自己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