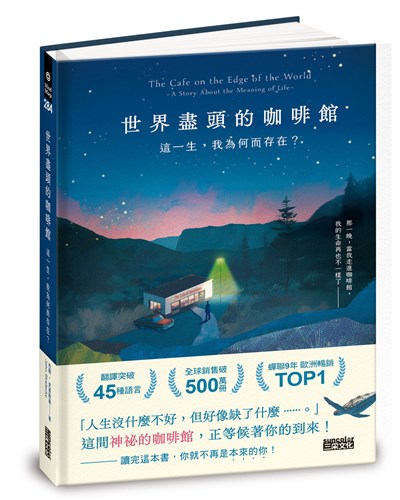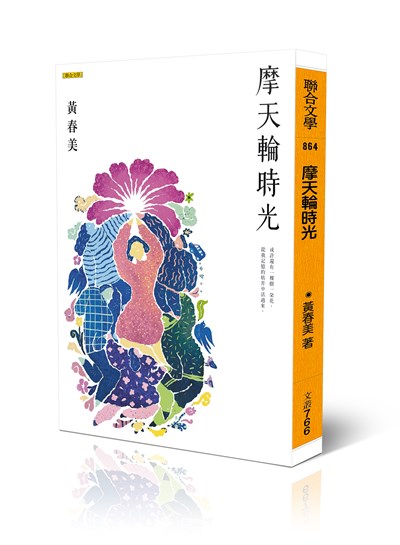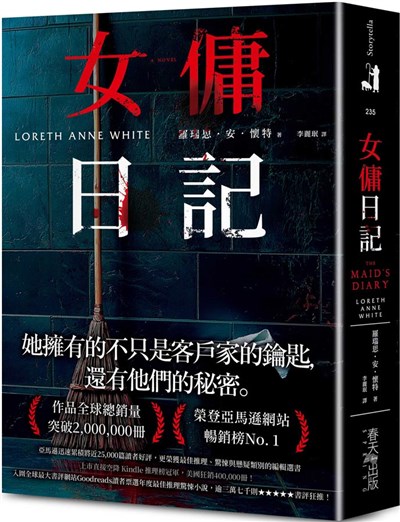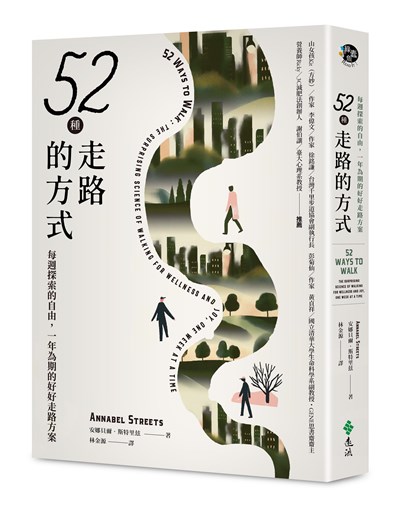「泰斯凱蘭二部曲」描述小國大使瑪熙特調查前任大使之死,卻遭遇帝國暗潮洶湧;在政治運籌之間,瑪熙特不甘淪為陰謀的犧牲者,但不斷出錯的憶象侵蝕著她的自我;而眾人都沒發現更大的陰影正壓境而來……
《名為帝國的記憶》及《名為和平的荒蕪》情節緊密連結,結合殖民與被殖民的文化衝突、身分認同的隱喻及主題,佐以宮廷鬥爭、異星接觸,描繪出一個具有爭議性但多面的女性自我追尋的永恆命題:我是誰?我屬於何方?又將往哪裡去?
文章節錄
《泰斯凱蘭二部曲》
前情提要:
萊賽爾太空站的外交大使.瑪熙特領命前往泰斯凱蘭帝國的首都。熱愛泰斯凱蘭文化的她,受到各方面的文化震懾,但同時發現自己的前輩—前任外交大使.伊斯坎德已死,甚至死了好一陣子,帝國卻沒有回報萊賽爾太空站。認為有內情的瑪熙特,偕同她在帝國當地的女性聯絡官.三海草,及三好草好友.十二杜鵑,偷偷摸摸地返回屍體所在的停屍間,找出這場謀殺真相的蛛絲馬跡;同時,她們也預計和認識過伊斯坎德的人會面—就算這些冒險,可能洩漏關於瑪熙特身上配戴的「憶象機器」祕密,她也還是義無反顧……
摘文:
這次,瑪熙特步行前往司法部大樓,三海草和十二杜鵑與她同行,在她身邊不斷變化隊形。她感覺自己像個人質,或像某個需要防範刺殺行動的政治人物,這兩者用來描述她的處境都太過精確,讓她樂觀不起來。而且,她這會兒可是走在闖入停屍間的半途上;或是在幫助某個合法擁有停屍間通行權的人,偷渡不具資格者進場,非此即彼。她在發揮政治手腕。
但願太空站議會曾針對如何施展政治手腕一事給她更妥善的指示。她接到的大部分指示,都是要她在查明伊斯坎德‧阿格凡出了什麼事之後善盡自己的職責,為太空站的居民代言,在必要的時候努力阻止泰斯凱蘭人侵略。她的印象是,議會中大概有半數成員,特別是負責處理外交和文化保存事務的傳承大臣亞克奈‧安拿巴,都希望她對泰斯凱蘭文化的喜愛恰足以讓她享受自己的任務;但也希望她對帝國文化懷有足夠的排斥,以免讓太空站民的藝術與文學遭遇更多的外來滲透。議會另一半的成員,以礦業大臣塔拉特和飛行員大臣昂楚為首(儘管亞克奈‧安拿巴對她寄予厚望,她仍認為這一群才是六人政要組織中的務實分子),則不斷主張要阻止帝國侵略,並力圖確保太空站繼續作為鉬、鎢、鋨礦產的首要供應者—當然還有作為安赫米瑪門周邊資訊與旅遊的門戶。「我的前輩遭人謀殺,我可能要私下調查以保護太空站的科技機密」,這種事算得上是「阻止泰斯凱蘭人侵略」嗎?伊斯坎德應該知道吧,或者他至少會說得出一番犀利的見解。
都城中帝國政府所在的這個區域面積廣大且歷史悠久,形狀如同六芒星:四個區塊分別指向東、西、南、北,此外還有北和東之間突出的「天」、南與西之間的「地」。每個區塊裡都有細長如針的高塔,設滿檔案庫與辦公室,以多層空橋和拱廊彼此相連。人員最多的塔樓之間,有一層層的空中庭院,地板有的透明,有的嵌入砂岩和黃金。每個庭院的中央各設一座水耕花園,浮在垂直流動的水中行光合作用;這是這個星球上令人難以置信的奢華景象。水耕花園裡的花朵顏色似乎精心排列過,離司法部大樓愈近,花瓣的色彩就愈紅,直到中間看起來就像一汪發光的鮮血。瑪熙特看到當天早上她首先抵達的建築物,簡直無法想像那只是幾個小時前的事。
十二杜鵑在門邊一片閃亮的綠色金屬板上用食指飛快畫出龍飛鳳舞的圖形,瑪熙特猜想那是草寫簽名—她瞥見中間有「花」的字符,他的名字拼寫出來會有「花」和「十二」的字符,還有其他代表花卉種類的修飾字。司法部的門嘶嘶作響地打開。三海草正抬手要碰觸面板,十二杜鵑抓住她的手腕。
「進來就是了,」他悄聲說,推著她倆進去,讓門在背後關上。「人家會以為妳從來沒有偷溜進……」
「我們有合法通行權,」三海草用氣音說。「何況,我們都在都城人工系統的影像紀錄中—」
「看來我們的東道主不希望他的通行紀錄跟我們有關。」瑪熙特用恰好讓他們聽得見的音量指出。
「正是如此,」十二杜鵑說。「而且,如果鬧到有人要去翻遍都城的影音紀錄,找今天有誰進過司法部,那我們的問題就太大囉,小草。」
瑪熙特嘆道,「就這麼辦吧,帶我去看前任大使。」
三海草的嘴抿成一道細細的、充滿憂慮的線條,在十二杜鵑帶領她們走向地下室的途中,她退回瑪熙特左肩旁的位置。
停屍間看起來還是一樣。冰冷,聞起來乾淨得不自然,彷彿曾通過清淨機的壓縮翻攪。科學部的那位官員—或是做完檢查後的十二杜鵑—已將伊斯坎德的屍體用罩布蓋起。瑪熙特突然被一陣緩緩蔓延的驚恐所籠罩:上次她站在這裡時,憶象在她體內激起驚人的情緒浪潮和內分泌激素,然後消失不見。現在她重返舊地,故障狀況又以片段閃現的方式再現:這個房間是否對她有害?(她是否希望有害的是這個房間,如此一來造成故障的罪魁禍首就不會是她自己,也不會是萊賽爾太空站的同胞?)
十二杜鵑再度將罩布拉下,露出伊斯坎德‧阿格凡死寂的臉。瑪熙特走近。她試著將屍體單單視為世俗的空殼,一個物理性的問題,而非供某人棲宿的居所,就像她身為同樣這一個人的憶象的居所。
十二杜鵑戴上滅菌手套,將屍體的頭輕輕抬起轉向,後頸朝向瑪熙特,隱藏住位於喉部主要靜脈、最大的防腐液注射點。屍體被挪動的樣子看起來柔軟有彈性,不像死了三個月那麼久。
「不太容易看得見—疤痕非常小,」他說。「但如果從頸椎頂端按下去,我相信妳會感覺到觸感的差異。」
瑪熙特伸出手,用拇指按著伊斯坎德顱骨上位於肌腱中間的凹陷。他的肌膚觸感如橡皮,太軟、太容易壓凹,感覺不對勁。憶象植入的疤痕在她指腹下,是一塊小小的不規則形,其下是憶象機器展開的結構,那股硬實的觸感幾乎跟顱骨本身一樣熟悉。她身上也有一模一樣的部位。她以前讀書時,常常用拇指摩挲著那裡,但自從她的憶象機器透過安裝手術接收了伊斯坎德的五年出使經驗,她就不曾再這樣做了。這不是他習慣的動作,而且在太空站以外的地方,這樣會露餡,所以她就讓這個動作隨著他們合而為一、成為融合的新人格而消失。
「是的,」她說。「我感覺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