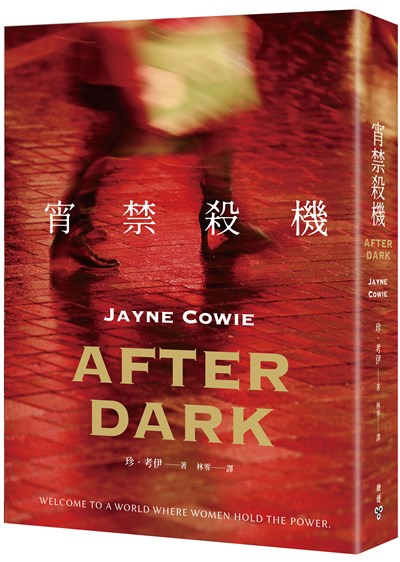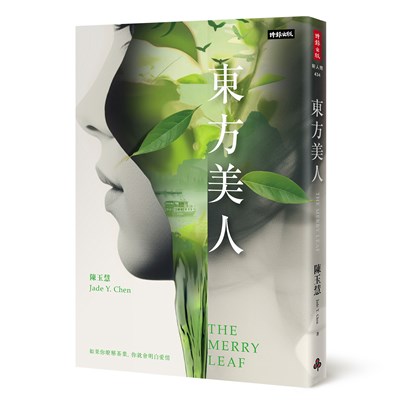《讓過去成為此刻:臺灣白色恐怖小說選》為國家人權館與春山合作出版選集,由胡淑雯、童偉格兩位小說家主編,從近兩百本作品中,選出三十位作者。這套作品包含四卷不同主題,在閱讀傑出文學作品的同時,將深入瞭解白色恐怖與戒嚴體制如何深深影響臺灣的各個層面。四卷的安排順序有其意義,不只是文選的並置,在各卷的主題下,這些作品彼此呼應,產生關聯,從卷一起首之作郭松棻〈月印〉,到卷四壓卷之作賴香吟〈暮色將至〉,這些作品使我們得見在戒嚴體制逐步生成、強化與轉變的漫長過程中,臺灣跨越數個世代的小說家如何連綴創造力。
文章節錄
曾經,面對白色恐怖,如同面對一座廢墟。廢墟裡有死傷,有監獄,有恐懼,斷垣殘壁裡迴盪著震耳欲聾的沉默,卻也閃爍著微微跳動的光點,只是,那些光點覆滿塵土,很少人伸手去撿。
二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臺灣送走了殖民政權,迎來了新的祖國。但是,這個祖國,就像馬奎斯筆下的「草葉風暴」,是一場沒完沒了的,內戰的遺物。他們像一陣暴風刮到這裡,在島嶼的中心扎下根來,尾隨其後的是「枯枝敗葉」。先是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清鄉,再來是戒嚴,白色恐怖,美蘇冷戰與韓戰。「枯枝敗葉冷酷無情。枯枝敗葉臭氣熏天,既有皮膚分泌出的汗臭,又有隱蔽的死亡的氣味。」在這群暴風般襲來的陌生面孔之間,最早與較早的居民反而成為違建般的存有,在自己的故鄉就地流亡。
動員戡亂(一九四八~一九九一)與戒嚴令(一九四九~一九八七,金門馬祖則遲至一九九二年才解除戒嚴),將「戒嚴」這樣的「例外」變成常態,將「臨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無限拖延成半個永恆,將「非常時期」化為「日常」,以殘酷的「律法」(《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炮製政治案件,將威權體制鞏固成國家體質,從而造就了臺灣的「國民體質」。恐懼吞噬心靈。在政權對肉體對反抗對言論與思想的鎮壓中,人民以沉默求得自保,遁入舒適的遺忘,安定向上,明哲保身。四十幾年過去,我們迎來了解嚴,但解嚴超過三十年,戒嚴的遺緒至今依舊,禁錮著這座島嶼。這之中最突出的「國民精神」之一,大概是,「去政治」的政治性格。許多人成為恨政治的人,一講到政治就反感,以「政治很髒」來迴避政治。然而,這種「去政治」的過程,弔詭地,正是一種高度「政治化」的過程,是幾十年教化的結果。它的政治效果是,讓人民懵懵懂懂,幾近無知,卻以這樣的無知為常,甚至引以為傲,以為乾淨。於是,開口談論政治的人,拒絕無知的人,往往被視為偏激,可笑,討人厭。白色恐怖不但鎮壓了反抗者與異議者,也將彷彿無關的所謂大眾,調教成某種方便統治的精神與形貌,從而傷害了文學與藝術,傷害了幾代人的創造力。
如此說來,《讓過去成為此刻》這套小說選的出版,或許可以是某種,以虛構抵抗現實的方式,抵抗威權統治的「教化虛構」,讓政權及其暴力的每一場勝利,都變得可疑。思考白色恐怖,如同書寫政治小說,恰恰在拒絕政治(尤其政權)對藝術的傷害。以小說的創造性擾動那些曾經,擾動那段均值,布滿「同一性」,因而空洞化了的時間。向「過去」借道,是我們邁向未來,或許不是唯一,但絕對不枉此行的一種方式。這條路或許比較遠,但是比較美,而小說所能提供的美學經驗,包括認識醜陋,認識惡。
然而,書寫與閱讀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對威權統治的記憶何其空泛,直到今天,民主化超過三十年,我們依舊在澄清與爭論著,威權統治下被槍決與監禁的確切人數。特務,眼線,抓耙子的身分與數量,跟政治案件的數字同樣不明不白。數字是謎。無解的謎足以造就各種扭曲。記憶的扭曲,道德的扭曲,人性的扭曲。於是這套書,某種程度可以被視為,「島嶼的肉體與精神傷殘史」。這是小說此一文類,給人性最獨特的禮物。它為我們留存了那一段,無論有無政治意識,都可以成為匪諜與叛亂犯的生活,「不要亂說話」,「囝仔人有耳無嘴」,彷彿就連夢話也能告了自己的密。沒說出口的思想,心裡的苦悶,房間裡的祕密,夢中的恐懼,也要面對特務的盯梢,與「軍憲警」三合一的戶口檢查。小心日記,小心與某某的合照,小心同事同學與朋友,小心你的抽屜,小心「知情不報」。在強迫告密的「連保連坐」下,在鼓勵告密的獎金制度下,人們在相互猜忌裡相互監視,官僚參與其中,基層公務員參與其中,學校老師也參與其中。就連即將出獄的政治犯,也要簽下這樣的切結書:「保證絕不洩漏案情等一切坐監經過否則願受法律制裁」,借用作家陳列的話,這形同配合政權嚴厲遂行社會控制的權力,協助掩飾加害者的罪行。「假如我們沉默不語,我們的心裡會覺得不舒服。假如開口說話,我們又變得可笑。」但文學收容了一切的曲折,與看似中立理性的成見決裂。文學抗拒媚俗,尤其抗拒「黨國」,「信仰」,「主義」,「領袖」施加的心靈獨裁。在黨國威權的媚俗裡,兩蔣的屍體不能下葬,他們的屍身不容腐爛。這對父子被幽禁在黨國神話的教化虛構之中,浸泡於防腐劑的惡臭裡面,活埋在銅像的微笑裡,一日無法步下神壇,就一日無法得到安息。
在解嚴後社會力爆發,本土化與自由化的浪潮下,白色恐怖逐漸受到研究與重視,並且在大眾化的學習熱情裡,出現了各種通俗的面貌,卻也冒著被「新的政治正確」抹除面貌的風險。這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冤,錯,假」與「英雄敘事」的風行。在編選這套小說的過程中,我們捨棄了這一類,略顯理所當然的申冤喊痛之作,過分化約的歷史意識,也繞開了英雄與烈士崇拜,而試圖以美學為尺度,給「內省」較多的空間,讓差異擴增,讓複雜性留存。這套小說無意為昂揚的「主義」服務,不論它是左是右,保守或是進步。不服務於舊的國家神話,也不服務於另一種,與之對反的,新國家想像的建構。小說維持它的叛逆,讓差異︱政治的差異與差異的人性︱復活,這是小說的無用之用。於是,在這套小說選當中,我們可以讀到出賣與背叛,讀到「政治轉向」,讀到「不重要的受難者」所遭遇的生存艱辛,家人的冷待,對信念的疑惑,讀到告密者的自剖,行動者的思想貧困,與思考者的行動軟弱。以及,中共在臺地下黨員的理想與挫折。
最後,讓我改寫小說家珍奈.溫特森(Jeanette Winterson)的話:文學是公有地,它無法由國家或商業利益完全把持,也不像流行文化那樣,被資本驅動著進行大面積的露天開採,它是由想像力所開展的一方,空曠不羈的空間。書寫是強敘事。閱讀,則是強記憶。頑強地走下去,並非常人所稱許的所謂勇敢,反而,這是一件幸褔的事,即使幸福裡布滿蹣跚。
在蹣跚的幸福裡,有班雅明的新天使守護著我們。祂抵擋著一切裹脅著逼祂背向過去,面朝未來的風暴,凝視著歷史災難的廢墟,明智而堅強地,面向過去,背對未來,以倒退的姿態,向未來邁進。
—本文摘自胡淑雯編序〈倒退著走入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