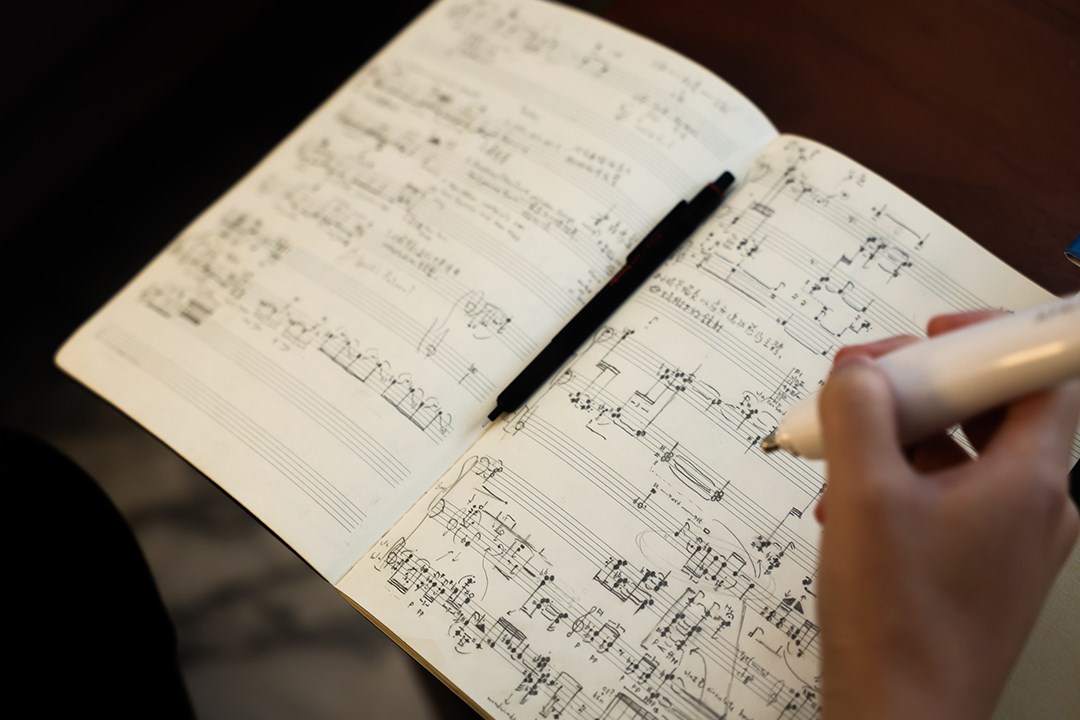碩果僅存的冬天陽光
前往尋找風景的過程,看作是⼀場永無⽌盡的旅途,有時未必要孤單前往,而是更喜歡⼀個⼈,進入那種放空,拍下感受性的事物。
梵谷作品中的色彩與構圖,大多來自他腦海中看見的真實;草間彌生的點點,是她一生用創作對抗自己的幻覺與幻聽。有恐慌症的作曲家張玹用自己的音符,為精神病患撐開了一片片靜謐與柔軟。
旅美作曲家張玹發現自己有恐慌症,是在2022年音樂劇場《緣那麼淺愛那麼深-幾個瘋狂書迷的大武山下之旅》的慶功宴上。
那天在屏東演完,張玹先回到飯店整理,打坐,走去熱炒店準備慶功,當他喝下第一口酒時,張玹發現自己上半身麻,手也麻了,緊接著耳鳴,呼吸困難,彷彿有人在捏他的心臟,「我想這是怎麼回事,自己是不是要掛了?」張玹開人生跑馬燈,「難道是小鬼來找我?」
小鬼是《緣那麼淺愛那麼深-幾個瘋狂書迷的大武山下之旅》裡面的主角,一個命喪大武山下的亡魂,隔了40餘年,化為作家龍應台筆下與敘事者作家在大武山家鄉相伴的14歲少女靈魂「小鬼」,音樂劇場再以此為靈感創作,「我明明就把音樂寫得這麼好,希望祂可以住在我的音樂裡,難道我有講錯什麼話對祂不敬嗎?」張玹越想越緊張,站起身來想要離開餐廳,突然發現自己走不出去。
張玹回憶他當下可以走,但他失去方向感,正好製作人黃毓棻經過,張玹一把抓住求救,送到醫院,「醫生看診加上遠方醫生友人,這是恐慌發作,一是過度換氣,二是感覺自己要掛了,我兩個條件同時滿足。」張玹說唯一慶幸的是,知道發作時自己死不了,「好像就稍微安心。」
至今張玹依舊與恐慌症共存,透過自我控制讓情緒平靜下來,張玹說音樂創作像釀酒,需要時間,「靈感來了,就在我身體裡面的某個部分,需要時間去長出來,不能硬逼,但也不能遏止。」張玹說那種感覺是創作過程中不只大腦在運作,而是需要動用到全身的神經元去接收靈感,「可能這個狀態連續很多個月,也因為這樣,身體沒有辦法負荷,就發病了。」
很巧,這也正是張玹受彰化敦仁醫院之邀,為醫院創作音樂的時刻。
敦仁醫院由院長胡延忠創立,到2025年就滿20年,這是一個很不像精神病院的精神病院。外觀看起來像是置身於森林之中的大宅院,第一進是門診區,室內明亮,牆上掛著許多畫作,有一幅畫裡面有各色人種,相依相親,彷彿宣告人們其實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畫作與鹿角蕨相依,襯著淡淡的音樂;一角則有研磨咖啡,任何人都可以免費享用。
這裡沒有藥水味,深藍色的窗框有點像童話故事裡的小屋,那是胡延忠親自挑選的顏色,「我不想要有醫院的感覺,但能選擇的顏色好像也不多。」
從小喜歡尼采跟哲學,高中時看許博允、林懷民的表演藝術長大,胡延忠對於藝術有自己的喜愛。後來念了陽明醫學院,就要畢業時思考出路,選擇了精神科,但因為想到時各大醫院都已經滿額,胡延忠到了一家公立療養院工作,一做就是十年。
「跟我想像的落差非常大。」胡延忠說,當時那是一個舊年代的設施,「第一天去病房,大門是鐵欄杆做的,開關得用手上的一大串鑰匙逐支打開,關門的聲音,真的很像監獄。」胡延忠回憶,病房走廊採光也不太夠,地面也很潮濕,「老實講我衝擊非常的大,但我不會去抱怨說環境不好,但那樣的環境給我了很大的刺激,我開始去想,如果另外一種作法會不會更好,當時累積了很大量的思維。」
十年倏忽,胡延忠即將有機會接科主任,「我就想即使我在行政職,因為公務機關,有很多事情也是很難去撼動,於是就想離開,出去看一看。」胡延忠離開之後先去國外工作,回台灣也半轉行轉任顧問,但都有所侷限,內心一直很想要有一個可以發揮自己理想的精神病院,「剛好有個因緣,有朋友有意願也有這樣的理解,就一起試看看。」
幾塊地讓胡延忠選,胡延忠決定了這塊山坡地,希望倡議日本里山(satoyama)的概念,胡延忠說,這是日本對「社會-生態-生產地景與海景」的傳統稱呼,是歷經幾百年累積人與自然共處的智慧,「我一直認為,大自然不可能等同於藥物,但大自然可以有美的觸發。」
20年倏忽而過,敦仁醫院不曾被鄰居列為「嫌惡設施」,不曾被勒索,身為院長也是老闆,胡延忠說自己是「務實的理想主義者」,「精神病患也是人,需要有尊嚴的被對待,我只是在做我自己也可以接受的事情。」
有一些障礙級別比較高的病人,用藥較為沉重,醫院聘任了健身教練帶病人做運動,一年多以來,病人跌倒的機率下降;醫院有圍牆但不會高聳,病友反而不假外出的頻率大幅降低;醫院讓病友可以照顧一個小小的植物,讓自己被需要;預定時間內病友還可以自己選擇設計師,剪出自己想要的髮型。
行政師跟護理師相互理解工作,也隨時補位;公共區域的座位刻意使用彩色,還有「麥當勞桌」,讓比較熟悉的病患可以一起互動;牆上掛了許多藝術品,胡延忠希望藝術的美感能夠盡量融到病人的生活細節之中,「我無法有很多量化的數字,告訴外界掛藝術品對於病人有甚麼實質的幫助,我只是想打造一般人都會覺得舒服的環境,不讓病人受到更多刺激。」
胡延忠說,會找張玹做音樂也是基於這樣的理念,「透過好哥兒們鍾永豐,認識了張玹,我一直覺得醫院的五感很重要,於是有了這套《安土》專輯。」
寫《安土》的張玹長年學佛,台北工作室裡有好幾尊佛像,神態端莊,「我是九成九的學佛人,但我沒有皈依。」學佛就是要「破我執」,但對一個創作者來說,張玹從開始決定作曲之後,會思考可以怎麼樣寫得跟別人不一樣,寫的每一顆音如何跟自己產生關係,怎麼樣可以變成自己的語彙,「這對我來說就非常地矛盾跟衝突,我一直在『有我』跟『無我』兩者之間的辯證,但是在『安土』這套作品裡面,其實我少了很多『自我』,這次的機緣對我的創作生涯來說,有了很重大的影響。」
張玹以醫院一天的作息為出發點,讓新創音樂替代原本的廣播與鈴聲,陪病友起床、用餐、運動、領藥、小睡,及至晚上伴隨入眠,每一首樂曲充滿藝術性與精巧性,張玹讓這些大家熟悉的旋律加以內化,聽起來充滿熟悉的歷史感,卻饒富新意。
張玹說這中間經過好幾個版本,中間有一個版本是有很多童謠跟老歌的選段,但卡在授權,後來才有了最後這個版本,「要做童謠跟老歌的改編對一個當代作曲家來說,一開始還真的內心有點掙扎,但我思考很久,這件事情要回到作曲家的社會責任是什麼。」
當代作曲家的責任之一,是為了拓展聆聽的邊界與聆聽的方式,張玹認為思考自己跟社會、跟人的關係是什麼也相對重要,回到台灣的當代音樂圈,「我認為老歌跟童謠這些文化財,其實還沒有真正被好好處理過,這會讓我願意去嘗試。」
想像一群不被社會接受的人,有部分的精神病患其實是連家人都不想要的人;也因為很多社會新聞,精神病患也常被貼上標籤,要怎麼寫他們可以接受的音樂,張玹也有自己的盲點,「一開始我很掙扎,我跟精神病患這件事一點關係都沒有,我是不是為了要做有社會性議題的,有關懷議題的音樂去做這件事。」
但,難道要生了病才能為精神病患創作?
「在美國的文化氛圍是這樣的,藝術圈或是文化圈常常會討論,如果不是黑人,憑什麼去寫黑人的歷史;如果不是LGBTQ群體,憑什麼去寫他們的故事,這當然這有很多討論的空間。」張玹說但以他自己的狀況,「如果要創作相關議題,最好的就是我自己如果有類似的情況,或者我跟病友與家屬聊,跟醫生跟護士聊,甚至我得在那個醫院生活一段時間,我覺得這才誠實,否則我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
偏偏這時候自己發病,這件緣分就非常玄妙,「我覺得是非常好的時間點,因為 有了恐慌症,讓我有了寫這個作品的正當性,也顧及身為一個藝術家的誠實,這兩件事情是我覺得寫這套作品最重要的部分。」
這也是一套張玹自己說自己可以每天都聽的音樂,但是創作背後,是張玹經過長期的靜坐、冥想,靠著呼吸終能與自律神經自處的歷程。
張玹說,其實藝術是很多元,也很多面向,可能某一個時候可以有功能性,「像莫札特的音樂早上聽會很開心,蕭邦的音樂可以在吃飯的時候聽,但這兩個時間點你不會聽蕭士塔高維契的音樂,因為太刺激了,換句話說,每一種音樂它有適合的時間跟空間。」這次為彰化敦仁醫院創作的音樂,就是一種陪伴,讓病友「舒心」,「我也希望這套作品會被其他音樂家喜歡,帶去更多地方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