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心回填耗損的肉身:訪《四樓的天堂》導演陳芯宜
在一切作為與創造之前,在他開始獻身於他的任務之前,藝術家先召喚當下的真心,透過練習加以把握住。他開始成功地抓住真心,不僅只是偶然的片刻,而是可以隨時把握,於是這種專注就像呼吸一樣和箭術連結在一起。
──《箭藝與禪心》 奧根.海瑞格(Eugen Herrigel)
由陳芯宜執導,黃秋生、謝盈萱主演的公視劇集《四樓的天堂》,已於10月9日開始播映。劇中黃秋生飾演推拿師,每集會有不同人物帶著身體的問題前來尋找治療,推拿過程中除了療癒身體,也點出各人心裡的結。
導演陳芯宜過去以紀錄片見長,主題觸角多變,囊括臺灣劇場、日本舞踏、社會運動、身體意識……此外也活躍於劇場工作。在訪問之初,本刊請她列出推薦給讀者的書單,只見清單上除了有《經絡解密》、《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這類與戲劇主題扣合的作品,以及《劇場及其複像》、《劇本:海鷗》等與劇場相關的書籍之外,還包括了像《箭藝與禪心》等等深入心靈探索的讀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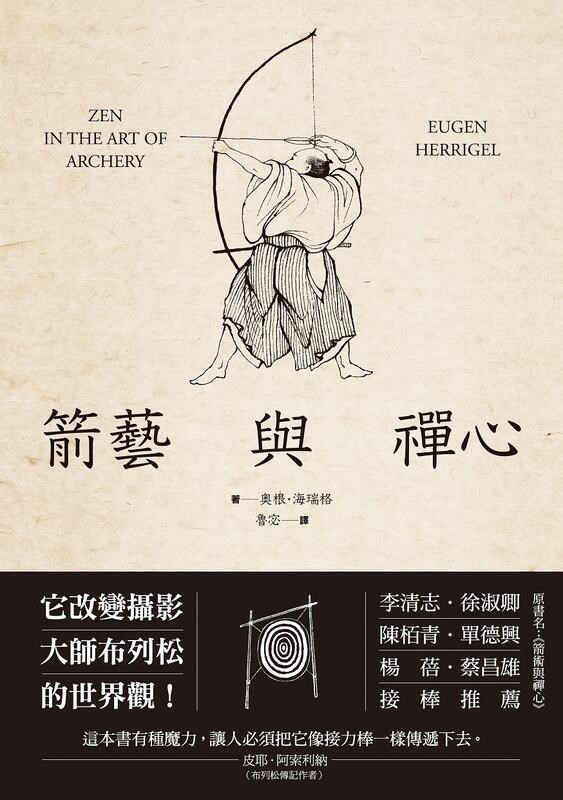
德國哲學教授海瑞格為了追問生命的意義,跨洋來到日本學禪卻仍處處碰壁,後來,透過箭術,他終於體驗到禪的真義。拍攝《四樓的天堂》時,陳芯宜反覆咀嚼了許多書,海瑞格的《箭藝與禪心》即是其中之一。
這部戲劇以四條主線為根──推拿師、心理諮商、劇場人、社會運動者──長出一棵巨大的提問:「如何成為一個完整的人?」
陳芯宜說,她知道這個提問的野心太大,不確定自己是否成功,唯一可以知曉的,是拍攝現場所創造出的真心。回憶拍攝的那幾個月,她溫溫地說:「表演是什麼?是除了表演以外,還有一種真的、純粹的東西存在於其中。」

心裡的傷痛,身體會記得
首先,為什麼是推拿?
「劇中有段台詞,張琪(謝盈萱飾)說每次推拿師把她的頭整得好好的、捧起來的時候,她就覺得可以去死了。」陳芯宜笑說:「這句台詞完全就是我的經驗。每次被推拿師捧起,那瞬間我真的可以秒睡,有種終於可以被放下去、可以去死,可以好好躺在棺材裡的感受。」
過去為了拍攝紀錄片《尋找乳房》,陳芯宜曾與幾十名女性有過深入問答,當時談的都是身體髮膚的話題,不過「講到最後,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心理諮商師。我們原本談的明明都是身體,但好像無可避免都會聊到心理。」

無形的傷口會藏放在有形的肉身中,在《四樓的天堂》裡,觀眾會發現整部戲的命題雖是「完整」,源頭卻是病痛。藉由推拿師的雙手,能夠理出一句話:「人必然有病,因病而完整。」
這個命題如此沉重,化成電視劇時卻必須舉重若輕,因此飾演推拿師的演員必須能沉穩如大地,亦能輕盈如鳥。
那句不是我寫的台詞,是他的生命
在塑造推拿師「天意」這位靈魂人物時,陳芯宜把自己過往拍過紀錄片的對象結合起來:「在我想像中,他應該是《行者》裡的林麗珍,也是《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裡的櫻井大造。」她說,那是融合內在療癒及外在抗爭、兼具柔軟而剛強的推拿師天意。「但最後的結果,天意這個角色變成林麗珍加上櫻井大造再加上黃秋生──他把很多自己的東西都放進來了。」
回想其中一幕戲,黃秋生與對手演員范少勳站在河邊,陳芯宜說:「那場戲他們把台詞都講完了,但我沒有喊卡,攝影師知道我的習慣也繼續拍下去。起初他們停在那邊也沒幹嘛,就是沉默看著河水。」
拍攝紀錄片的經驗,使陳芯宜成為一個敏於「時機」的人。表演固然依靠技巧,但時機卻不可強求而至,這使得她在拍攝劇情片時,不知不覺成為「不喜歡喊卡」的導演,只要現場狀況允許,她寧可讓演員的情感流瀉,就像不阻斷河水自然流淌那般。如果夠幸運,就能看見角色與演員融為一體,演員藉著角色之口講述自己的生命經驗,而那份經驗又活成了該名角色的靈魂。比方說,在那場應該要喊卡的河景之戲,陳芯宜等到了這句話:
黃秋生凝視河畔好一陣子,開口說:「我小時候也住在河邊。很小的時候。在香港。」
「那句話不是我寫的台詞,」陳芯宜語帶哽咽:「秋生哥年輕的時候有段時間真的那樣,很貧窮、睡在河邊過,那句話就是他的生命。」
對照著香港此時的光景,做為演員的黃秋生拿著「臺灣就業金卡」出演《四樓的天堂》,戲中他所飾演的推拿師有句台詞是「好好活著本身就是一場戰鬥」,寫下這句台詞時,陳芯宜無法預料到黃秋生不僅接住了,還以更具生命力的方式輕輕地道出。
那是表演,卻又不只是表演。
撕開保護結界,抵達真實
從事導演工作,最迷人的時刻便是「所有人都處在創造的那一刻」。陳芯宜解釋所謂的「創造」不是技巧性的追求,而是眾人彷彿忘卻那些形式上的技巧,轉而凝聚於下一秒的未知。
「《四樓的天堂》團隊都是一起工作很久了的夥伴,我們找來的演員也很不一樣,他們投注了很多生命經驗在裡面。」陳芯宜說:「這齣戲我一再看到演員撕開保護自己的結界,顯露出某種真實的時刻。」

紀錄片拍久了,陳芯宜對於「真實」的要求簡直到了苛刻的地步。「很多東西的確是可以『演』出來,不過有件事情很難表象化,就是『氣場』,它讓你的存在本身就成立,不用演,在很多厲害的演員身上都一定存在這種氣場。」
雖然有些人認為,陳芯宜連臨時演員都要求要有氣場,「有點over了」,但她沒有因此放下自己的執念,「所以到後來,劇情若需要劇場工作者,我就找一個劇場工作者,畫面中的舞台監督是真的舞監,如果需要擋拆的人,我就真的找做社運的來演——他們知道如何用身體擋拆,知道怎麼保護夥伴。那個東西完全教不來,就僅只是存在著,那是我很需要的。」
小說《1Q84》曾寫道:「所謂的現實,就是針一扎下去便會流血的地方。」而陳芯宜的導演風格,同樣存在一種扎針血流的痛感,她期待在安排好的表演裡有真切的生命狀態,期待從絕醜裡見到美的快意,在太過順暢的時刻反而質疑起拍攝的必要。
「例如有次我拍《如果耳朵有開關》,記錄三個聲音藝術家。那次的感覺實在太順了,順利到我產生很大的質疑,所以後來看到拍攝者在哭,我理應要趕快拍啊,可是我卻對這一切產生疑惑,反而想試看看我在最想拍的時候刻意不拍會變怎麼樣?有點像找自己麻煩的樣子。」
她相信繞遠路才能找到最好的路徑,因此《四樓的天堂》為了抵達完整,必先陳述病痛;同樣地,為了掌握住全劇的美感氛圍,她得要先理解醜惡為何。
那樣的醜,反而最美
《四樓的天堂》有一場劇中劇,呈現未來AI世界──一切都被設定好了,你將看不見任何與你美感相違背之物,無論眼之所觸、耳之所聞、心之所感,一切皆美。問題是:倘若抵達了那個未來世界,我們是否更容易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了呢?
這個設定,來自陳芯宜有段時間對美產生的懷疑。她說,「劇場和舞蹈總是會帶給我很多想像,不過有一陣子看完表演,我仍然覺得無法滿足,很渴望自己的內在有被打到,覺得那樣一來才是所謂的『美』,而不只是外在的、視覺的表現而已,美是能讓內心震盪的。」
在此之間,有兩個藝術家的作品是陳芯宜面對美的疑問時,無法從心中洗掉的印記。第一是林麗珍的《花神祭》,二是日本的舞踏家秦Kanoko。前者簇擁著陳芯宜拍下紀錄片《行者》,而後者則讓她重新發現了美。
「舞踏非常醜。」陳芯宜說,舞者滿身百粉,赤裸上身,如鬼魅靈影,彎折扭曲,在淒厲的聲響中創造身心的解放。但也正是那醜絕的姿態,讓陳芯宜深深體驗到了「美」的意涵。
這個概念延伸到了《四樓的天堂》。陳芯宜談起其中一幕,演員在臨終之際,望向她被打掃得一塵不染的家,望向她所建立的乾淨、有條不紊的一生,如今竟將敗壞於病痛之中,忽地哭了出來,哭完以後便似氣力用盡般癱坐客廳。
「那個姿勢並不好看,但在那一刻,那懶散、醜陋的姿勢與角色生命最後的狀態疊加在一,就像是把過去緊緊抓住的SOP與規則一口氣放掉,把你的一生給哭出來。那個所謂醜醜的姿勢,在我看來也是一種美。」
好好活著本身就是一場戰鬥
《四樓的天堂》殺青後,陳芯宜將《箭藝與禪心》送給演員范少勳。戲中他是推拿師天意的徒弟,是一名塗鴉客,也是個社會運動人士。
幾年前陳芯宜拍過關於拆遷議題的短片,「總覺得無力感很深,好像再怎麼衝撞都沒有用,好像無論如何都打不過高牆。」她以鏡頭見證在那些場域中,肉身如何不斷地被消耗,好像我們離「完整」越來越遠。
然而意料之外的是,有些社運的朋友在看完紀錄片《行者》後,哭著走出來對陳芯宜說:「我從林麗珍老師身上得到能量」、「我覺得所有做抗爭的人都應該去做林麗珍老師的徒弟。」

與朋友們聊過以後,陳芯宜才明白,雖然一是捕捉美的動能,一是抵擋醜惡的威脅,然而兩者都是在無形的壓力之中,以有形的肉身去體現、去承接。「不是說那部紀錄片真的說了什麼,而是林麗珍老師傳達出一種整體性的能量。那是無形的,告訴我們這一路消耗的身體,如何能夠藉由其它過程去回填──那是一個契機,讓我思考有沒有可能把我所有正在關注的事情,用一齣劇來表現出來?」這個疑問,催生出《四樓的天堂》。
為了形塑劇中社運的角色,陳芯宜真的介紹范少勳向林麗珍學習身體的運用。相較於《四樓的天堂》中諸多資深演員,范少勳是新生代中很亮眼的存在,使陳芯宜能一再看見表演者身上不假雕飾的「真實與純粹」。
演員之路如何走得長久?比起討論技藝,陳芯宜更相信是《箭藝與禪心》所謂「先召喚當下的真心,透過練習加以把握住」。她說:「演員工作有時候很像街頭運動,每一次演出都在消耗自己的真心。」
最後再一次,讓我們回到那句台詞說的:好好活著本身就是一場戰鬥。
關於「如何成為完整的人」這個大哉問,陳芯宜以《四樓的天堂》交出的並非一句答案,更像一種叮嚀:唯有好好活著,我們才能踩著質疑去尋找答案;唯有好好活著,我們也許才能向「完整」的人持續靠近。
導演陳芯宜的田調書單: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
快門慢想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