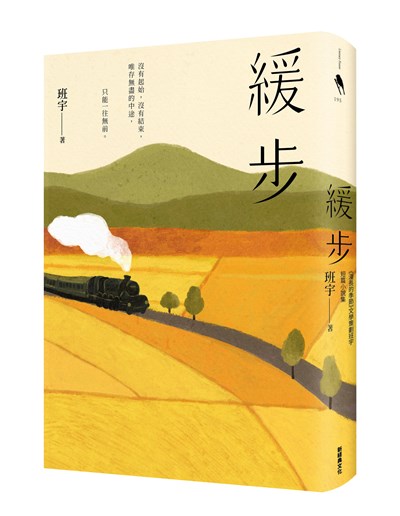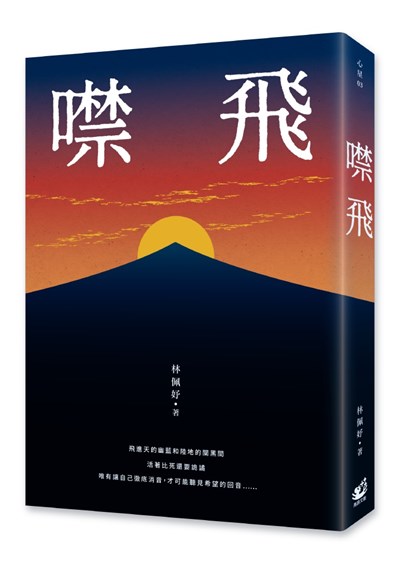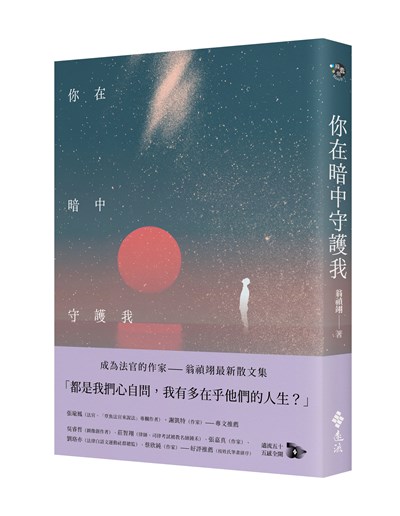法國當代最暢銷的作家瓦萊莉.貝涵(Valérie Perrin)繼《星期天被遺忘的人》,在台灣推出最新力作《為花換新水》,又一次帶讀者走進她的家鄉法國勃艮地一座小鎮,以墓園裡的美麗中年看守人維歐蕾特為主角,描寫她在女兒意外死亡及丈夫無故失蹤後二十年來的生活。小說圍繞著這座老墓園進行一場超展開,寫墓園的地景物事,也寫維歐蕾特的工作團隊和她管理的工作內容,寫墓園裡妙人趣事。直到有一天一位警官的出現打破一切平靜……小說用兩條敘事線為讀者娓娓道來不同世代的生命課題,一個揭開了維歐蕾特的女兒之死和她丈夫出走的真相,另一個則讓人看見一種超脫世俗框限的愛情。最後當真相揭曉,人要如何原諒他人並找到重新站起來的力量,而這一切關鍵都在維歐蕾特培育的那一座花園裡。
內容節錄
《為花換新水》
1 不過是少了一個人,這個世界對我們卻已無處不是荒蕪。
和我住同一樓層的鄰居什麼都不怕。他們沒有煩惱,不墜入情網,不懂得焦慮。他們不相信偶然,不做承諾,也不會出聲。他們沒有社會保險。他們不哭泣,不找鑰匙、不找眼鏡、不找遙控器,他們不找小孩,也不需要尋找幸福。
他們不看書,不繳稅,不節食,沒有偏好,不三心二意,不用鋪床,不抽菸,不列購物清單,話不需經大腦才說,也從不需要找人代班。
在他們的世界裡,他們不拍馬屁,沒有野心,不懂記恨,他們不懂得招搖賣弄,不會心眼小,既不寬宏大量,也不懂得忌妒,他們不在乎邋遢或整潔,不在乎自己是高尚或滑稽,不沉迷於事物,不懂吝嗇,不懂微笑,他們不會展露惡意,不舉止暴躁,不對誰心生愛慕,不發牢騷抱怨,不偽善,他們既不溫順也不頑固倔強,他們不優柔寡斷,不耍狠,不說謊、不偷竊、不投機,他們既不懷抱幹勁、也不怠惰懶散,他們沒有宗教信仰,也不邪惡詭詐,他們不是樂觀主義者。
他們是死人。
他們彼此間的唯一差異是,棺木的用材不一樣:有的人用橡木,有的人用松木,不然就是桃木。
2 你要我如何才好,如果從此聽不到你的腳步聲?你的,或是我的人生還能不能夠繼續?我不知道。
我是維歐蕾特.杜森,我做過鐵路平交道駐工,現在是墓地管理員。
我品嘗這人生,就如同小口小口啜飲著摻和了蜂蜜的茉莉花茶。當夜晚來臨,墓園柵門關上後,把鑰匙掛在浴室門上,我就置身天堂了。
不是我同層樓鄰居的那種天堂。不是的。
我說的是活人的天堂:就是喝一口一九八三年釀造的波特酒。每年九月一日,荷西-路易.斐迪南會帶一瓶這樣的優質葡萄酒來給我。而我倒在小小水晶杯裡品嘗的,就是我僅存的些許度假時光。每到晚上七點,不分晴雨,風雨無阻,我都會享受一下這此生遲來的小確幸。
兩個盎司杯的酒透著紅寶石的色澤。閉上眼睛,我品味來自葡萄牙波多的葡萄之血。只要喝上一口,整晚快意暢然。只要兩個小小盎司杯就足夠,我不是愛喝酒,而是喜歡微醺的滋味。
荷西-路易.斐迪南每個禮拜都會來他太太瑪麗亞.潘托(1956-2007)的墳前獻花,只有七月他不到墓園的期間由我代他奉上鮮花,他以波特酒做為答謝。
我的禮物式就是上蒼給的禮物,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我都這樣告訴自己。
我的人生曾經很不幸,甚至頹然絕望。人生一無是處,整個人被掏空耗盡。我的生理機能不需我的靈魂即能自主維持。聽說,人無論高矮胖瘦、年紀輕或長,靈魂的重量都是二十一公克。
但我從不想要不幸的人生,我決定不讓不幸的人生延續。我的不幸,終有一天要劃下句點。
人生起步我就拿到一副爛牌,我是匿名生產的孩子,出生於亞爾丁省北部,和比利時國土曖昧交合的一隅,被形容為「過渡性大陸型氣候」的地方,秋天降雨豐沛,冬天結冰頻繁, 會讓我聯想到賈克.布雷爾歌裡唱的在低暗天空下漂浮的運河。
我出生的那天沒有哭。因此,宣告我出生前已胎死腹中的行政文件還在填寫時,我就像一件沒貼郵票也沒寫收件人的二千六百七十克重的包裹給扔在一旁了。
死胎,一個無生命跡象也無姓氏的嬰兒。
助產士趕著把表格填好,速速幫我選了個名字:維歐蕾特。
我想像自己出生那時大概從頭到腳全身發紫。
當我的身體開始出現血色,助產士此時不得不填寫出生證明,她沒再改掉名字。
我被放入保溫箱,皮膚重新熱了起來。想必是那個不想要我的媽媽,在她的肚子裡把我凍壞了。保溫箱的溫暖將我重新帶回人世。一定是出於這個緣故,我才這麼喜歡夏天。如同向日葵那樣,我從不曾錯過任何泡在第一道陽光下的機會。
我結婚前本姓是特雷內,與歌星夏勒.特雷內同姓。想必是幫我取名作維歐蕾特的助產士幫我取的姓。她應該是喜歡夏勒.特雷內。後來我自己也喜歡夏勒.特雷內,有很長時間我都把他當作我的遠房親戚,一個怎樣都不會見到面的美國姑丈。人們要是喜歡一個歌星,也會因為老是唱他的歌,感到與自己喜歡的歌星莫名有某種親緣關係。
杜森,是後來我與菲利浦.杜森結婚後改的姓。遇到有這種姓氏的人,我本該很有戒心才對。不過,有的男人姓普蘭東,卻是會打老婆的人。可見就算有個好聽的姓,也不能防止人變成爛人。
只有在發燒的時候,我會想起媽媽。其他時候我從不曾想她。然後我就這樣健健康康長大了。我的身形很挺直,父母的缺席反而使我的脊椎好像有了根柱子支撐著。我總是昂頭挺胸。這是我很特別的地方。我從不駝背,即使在哀傷的日子裡也一樣。人們常常問我是不是學過古典芭蕾?我說沒有。是我的生活鍛鍊出我的體態,是我的生活讓我每天過得都像在做扶桿練習和立腳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