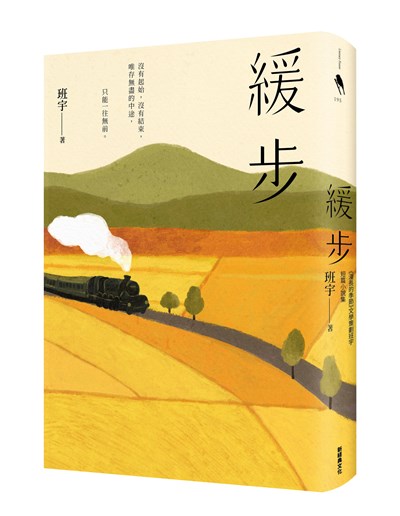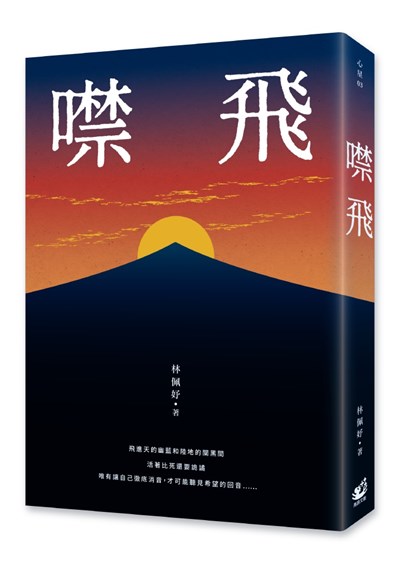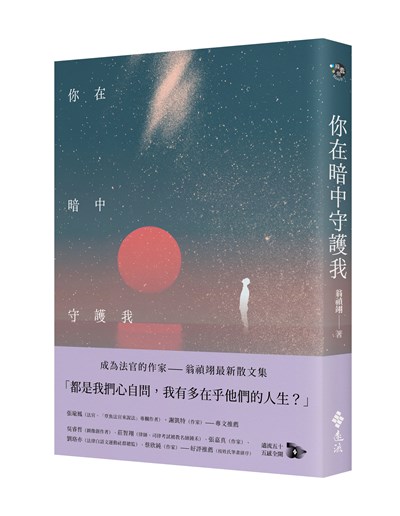位居北美的佛蒙特州的藝術村,這些年輪流進駐了好幾位台灣作家,詩人葉覓覓、小說家黃崇凱、陳又津、洪茲盈,加上陳育萱、何敬堯。許多讀者或有志寫作的青年作家,應該都很好奇在異鄉的駐村寫作生活,有哪些不為人知的衝擊與獲得。這次就由著有長篇小說《不測之人》的陳育萱,及以奇幻和推理風格著稱的何敬堯,合力寫出他們在2015秋天的佛蒙特駐村行,是否真如陳又津說的:「佛蒙特駐村寫作計畫,讓不同時空、懷抱不同夢想的人,走進那間紅色磨坊,走進小牛寫作樓,面對同一條河。……語言的幽微界線,跟著12小時的時差,一口氣跨越了。」
文章節錄
《佛蒙特沒有咖哩:記那段駐村寫作的日子》
不枉他方◎陳育萱
駐村是介於旅行和定居之間的小小妥協,對於渴望擁有安靜時光創作的異邦人,前往異地的意義之一,摑醒沉睡的異質性。
縱然以為自己還可以做到盡力不與世界妥協,然而我永遠清醒自己錯估了全球資本主義暢行所帶來的無國界假象——使用其他國家的語言,等同於國際觀,這是過往教育隱形傳授的錯誤密信。我們各自拆閱,羨想著有群人不必學習他國語言,便能逕自攀上自由女神像。
念頭退潮,多年後,我搭上駐村列車,短暫成為無國界的一員。在抵達之前,我設想出現在我面前的創作人將來自世界各地,我們將在這種特殊的機制下,站在文學或藝術的版圖上,為對方指路。
這是一條長路。
引薦這座島嶼上的作家,餐桌另一端的作家瞇起眼來,他略為尷尬的神情,表示他一無所知。我安慰自己:至少他沒把台灣和泰國搞錯。
幾人起身去盛甜膩的草莓奶油蛋糕,我叉住盤中的沙拉和麵包,不塗奶油也不蘸醬,木木吃著,腦中的兩種語言正在打架。到佛蒙特數日後,最常衝擊腦容量的是暫歇中文使用權,為英文另闢疆域,盡可能找尋說話的機會。
偶爾我流暢,友善的作家和藝術家,總會碰到幾位,他們便大力稱讚我,英文說得好。只是,模組很快用光,字彙彈藥庫空懸,我走到書店,買一本當年度的最佳短篇小說選,返回坐在工作室裡,逐行讀。盯著,歪歪扭扭契入,過去習以為傲的語言能力,在英文小說行陣中感受到的是寂寞。
交錯飲著咖啡和蘇打水,我猜想哈金、納博科夫、石黑一雄,這群自願移民或被迫流亡的作家,順著潮勢上岸後,他們如何寫作與生活?當查詢到索忍尼辛定居於佛蒙特州的卡文迪希鎮,距瓊森鎮約兩小時半的車程時,忍不住大呼不可思議!鎮民在索忍尼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肯定後,一致決定將一間石屋老教堂用於設置索忍尼辛的展覽館。非自願身處異邦的索忍尼辛,竟能熬過漫漫十八年,堅守當年的誓言——我將活著回來。
寡居於清寥的小鎮,若又不願花時間經營他鄉語言,過於龐大的孤獨感必定堅若磐石。索忍尼辛畢竟不是出於自願交流的心意,然而被迫移動的經歷卻也促使他寫出比鄉愁本身更好的作品來,透過作品重置空間,沖淡無法歸鄉的痛苦。
只是,我亦確實敬佩所有滯留於原鄉的靈魂,無論他的形體是否被迫移動,幾乎某個抵抗的理由自願放逐,他與停留在家鄉的創作者純以語言打造了一個共同的國度。
對向櫃台有聲音喚住我。轉身看,是藝術家中唯一問起我中文名字怎麼發音的Carolyn。我把她的名字盡量唸得正確,問她今天創作進度如何?順道把好不容易完畢的找零工程告一段落。
她眼角的皺紋笑得好看,我的英文使得輕鬆,我們並肩走向往工作室的路上,心想自己比索忍尼辛幸運。稍晚,廚房供有熱騰騰的晚餐等候一干藝術家,餵飽迷失,讓曾在創作時迷入岔路的異邦人,不枉「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