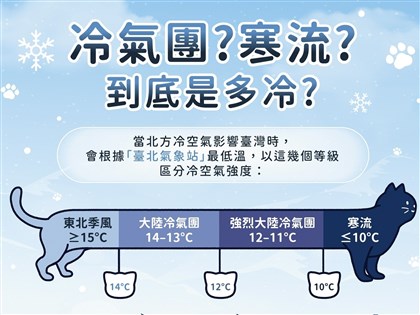吳念真 再當一次說故事的孩子
「每每當我聽到別人講故事,因此得到安慰或啟發或什麼的,自己就會開始希望能扮演那樣的人。」對吳念真來說,那天在高雄衛武營的「人間條件」演出,是他努力扮演「那樣的人」的方式。
文:汪宜儒
吳念真是台灣最會講故事的人。大家都這麼說,主角本人對此稱譽沒什麼反應,他沈默了很久,突然開口:「獅子座有個很強的個性──怕場面冷。」
那天,襯著結束工作的北返高鐵列車呼嘯聲,吳念真低穩的聲嗓瞬間引人飛越到他兒時的侯硐大粗坑老家,到那條長長的、從學校一路延伸到村口的上坡路。
「小時候放學,一大群人爬著上坡回家,大概要花上一個多小時,那很無聊,又不能期待別人,就自己想辦法…,我就加油添醋了那些幫大人讀過的報紙內容、看過的書、鄰居的閒話聊天,每天講給同學聽」,他說。
小吳念真在家多數時候大氣也不敢喘一聲,「囝仔人有耳無嘴」對他而言是至理名言。「我很安靜,因為隨便開口,很容易被大人罵。我就是聽他們講,聽那些我其實不是很懂,卻隱隱知道大人世界有點複雜跟麻煩的事情。」
那些靜靜聽來的「養分」,以及要將大人複雜故事說成讓同學聽得懂的「加油添醋、重新編排」過程,意外成了紮實的訓練。吳念真未曾想過,那一段回家必經而勢必走了千百回的上坡路,竟成了他後來在小說、電影、電視、廣告、舞台劇等領域創造獨到敘事節奏的牛棚暖身。
後來的日子,聽他說故事的對象從幾枚小毛頭擴成數以千、萬計的人們,吳念真被譽為台灣最會說故事的歐吉桑。但在夜深人靜獨處時,他想著自己的模樣,不是髮漸白的吳姓歐吉桑、不是備受稱譽的吳導演,是上坡路上的那個小不點吳念真,他講故事的初心,不曾因時空變換。
去年12月9日,高雄衛武營都會公園的草地湧入超過2萬名觀眾,在那充滿寒氣的夜晚跟著吳念真編導的舞台劇「人間條件」一起呼吸,一起笑著、哭著。或許因為那些演員所演的,笑著、哭著、煩惱著的,與所有人的日常是那麼近似而幾乎一致。
吳念真早因新浪潮電影、電視和廣告知名,直到2001年才開始跨足舞台劇,以「人間條件」為名,至今發展了6部作品。他寫人世的遺憾與虧欠,寫說不出口的愛與思念,寫責任與情義,也寫階級的殘酷、不公義與青年世代的掙扎,就是不寫心靈雞湯式的人生大道理,也拋開上對下的指導姿態,通篇呈現屬於生活的細節、最日常的對話模樣。
因此有人說他的戲是通俗的、八點檔的,他笑得很坦然,「我的戲沒有甚麼學術氣氛,沒有什麼文學性或企圖,被說通俗或八點檔,我覺得很對,也覺得很好啊,因為那表示能被人懂啊。」
戲劇的意義與模樣,在學院裡自有一套理論說法,但在吳念真腦裡,戲劇是他故鄉礦區那些不識字的叔伯嬸姨們都可以輕易靠近、理解的,也是他那不識字的阿公甘願背上小小的他、走上40分鐘路程仍願意親近的。「我的阿公很喜歡看新劇,就是現在說的舞台劇,他常常從我的家鄉,背著我走40分鐘的路去九份看戲。」
他一直記得那些看戲的場景,記得所有人在裡頭的呼吸反應。「可能在貧窮一點地方的戲劇或電影,通常放悲劇會很好哭,除了是看了會難受所以哭,也是因為現實生活的很多時候是想哭不能哭,趁著看戲、看電影,終於可以哭出來。我想,戲劇最好的地方就是這個吧。」他的笑容裡,藏著鄉下孩子才會擁有的理解。
他還記得有一次,看完戲的回家路上下起大雨,阿公帶著他在有應公廟躲雨,「我手上吃著阿公買給我的一塊豬肝,身上蓋著阿公的外套,我們一起看著雨停。遠方山邊突然有兩道彩虹,我到了長大才知道,那叫霓。雖然阿公離開很久很久了,但那個下午的畫面,到今天都印象深刻。」
那些飄散在黑暗戲院裡的氣味與呼吸,那些故人的哭泣與笑,從此就沈澱在吳念真心底深處,不論小說、散文或電影、舞台劇,吳念真後來創作總是很自然的想著他們、對著他們。也因為他們,他從此有了「戲劇最大的作用是理解與安慰」的體悟。
(本文出自第一期封面故事「吳念真的人間條件」)延伸閱讀》獲政院文化獎謙稱「不應該是我」 吳念真要將獎金捐出助弱勢
延伸閱讀》80歲仍創作不輟獲文化獎 畫家謝里法:畫到老、畫到死
延伸閱讀》年度十大藝文新聞 林懷民宣布退休奪冠
本網站之文字、圖片及影音,非經授權,不得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及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