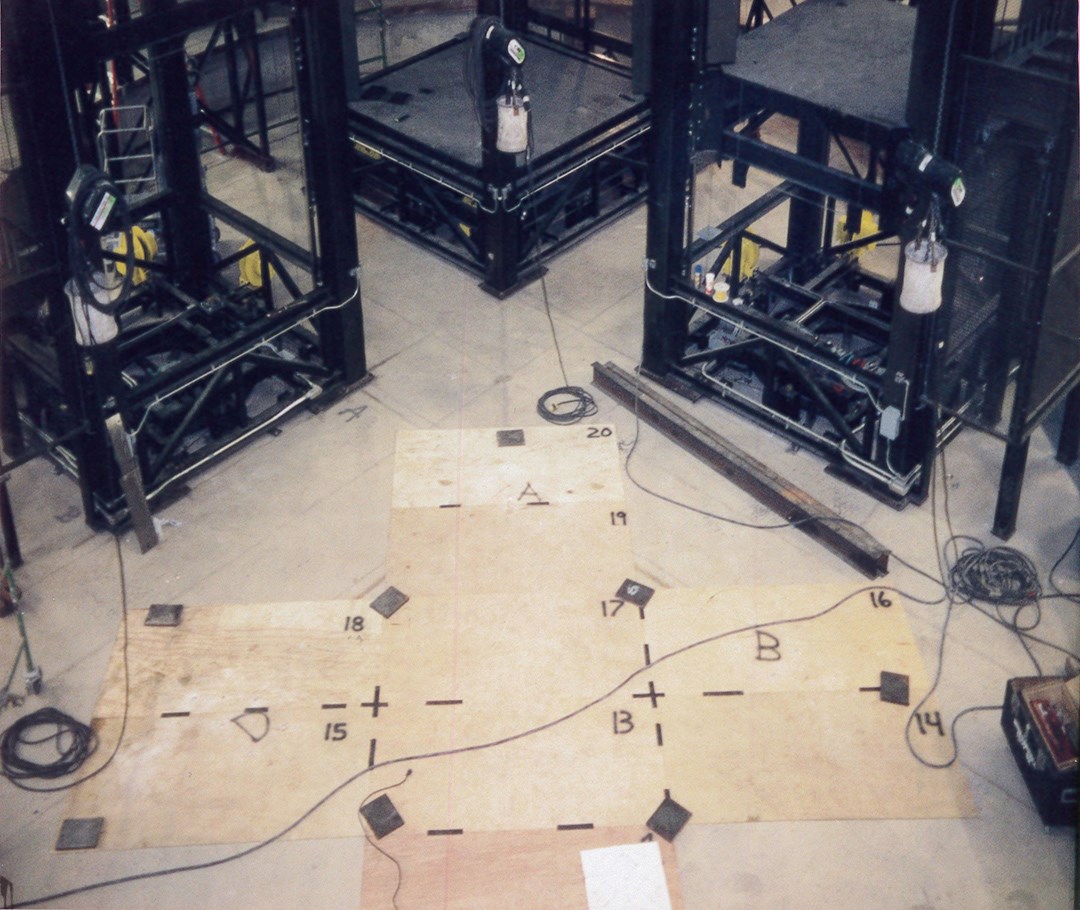棒球給的情緒價值
正當我在想構圖時,台灣隊擊出適時的一棒,觀眾席集體站了起來,連同冷靜的區域及啦啦隊都往球的方向看去,確認擊出安打後,全場又熱情的歡呼,啦啦隊亦又帶動觀眾為選手加油喝采……
滑著馬天宗的臉書,大多數的照片都是合照,還常常找不到他站的位置,總是藏在低調的角落。這也很像他的個性,他說他喜歡把事情做成功,但不一定要他領頭;如果領了頭,他就要做到對團隊最好。
「我不怕跟人家合作,要做好一件事,一個人的能力也有限。」馬天宗直白說,「我不是那麼聰明的小孩,如果不跟夥伴一起,我一定做不成。我從來沒有把我自己當做是那個帶頭的,如果我扮演領頭的角色,最重要是把團隊組好。」
這就是製作人的必要條件,可以帶頭衝也可以退居幕後,習慣也喜歡團隊合作,才能讓一齣音樂劇有機會達到完美。
現在掛大清華傳媒總監製的頭銜,馬天宗其實很斜槓,他是Legacy創辦人、中子文化製作人,投資電影、唱片;投資餐廳,賣貝果;他做簡單生活節,投資美國百老匯音樂劇。回到台灣,他為了讓音樂劇有沃土可以生長,爭取承租政府閒置空間,成立南村劇場以及空總劇場,透過空間孕育更成熟的劇場作品,這 些全來自他大學時期對於劇場的概念以及美國讀書與百老匯工作的十多年經驗。
「劇場可能是我血液裡面比較厚的東西,但我究竟怎麼會跟音樂劇發生關係,沒有甚麼天大的緣分,純粹就是我沒有選擇。」馬天宗說,清大核子工程本來是他的第一志願,也順利考上,「但是我念半年,我就發現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到畢業典禮前一天才補考完所有科目。」不過大學4年也沒白過,他至少明白有一件事情是自己喜歡的,那就是劇場。
馬天宗從小玩團,擔任鼓手,「因為鼓手不需要搬樂器,去演出鼓一定會就定位,我就開始幫大家整理樂器弄音響。」大二他參加學生代表聯合會,常常需要辦活動,正好學校禮堂的燈光音響剛換新,學校的管理伯伯又不想管,「我就帶著活動組的學弟們想去學,學了,會操作,就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馬天宗回憶,當時有一個學長很會操控這些機器,「派去學的學弟們都被他罵回來,說太笨,我只好自己去。」馬天宗的方法是每天跟在旁邊一直看,偶爾問一個問題,「要謙虛,不能太聰明也不能太笨,前後大概一個多月,學長開始對我比較信任。」工作來了,馬天宗就會主動幫忙,開始上手。
不喜歡上課,馬天宗常常在禮堂出沒,舉凡口琴社,合唱團,吉他社,外語系的話劇比賽,畢業公演,只要跟劇場相關,馬天宗就幫他們做燈光。馬天宗說舉例,1989年當時《悲情城市》是台灣第一部採用同步錄音的電影,但那時好萊塢電影《魔鬼終結者》出了第一集,特效已經嚇死人,「台灣在燈光音響音效這幾塊發展得很晚,那個時候沒有網路,知識取得很難,拿到幾個英文單字就可以研究3個月。」
也是在清華,馬天宗認識了他生命中第一個專業劇場人鍾寶善,當時蔡明亮在小塢劇場自導自演《房間裡的衣櫃》,鍾寶善負責巡迴時的舞台和燈光,他就幫鍾寶善執行,開始對於劇場專業有興趣。當兵後開了唱片公司,邀請李泰祥製作以交響樂的方式演奏流行音樂,為了學習更多的製作知識和技術,馬天宗決定出國念書。
馬天宗盤點自己大學四年,發現劇場這一行的專業台灣真的很缺乏,應該出國學習。帶著出國前做過舞蹈家劉鳳學、京劇名伶郭小莊等人的演出經驗,馬天宗出國念書,「出國前鍾寶善還送了我畫圖的尺,我隨身帶上飛機,他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貴人,至今仍然懷念。」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馬天宗申請了10所學校,9所學校都是申請燈光設計,最後耶魯大學的劇場技術設計與製作管理系錄取他。念完之後正好有了孩子,他也就留在美國工作,一路從技術設計、製作管理到公司合夥人,從百老匯音樂劇做到拉斯維加斯大秀。
馬天宗說,開始了百老匯的工作之後,發現停不下來,「因為太好玩了,也就沒有想到回台灣這件事情。」那時候美國有三大百老匯製作公司,他上班的是其中一家,一開始從設計部的製圖員開始,到負責製作技術統籌,一年總是要做六、七檔音樂劇;「後來公司有點經營不善,大家都跑了,只有四五個人包括我留下來。我看到的是,老闆很會做業務,但是公司內要有人可以執行。」他跟老闆合力再造這個公司,從技術轉管理到營運合夥人。
馬天宗陸續從從迪士尼的秀做到台灣的秀,也為月眉育樂世界與花蓮海洋公園規畫表演。2002年正式回到台灣,馬天宗先在電影公司發行製作,2005年曾經在北京做音樂劇《電影之歌》,介紹中國電影100年,當時導演是張婉婷,合作歌手包括庾澄慶、房祖名等藝人。2013年,馬天宗在台灣開始做音樂劇《搖滾芭比》,還把《木蘭少女》推去新加坡做跨國演出,正式一腳回到了音樂劇產業。
「回頭來看,我覺得命運給我的比較多,但也是等命運來了之後,我有能力做就做。」馬天宗說。
音樂劇《木蘭少女》是台大戲劇系十周年大戲,馬天宗去看了之後,非常喜歡,主動聯絡創作者王希文,之後又合作了音樂劇《搖滾芭比》,也發現台灣發展音樂劇的困境,「沒有劇場空間,周一進劇場,周四才有機會總彩排,週五到週日就結束了,這非常不符合劇場專業,而且非常浪費,也才有了後面的南村劇場跟空總劇場。」
「我會想做南村劇場,也是因為耶魯大學念書時的啟發。」馬天宗說,耶魯有自己的學校劇場,完全跟教學相結合。但也有一個Cabaret劇場由學生自己管理,自己排節目,自己生劇本,演出,學校完全管不到。那真是很有爆發力,「每個星期我們都會看到新東西,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就是劇場的可能性,有些戲是好到連紐約都會有人跑來看。也許是音樂劇,也許是嚴肅話劇,這個事情對我來講說:哇,原來那個戲劇的最根源,那個泥土如果夠豐富,就可以長出奇花異草。」
另一個重點是,當馬天宗看到許多演出都被迫上大劇院。但是要花很多精力去照顧大劇院裡外的東西,反而沒有花時間把文本做好,「戲劇的本質如果文本夠好,演員可以傳達,就有機會了。所以讀劇為什麼這麼重要,只要一讀,就知道它可不可行,就像我們在上編劇課的時候,編劇一讀就知道可以不可以。」。
馬天宗思考台灣現狀,以台北市藝穗節為例,一年也有個百來齣小戲劇,如果有兩個好看的,也很值得,但藝穗節演出之後呢?馬天宗認為,如果有一個像耶魯的Cabaret劇場,就有可能長出奇花異草,也有可能迫使大家面對文本,面對演員,回歸戲劇的本質。現在有了南村劇場,也就有長演的可能性,也就是做長銷劇,這也是音樂劇可以成功重要環節之一。
在百老匯工作十年,馬天宗參與各種製作,「有的製作是為了賺錢,比如說太陽馬戲團,沒有什麼好囉嗦的,賺錢最重要。」有些製作是為了藝術家,比如說有些音樂會就是為了參與的音樂家,「那些中間不准觀眾進來的,都是以表演者為為主。那些可以在段落之間放觀眾進來的,大概都是娛樂為主,當然這不能
以偏概全,只能大概心中有底。」
身為製作人,馬天宗認為首先要很清楚知道要去的目的地在哪裡,「有的可能是政策,有些為了溝通,有的為教育,設定的總體目標不一樣,達到這個目標的手段也不一樣。」挑戰之一是整體最後呈現的完成度,第二個挑戰是如何面對預算。「做製作永遠都只有有限資源,有人是選擇在有限資源裡面做完,有的可能是有限資源之外擴大或超支。」
馬天宗說,在學校常常會被教導要學會控制預算,但思維就很容易被天花板擋住,「百老匯教會我第一件事,如果做這件事情,可以賺更多錢,做。」馬天宗不諱言,這是很資本主義的學習,「資本家的思考出發點,有機會賺錢,我就做,我就投入。」
此外還要挑戰「判斷哪裡要花錢,哪裡可以不要花錢」,學會如何去分配資源。馬天宗說,每一個製作都會有「意外」,如果這個部門可以省一點,就可以把預算撥給更需要的部門,「這個判斷對我來講非常重要。大家有時候覺得我很節省,但我前期的『摳』是為了後面做準備,因為等到最後兩個禮拜,最後一個禮拜要上演,只要是錢能夠解決的,都是簡單的事情。」
馬天宗說,「如果花五毛錢就可以做完,那我就只花五毛錢;但如果這個效果是亮點,即使只出現1分鐘,需要90萬美金,我會加。」馬天宗說,劇場賣的就是驚喜,效果到位才算到位。
馬天宗也認為,就像影視影產業,如果在本土都不能跟國外產品競爭,那怎麼在國外跟人家競爭,「如果串流平台打開沒有前十名,就不用玩了。音樂劇也是,要做就要做到好,台灣市場做好了,就會有機會長銷,外銷。」
馬天宗舉例,過去20年來,全世界土壤沙化嚴重,導致再也不能耕種,情況嚴重,科學家研究發現,因為 農人用了太多的氮肥,導致地力流失,科學家後來使用自然耕法,或不用農藥,或飼養天敵,讓地力重新再回來,「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一直給肥料,土壤到最後還是不會好。」從這個例子回看台灣音樂劇產業,馬天宗不諱言,20年來,大家沒有停過倒水給劇場及影視産業,但累積不多,「只要有人問我,我都會講一樣的事情,一個漏水的桶你倒多少水,就會漏多少水,但如果桶子是不漏水的,即使只倒一點點水,都會有累積。」馬天宗認為,台灣音樂劇有很棒的演員,有很棒的創作者,但大環境還是讓身處其中的從業人員感到「微臣無力可回天」,「整體生態系要健康,音樂劇才能長得好。」
回想這些職涯,馬天宗覺得自己很幸運,「如果有機會,我就想分享,沒甚麼好藏私的,藏就是因為對自己沒信心。」馬天宗說,這一行要多跟人家交流才會變更好,「還有一點很重要,如果是削價競爭,市場就會越做越小,我不搶餅吃,搶餅吃有點羞羞臉,有本事的應該是把市場做大,大家都有餅吃。」馬天宗期待在台灣,整體的音樂劇產業不管是在技術上,還是在產值上都能持續進步,音樂劇才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