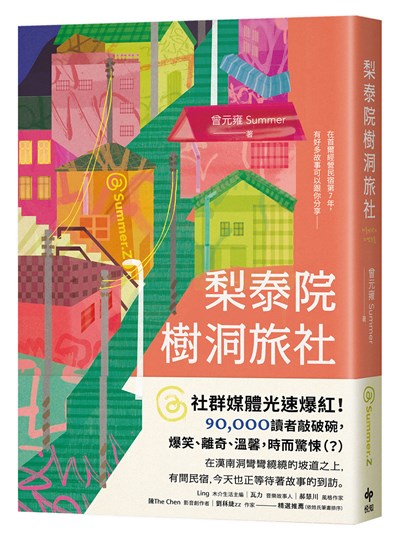2011開卷十大好書(中文創作)
推薦理由:作者著意書寫上海,此次更以一貫的工筆手法,細細描摹現代上海為人忽略的前史,透過一個傳統仕宦家庭造園織錦的尋常世情,側寫出這個古老帝國在現代大浪來臨之前的晏好微瀾。(朱偉誠)
——轉載自《中國時報‧開卷》
文章節錄
內文節錄
天漸漸冷下來,園子封了。宅子完工,章師傅帶了蕎麥阿毛回家,申府上冷清下來。小綢就帶著丫頭在屋裏,生一個炭盆,炭灰裏埋了花生、核桃、紅棗、白果,烤熟了,用長筷子搛在碗裏吃。時間在炭火的暖和糧食的香裏消磨著,往柯海回家的日子挨近。有時候,小桃和鎮海媳婦相邀來串門,帶了各自的孩子。阿奎五歲,阿昉只半歲,丫頭很是高興,要阿奎替她砸核桃,又要看嬸娘餵阿昉吃乳。與丫頭相反,小綢冷冷的,小桃以為嫌自己是姨娘,鎮海媳婦卻知道其實是對她。免不了的,要算計柯海的行程,鎮海媳婦說,無論如何,總是要回家過年。小桃說:倒不見得,維揚那種地方,處處留人!鎮海媳婦想攔沒攔住,小綢已經變臉:他愛回不回,我和丫頭兩個人就很好,我們向來喜歡清靜煩人多。話裏是嫌她們打擾的意思,這兩個走也不好,留也不好。只得另起話頭,議論妹妹的嫁娶,因正有新場的杜姓人家,託媒過來。杜家祖上中過進士,做過漕運監司的官,很慕申家的名聲。小綢就說:申家有什麼名聲?不過是顯富罷了,就是這一點叫人家看中,所以不顧正出庶出,只要嫁妝。話一出口冒犯兩頭,小桃是姨娘,阿奎便是庶出的身份;鎮海媳婦的嫁妝滬上出了名的,如此彷彿就只剩嫁妝,沒有人品,倒成了詬病。橫豎談不攏,串門的就要告辭。可丫頭正拉著阿昉的手,要將攥緊的拳頭攤開,看裏面藏著什麼。拳頭攤開,什麼也沒有,兩人都很意外,再將手翻過來看背面,還是沒有。大人們就靜靜地看孩子玩。
下雪了,小綢終究憂鬱下來。柯海臨走那一夜寫的字,小綢收起來,又展開,等他回來親手裱。不由想起柯海調製漿糊的情景,那麼有興致,那麼有耐心。夜裏睡不著,打開妝奩,看那一塊塊的墨,看著看著,忽然嗅到了柯海的鼻息,呵在鬢邊,一驚。回頭看,房裏只有丫頭,伏在枕上酣睡。滿屋子的綾羅帳幔,都寫著柯海給起的字:綢!小綢念著自己的字,忽覺出一絲不祥,這“綢”可不是那“愁”?雪打在窗戶上,沙沙地響,響的都是“愁”字。早上起來,鴨四進套院裏鏟雪,說門前方濱成了一條雪溝,船走在溝裏,就好像在犁地。小綢不指望柯海回來了,可柯海偏就在這天夜裏回來。船走在太湖,天下起雪,船家再也不肯走,也雇不到車,都不捨得用馬。錢先生留下了,柯海一意要回家,結果乘了八人大轎,幾倍的轎錢,一路還要好酒好話哄著轎夫,走一程換一程地過來。黑天白地,只見一乘雪轎停在方濱申家碼頭,轎夫們齊聲大吼叫門。門叫開了,出來一串燈籠,映得雪地像著了火一般。轎裏面沒有一絲動靜,揭開雙重轎簾,裏面是一堆紅花綠葉的鄉下被窩,幾雙手上前去刨出一個人,睡得暖和和的,不知做什麼夢,睜開眼就叫了聲:小綢!
夜裏,相擁著,小綢說:何苦呢?又是冰又是雪,一步不巧,滑到河裏餵魚!柯海就朝小綢身上拱一拱:吃吧,吃吧,你就是那條吃我的魚!小綢躲著他:哪個人要吃你!哪裡躲得開,柯海就像藤纏樹樣死纏著。小綢就說:既是如此,何不早幾日動身?柯海訴苦道:如何走得脫!阮郎的朋友多,都要見我們,一日恨不能排七餐宴。小綢不信:你們有那麼大面子!柯海道:並不是我們面子大,是阮郎面子大!小綢哼一聲,沒話了。柯海就將吃過的宴席在耳邊細數一遍,不外乎山珍海味,其中有兩樣稀奇是特別要說的。一是湯包,小碗大的一個,筷子夾起來,滿滿一兜湯在晃,一滴不漏,吃起來卻要十分在意,一不留神就燙了嘴;另一件說起來很普通,就是雞蛋,可要告訴端底,準得嚇一跳!小綢問怎麼了?一兩銀子一枚!柯海嚇人地說道,你知道為什麼?小綢愕然搖頭。那下蛋的母雞是用人參餵養的,所以雞蛋就有一股參的香,大補!小綢說:不如直接吃人參罷了,九曲十八彎,到頭還是一個參味。柯海只得解釋給她聽:好比你帶過來的墨,那一款紫草汁浸燈芯熏煙凝成的,泛朱紅的暗光,怎麼不說直接用紫草汁寫成字呢?小綢被他比得有些糊塗,轉不過來,又不服氣,翻個身說:千山萬水,拋家棄口去了數月,就長了吃的見識。柯海說:吃的見識也是見識,總比沒有的好。小綢說:好當然好,躲了清閒,不過,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見得讓我和丫頭兩個搬屋子,等著你來住!柯海就說:我這麼苦趕,不就為了搬楠木樓,咱們住新樓,也好把院子騰出來!
說了半夜的話,兩人都睏了,吹燈睡覺。燈滅的那一霎,滿屋子櫥櫃桌案、簾幕被蓋在眼瞼裏活潑潑地一動,小綢忽然覺得不安,一個字跳進心裏,就是那個“騰”字。“騰”這邊的院子給誰住呢?柯海急慌慌趕回來,是為搬新樓,還是為騰舊院子?
接下來的幾天,就是忙著搬住處和過年。過年的事輪不上他們小倆口操心,他們只管初二去岳丈家的年禮。半擔年糕,半擔上好的新米,兩疋姑絨,兩疋雷州葛布,兩斤佘山茶,兩斤燕窩菜,一斤檀香,一匣心紅標朱,十二刀荊川太史連竹紙。年禮備定了,新房間也安置妥了。燃了幾束松枝薰過,驅散了潮氣,又用茉莉花乾燃了熏幾日,滿屋生香。柯海走前寫的字,這會兒裱好了,掛在楠木樓的迎門地方,底下是新案子,擺了兩個官窯瓶子。臘月二十八,就要移床遷居,不料,這天一早就來客人,是錢先生。
柯海乘轎上路的第三天,雪稍下得緩了,錢先生就搭上一條船。船主是皮貨商,北邊進了貨,萬里趕了九千九,阻在錫山太湖裏,急著回家過年,說什麼也不肯等了。雪下一陣停一陣,船走一程停一程,終於到了上海。錢先生到家頭一件事就是來申家府上,拜見申老爺。柯海得著消息的時候,正幫小綢收拾那些墨水匣筆錠什麼的,因是小綢的嫁妝,特別上心,要親自動手,生怕底下人碰壞了。聽到錢先生來,柯海手一鬆,東西落下來,幸好小綢接住,嗔怪說:聽到虎朋狗黨的名字,魂魄就出竅!柯海辯解說:並沒有。小綢趕他:去吧去吧,別砸了東西,大過年的。柯海偏不走,臉卻紅起來。小綢就不讓他碰東西。當地站一會兒,百般無聊的,說了聲“去看看”,慢慢轉過身去走了。小綢停下手,看他走出院子的背影,心一陣亂跳,覺得事情不好。這不好彷彿是她等著的,這會兒等來了,很奇怪的,反倒踏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