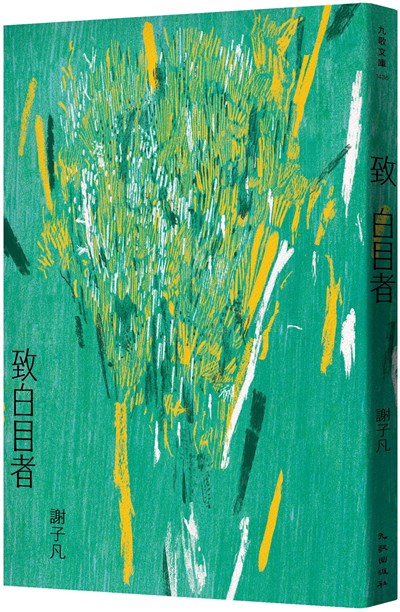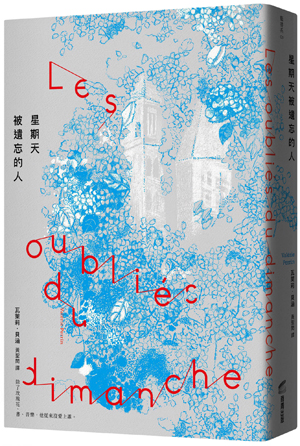
一開始吸引我的是幾個關鍵詞,法國勃艮地小鎮、養老院裡的老人,養老院裡喜歡聽故事的21歲照服員曲絲汀,以及喜歡說故事的失智老奶奶海倫。小說裡沒有葡萄酒,也沒有第戎芥末醬,只有一個又一個的謎排在讀者眼前,一切從小鎮那座叫做「繡球花」的養老院展開,透過年輕人的家族祕密與老奶奶的一世情迷,說故事的人勾勒織出一幅勃艮地小鎮百年史。
讀者聽著,第一次感覺自己那麼靠近勃艮地,那麼赤裸見到一座小鎮的戰後傷痕,又椎心刺骨地臣服於人物間各種愛恨嗔癡帶來的彷彿希臘悲劇張力般的毀滅性的愛與不被愛造成的人間至痛。
沒有是非對錯。用最輕靈詩意的文字描畫人間苦難的代表。瓦萊莉.貝涵在2015年推出這部處女作《星期天被遺忘的人》,三年間,拿下大小文學獎項13座,包括熱潮延續至2018年的「法國書店員年度選書」,這堪稱難得的法國版「鄉土小說」,以她如攝影師之眼捕捉得精妙到位的小人物故事,帶領全球讀者以另一種方式品味法國小鎮,共感普世的老年價值。
文章節錄
《星期天被遺忘的人》
我著迷於老人,最初是受到我的法文老師波蒂女士啟發,她有一天帶著國中八年級全班同學到「三杉安養院」陪老人度過午後,當時酩意鎮還沒有「繡球花」。那天,在學生餐廳吃完飯,我們就搭巴士去,車程約一個小時,我記得自己在牛皮紙袋裡吐了兩次。
抵達「三杉」時,老人家已在餐廳等候,裡頭有股濃湯混著乙醚的味道,讓我又開始作嘔。和老人們吻頰打招呼時,我憋著氣不敢呼吸,他們的臉摸起來刺刺的,臉上的毛髮整個失控爆炸。
我們班準備表演ABBA合唱團的〈Gimme ! Gimme ! Gimme !〉,我們身上穿萊卡質料的白色表演服,頭上戴著從學校戲劇社借來的假髮。
表演結束,大家坐下來和老人家一起吃可麗餅。他們個個手腳冰冷,抓著餐巾紙不放。從那一刻起,我對老人深深著迷:他們講著自己的故事。老人家沒事做,開始聊起往事。無人能比,比看書和看電影還精彩,實在無人能比!
那天起,我開始懂了,只要摸摸長輩,握握他們的手,他們就會開始講故事,像在沙灘上挖洞,海水自然從洞口湧現。
而我,在「繡球花」也有偏好的故事。她叫海倫,住在十九號房,是唯一能讓我真正放鬆的人。如果了解老年醫學服務的日常照護,就會明白遇見她是多麼奢侈的一件事。
院內職員私下都叫她「海灘夫人」。
剛到職時,有人跟我說:「她會在海灘的遮陽傘下待一整天。」而且,自她搬來,有隻海鷗也飛來「繡球花」的頂樓住了下來。
酩意鎮位於法國中部,從來沒有過海鷗,不過烏鶇、麻雀、烏鴉、椋鳥倒是很多,就是沒有海鷗,除了住在頂樓那一隻以外。
海倫是我唯一會直呼名字的房客。
每天早晨梳洗後,我們把海倫安頓在面窗的躺椅上。我發誓,她看到的風景絕不是小鎮的屋頂,而是美得無與倫比的東西,像一抹淺藍色的微笑。其實,海倫淺色的雙眼跟其他房客一樣:都有褪色床單的顏色。每次我心情不好,都會祈禱命運賜我一把遮陽傘,像海倫的那把一樣。她的遮陽傘叫呂西恩,是她的先生……好吧,應該說是半個先生,因為他沒真的娶她。海倫向我傾訴過她全部的人生故事,說全部,其實是拼出來的,好像是她送給我家裡頭最珍貴的東西,只不過送我前,她不小心把禮物摔成碎片。
幾個月來,她的話變少了,彷彿人生唱片轉到尾聲,音量漸弱。
每次我離開她的房間,會在她雙腿上蓋條毯子,她老是對我說:「我要中暑了。」海倫從不感到冷,即使在最冷的冬天,所有人離不開「繡球花」短路的暖氣機時,只有她一人恣意享受著太陽下的溫暖。
據我所知,海倫唯一的家人是她女兒羅絲。她是位繪圖師,也是設計師,畫了許多爸媽的炭筆肖像,還有海景、港口、公園和花束的寫生。海倫房間的牆上掛滿了她的畫。住在巴黎的羅絲,每週四搭火車到車站,再租車到酩意鎮。每次來都上演同樣的劇碼:海倫遠遠望著她,或者說,從她幻想的地方望著羅絲。
「您是?」
「媽,是我。」
「小姐,我不懂您的意思。」
「媽,是我,羅絲。」
「可是……我女兒只有七歲,跟爸爸去玩水了。」
「是喔,她去玩水。」
「對呀,跟爸爸。」
「妳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回來嗎?」
「等一下就回來,我在等他們。」
羅絲接著會翻開小說,唸幾個段落給海倫聽。通常她都挑愛情小說,每次讀完都把書留給我。這是她向我道謝的方式,謝謝我將她母親當自己媽媽一樣照顧。
上週四約莫下午三點,我遇上人生最瘋狂的事。我推開十九號房門,看見他,正坐在海倫的躺椅旁邊。牆上掛有幾幅呂西恩的肖像。是他本人!我像傻子一樣看著他們,站在原地不敢動:呂西恩握著海倫的手。而海倫的表情讓我差點認不出是她,好像她發現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他露出一抹微笑對我說:
「您好。是曲絲汀嗎?」
我心想,噢,呂西恩竟然知道我的名字,這也很正常,畢竟鬼都知道人的名字,也應該知道很多我們不曉得的事。我也終於明白,為什麼海倫願意在海邊癡癡地等,讓自己的時光暫停。
只消一眼就秒懂,這種男人的出現,就像命運用頂級的宅配服務把對的男人一次送上門。
他的雙眼……有我不曾見過的藍,就算翻遍奶奶的郵購目錄也從未看過。
我支吾問道:「您是來接她的嗎?」
他沒回答我。海倫也沒作聲,只像中邪一樣盯著他看。她的眼睛哪有什麼褪色床單的顏色,那一瞬間,全-部-消-失。
我走近他們,輕吻海倫的額頭,她的臉比平時來得燙。我的心情像天候一樣,宛如俗語說「惡魔嫁女兒」:天空終於放晴,我的心底卻下起雨。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呂西恩終於玩水歸來,準備帶她去天堂。
我緊握海倫的手。
「您會帶海鷗一起走嗎?」我問呂西恩,語帶哽塞。
從他看我的表情,我想他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原來我面前的這人不是鬼。
當下,我覺得人生好恐怖,這傢伙確實活著。我腳底抹油,像個小偷般轉身溜出了十九號房。